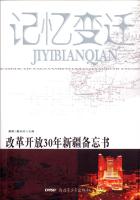——访著名女翻译家许磊然你如果曾经受到过俄苏文学的熏陶,大概不会忘记叶水夫和许磊然这对“夫妻翻译家”的名字。许先生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工作,主要译作有普希金、屠格涅夫、法捷耶夫的小说,尤其是西蒙诺夫《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真正的人》、马卡连柯《教育诗》,在我国影响甚大。而叶先生翻译的《青年近卫军》自1947年出版以来,更是备受读者青睐,点燃了几代青年心中的理想之火;1988年他离休以前,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世界文学》主编。
许磊然回忆往事这是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我来到这个高级知识分子之家。进门第一感觉就是整洁、舒适。客厅排列着的书柜里面,大都是整套整套的外国文学书籍,琳琅满目。年近八十的许先生聊起天来轻言细语,一派安然的神情。因为事先已收到我寄去的有关咸宁干校的资料,她热情地说:“读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挺好的,倍感亲切。我在向阳湖度过的岁月,至今难忘……”
许先生缓缓介绍道,“文革”之初,她也和社里许多高级编辑一样,差不多都被关进“牛棚”。由于她和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有交往,随时可能被戴上一顶“里通外国”、“苏修特务”的帽子,后来不知怎么竟没被“揪出”,随大流下放咸宁。她当年所在的十四连,知名作家不乏其人,译林高手亦比比皆是,如孙用、金满成、赵少侯、金人、纳训、刘辽逸、蒋路、孙绳武等等。大家整天一起劳动,吃过早饭马上出工,起码要走上半个钟头才能到达工地。咸宁的雨水多,有时下小雨还不让收工,非得等大雨淋得满身透湿才停下来,弄得她回到家里,不知是先洗头还是先洗澡……这样累得够呛,再也没有时间和兴致看书。后来,连里考虑她年纪偏大,才照顾干轻微一点的劳动,和金人一起值班守夜。
说到金人,许先生自然流露出惋惜之情。她告诉我,这位《静静的顿河》译者吃苦头在于嘴巴没有“把关”。例如,在社里同事一起闲聊,有人说《毁灭》里写知识分子领导革命,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没想到金人却提出疑问:“毛主席的话就是句句对的吗?”那时,林彪强调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岂不是自找苦吃,结果被批得灰溜溜的。下放到向阳湖以后,金人精神受压抑,又患高血压,可谓祸不单行。最让他伤心的是,离开咸宁转到丹江时,孤零零的,没有人敢送他。还是许先生得知后赶到,聊表同事之谊,他才忍着泪水上了卡车。到了鄂西北,他的病情日益加重,而从京城赶来的妻子仍和他“划清界限”,训斥他“不要耍死狗”,使得这位杰出的翻译家很快命归黄泉。
我听了一阵难受,不免心中发问:金人之死应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点什么?这时,一直在沙发上“旁听”的叶水夫先生插话道,“文革”中像这种划清界限的事情并不少见,别提了!他转而谈起自己下放的河南信阳干校,那里的名家也很多,如钱钟书夫妇、俞平伯、何其芳、刘大年、罗大冈、孙冶方等等,大翻译家有冯至、卞之琳、戈宝权……
我随口问道:“下放干校的文化人那么多,为什么至今尚未形成‘干校文学’的气候呢?”叶先生笑了起来,说这个问题他倒是没有想过!沉思片刻,他马上回答说:“照我看,知识青年下放,一般都没什么专业,回城后很多人热心写这类题材的小说,才成了作家。而下放干校的人不同,大都有固定的岗位和专业,回来后不可能改行再搞创作,这至少是原因之一。但杨绛之所以写出《干校六记》,因为她本身也是搞创作的。”许先生听罢表示赞同,又补充道:“干校的历史不好说,既不能耿耿于怀,又不能不当回事,而且还涉及许多个人恩怨,而知青们都比较单纯,没有这种顾虑。”
作者和许磊然我20年前也当过知青,对老两口的话深以为然,于是,也坦陈己见:“不同干校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你们夫妻分居两地,命运却紧密相连,我正好可做一些分析比较。写好咸宁干校,也可以附带反映其他干校的人和事。”
两位老人又分别介绍了一些干校趣事。在向阳湖,一位鲁迅研究专家有次挖沟,不慎掉下水,吓得大叫:“快来救我!”事后还被大家开玩笑。又如,十四连最后一个连长是翻译家卢永福,他因此被大家戏称为“末代皇帝”。而叶先生在干校也闹过“笑话”。一次聊天,他兴头上忘了自己的“身份”,说起将来工作怎样怎样,被人钻了空子:“你还有将来呀?难道还指望回北京吗?”
许先生叹息道:“他到咸宁来看过我,也是从不谈业务,只是说哪一天争取‘解放’,然后他说那边苦,我说向阳湖苦。那年头能有空去咸宁洗个热水澡,就是我最大的享受!”
好在这颗昔日译海的“明珠”,终于等来了重操旧业的机会。许先生从向阳湖回京以后,又编辑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果戈理的《死魂灵》、《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和《屠格涅夫选集》等名著,1979年起担任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现改名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后来又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93年获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委员会委员。临别时,我顺便请教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搞翻译的人多了,出书的速度快了,但高质量的却少见,同一名著出了多种版本,不像过去老翻译家译几本名著磨了多少年,许先生如何看待这种状况?她答道:“从前出版文学译作,只有北京的‘文学’和上海的‘译文’两家,现在是全国遍地开花。一本《红与黑》,出了十几个译本,可见繁荣的背后缺少宏观调控。如果古典的作品都抢着去翻(因不涉及版权),现代的就译得少,印数也就上不去,包括外国文学期刊也是如此……”
从1977年至今,我一直坚持订阅《世界文学》,因此对这番话亦有同感,忧虑之余却无能为力。随后,我接过老伉俪惠赠的几本精装译著,感到沉甸甸的。乘着皎洁的月光,又美滋滋地返回了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