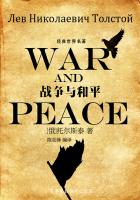一
关于回龙村的来历,说法有许多,最确切的有两种。一种是说从村前流过的檀江流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然后酣然入海,如同一条青龙在波光潋滟中一次舒畅的舞动。还有一种说法是村子背后的紫云山宛如一条青龙探海,随后傲然回望。对于这两种说法,村子里的人都十分认同。村前横碧水,村后倚青山,自然是绝佳的风水。
司徒振南离家快半年了,住在村东头那间土屋里的邓秋月收到了他寄回来的第一封信和第一笔钱,知道他没有去加拿大,而是去了美国的三藩市,而且还找到了阿力婶的丈夫。一家人悬了半年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这之后,每隔几个月都能够收到振南寄来的银信(附有家书的汇款单),很快就还清了振南结婚时欠下的债,还买了一小块田耕着。司徒乔想,这样下来,用不了五年,就能够起新屋了。秋月对于起新屋的事情倒不是特别在意,除了照顾好司徒乔父子俩的起居饮食外,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个月替振南做一双鞋。当箱子里的鞋积够六十双的时候,他就该回来了。
振南走后,十五岁的司徒振江便开始承担起了下地、砍柴、挑水等粗重一点的活。可他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依然是跟着师傅司徒永堂练功夫。司徒永堂年轻时参加过义和团,近些年年纪大了才回到乡下种田,闲暇时便教村里的小孩们练练拳。别的孩子都是学几天,图个新鲜便不学了,只有振江跟着一学就是好几年。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也只有振江才算是自己真正的徒弟。
振江本来就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练了几年之后,总想找机会试试自己的功夫。有一次,在几个混小子的怂恿下,他试着爬上七八丈高的老榕树尖上,壮着胆子往下蹦,可还是摔了个头破血流,气得司徒乔拿着棍子撵着他满村子地跑。后来还是秋月护着他,好说歹说,才让司徒乔消了气。
尽管司徒乔一天到晚叮嘱他别闯祸,可他一出去就忘了。不是和人打架,就是在山崖、树头上蹦来蹦去。就连在地里干活,也是一边干,一边将锄头乱舞,使得秋月隔几天就得替他缝补衣服裤子。
有一次,因为见隔壁村里的几个混小子抢司徒永年的儿子司徒盛才手里的东西吃,振江气不过,又和他们打起来了。对方人多,个个都比他大,他赤手空拳打不过,就捡了根棍子和人拼命,结果打伤了两个,他自己也鼻青脸肿地回来了。这一次,司徒乔决定不放过他,将他绑在祠堂门口的木柱子上,整整一天不给吃不给喝,把秋月心疼得坐立不安,可又不敢去劝自己的公爹。乡亲们见了,也都又好笑又好气,都来劝司徒乔。可司徒乔就是不松口,决心要绑他一天一夜。后来还是秋月和司徒永堂使诈,骗走了司徒乔,喂他喝水,吃东西。
那次之后,司徒乔不准他去练武。可这简直要了振江的命。他犟起来,任司徒乔怎么骂,任秋月怎么哄,就是不吃饭。三天下来,司徒乔心疼了,知道犟不过这混小子,只得又松了口。振江也发誓,以后决不随便和人动手了,这事才算了。司徒乔心想,一家之中,振南和秋月都识文断字,这个混小子爱练功夫,两兄弟一个文一个武,也很好了。可这小子天天这么练,功夫到底练到了什么程度?谁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才让大家对振江有点刮目相看的味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天,福贵的妹妹谷雨和邻村的两个姐妹一起到镇上趁墟(赶集)。自从福贵失踪之后,由于福贵爸身体不太好,福贵妈眼睛又不方便,里里外外很多事情都是谷雨在操持。十五岁的谷雨这时已经出落得水灵灵的了,走到哪里都常会碰到些坏小子调戏。这天卖了瓜菜,买了些生活用品正要回家,却被五六个混小子当街拦住,动手动脚。三个姑娘吓得直哆嗦,街上的人谁都不敢上来劝阻。恰巧振江也赶集经过,见到这种情形,忙过来阻止。说不了几句,就动起手来。振江也不含糊,一阵风似的将几个混小子全揍趴下了,拍拍身上的灰尘,没事人似地走了。
这事一传一渲染,大家都知道司徒家的老二一身好功夫。第二天,村里就多了好些个小子要拜司徒永堂做师傅学功夫。司徒永堂得意得吹嘘了好些天,说是振江现在才学了自己五成功夫。要学全了,一个人打二三十个也不在话下。
可从那以后,振江却傻眼了。因为他爸让他以后每次趁墟都和谷雨一起搭伴去,还得和谷雨一起回。福贵失踪之后,司徒乔平日里总叮嘱秋月和振江多去福贵家里走动走动,有什么事情帮一把。挑水劈柴这些事振江都十分乐意干,可现在让他陪着谷雨去趁墟,而且必须“寸步不离”,让他实在太难受了。
陪了一次,他就向他爸提出坚决不干。他说以后谷雨家里要卖什么,要买什么他都包了,就是不和谷雨搭伴。司徒乔却坚决不允,把振江臭骂了一顿。秋月在旁边听着忍不住笑。振江听嫂子笑,脸胀得通红。
按照司徒乔和福贵爸的想法,这两个孩子迟早是一对。谷雨不仅长得好看,人又伶俐,又勤快,嘴也甜,司徒乔心里是一百个满意。他常想,两个儿媳妇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也算是对得起死去的妻子了。福贵爸妈对振江也满意,这孩子人憨厚、诚实、听话,他们心里早就将他当成自己的女婿看待了。两家老人甚至已经多次商量订亲的事,只是瞒着两个孩子没有说破而已。
就算两家老人不说,谷雨心里也有些谱了。村里那些多嘴的媳妇大婶们常会将他俩摆到一起来开玩笑,就是秋月也私下里拿她和振江取笑。渐渐地她的一颗心也系在了振江身上。振江被他爸强逼着陪她去趁墟的时候,她偷偷地一路观察着他。她将振江一路上的模样悄悄地讲给秋月听,秋月笑得气都喘不过来。
二
在檀江岸边,绵延十多里都生长着像伞盖一样撑开的蒲葵树,将葵叶割下来晒干,制成大大小小的葵扇葵帽葵篮,拿到镇上和县城里去,倒也能换几个钱。这项手艺在回龙村已经延续了近百年。农闲的时候,人们就开始忙着割葵,晒葵、编葵。
这天,人们像往常一样坐在村头的老榕树下编着葵,聊着革命党人在各地造反的事情。正在议论着,司徒乔深吸了一口烟,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剧痛,随后是一阵撕心裂肺似的咳嗽。咳着,一阵晕眩,一头栽倒在地上。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回家。郎中赶来检查了好一阵,走出门对秋月说:“怕是不行了,你公公长期内伤积损,以致气血逆乱,气滞血瘀。我开几帖药,吃几天,看有没有好转。如果几天之内,不见效果,你们就准备后事吧。”
接下来的几天,秋月和振江都日夜守护在司徒乔的身边伺候着,情况却没有一丝好转。又到县城请来医生看了,吃了他开的药,仍是没有效果。司徒乔躺在床上,眼睛紧闭,口唇青紫,气息越来越微弱。
深冬的夜晚,透着彻骨的凉,守候在司徒乔床前的秋月虽然已经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却没有丝毫的睡意。她呆呆地望着躺在床上的司徒乔,想着自己的心事。振南已经半年没有消息了。以往每隔三四个月她都能够收到他寄来的银信,可这半年来却音讯全无。这些日子里,她的心一直悬在半空。现在公公又倒下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醒过来。她就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了。想到这里,她扭头看看身边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的振江,这个可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浑身都充满了力量。但是爱冲动,喜欢打架的毛病却一点没改。这次却也把他累坏了,白天里到处求医问药,晚上又整夜地守护着父亲,几天下来他已经明显消瘦了许多。她心里想着,振南呀,你在哪里呀?你知道我多想在你的肩头靠一靠吗?
发着呆,脑子里不知怎么又浮出小时候父亲教自己背的一首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振南,你总不会让我忧伤以终老吧?一阵揪心的恐惧在秋月身体里弥漫开来。
胡思乱想着,天亮了。秋月想,新的一天又到了,希望今天能够有奇迹发生。这两天,也不断有乡亲来劝秋月去紫云山上的黄大仙庙去求求神。一来秋月和振江都不懂,二来确实不敢离开半步,也就没去。这时她忽然想,这世上如果真有菩萨,有神仙,那么他们必定是无处不在,必定能够听得到我的求祷。
想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就跪倒在了司徒乔的床前,默默地在口中念道:“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各路神仙,求你们保佑我家公快快醒来,求你们保佑我丈夫司徒振南平平安安,求你们告诉我他在哪里?这个家需要他。”默默地念叨了好几遍,站起身来,准备去厨房熬点粥水。这时却忽然发现司徒乔的眼皮轻轻蠕动了一下。她以为自己看错了,忙凑上前去,一连轻声地唤着:“阿爸,你醒醒!”果然,司徒乔的眼角又轻轻地动了一下。一阵巨大的惊喜涌上她的心头,她加大了声音唤着,又忙一把推醒了司徒振江。两人都欣喜若狂地唤着,振江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感觉到父亲的手上也传来微微的力量。
半袋烟的工夫后,奇迹果然发生了,司徒乔一直苍白的脸上现出了淡淡的血色,一直紧闭的眼睛微微睁开了。感谢菩萨!感谢各路神仙!秋月一把抓住振江的肩膀,眼泪像泉涌般流了出来。振江也高兴地大叫:“阿爸,你终于醒了,阿嫂,这下好了,这下好了。”
秋月忙对振江说:“你守在这里,不停地和爸说话,别让他又睡着了。我去熬些粥水,煮点鸡汤,给阿爸补补气。记住,不停和阿爸说话。”
熬好粥水,慧清爷、司徒永堂、福贵阿爸也都来了。司徒乔虽然眼睛睁开了,却一直无神地盯着蚊帐顶,嘴巴也张不开。大家慢慢地将他的嘴巴撬开之后,才能够喂一点点粥水下去。慧清爷和司徒永堂将秋月叫到门口说:“秋月,看情况,不像是有好转,只怕是回光返照,他还有话交代。死不闭眼睛呀。”
秋月心里一沉,刚冒出来的欣喜化为乌有。几个人重新回到司徒乔的床头,坐了下来。司徒永堂将秋月和振江都叫到跟前,然后握着司徒乔的手,大声地和他说话:“哥,我是永堂,我现在问你话,要是说对了,你就眨一下眼睛。你是不是有话要对孩子们说?”
大家都看到了,司徒乔的眼睛慢慢地眨了一下。
司徒永堂看了秋月和振江一眼,又对着司徒乔大声问:“你是不是舍不得抛下孩子们就走?”
司徒乔眼睛又缓慢地眨了一下。
司徒永堂说:“你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也都大了,放心吧。想振南了吧?”
司徒乔眼睛又缓慢地眨了一下。
司徒永堂看了秋月一眼,秋月会意,强忍着眼泪大声地说:“阿爸,您放心,振南很快就会回家。我会和他一起好好过日子,照顾好振江。”
司徒永堂又问:“有什么话要对振江说吗?是不是放心不下他?”振江也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妙,忙凑到父亲跟前,大声说:“阿爸,您放心,我已经长大了,我一定会听阿哥阿嫂的话。我会撑起这个家,等着阿哥回来。”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以这样的方式和司徒乔做着最后的沟通。福贵阿爸也握着司徒乔的手,哽咽着说:“兄弟,我两家一起几十年,亲如一家。你现在要先走了,哥这心里像刀剜了似的。这方圆几十里,谁不赞你好人品,又有两个听话的儿子。你这辈子不冤了,值了。不像我,养了个儿子十几岁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说了,你先走一步,哥过几年就来找你说话。你别嫌我啰嗦,我问你件事情,这事我们两兄弟私下也说过好多回了,今天我再问你一声,让谷雨这孩子给你做儿媳妇,你满意吗?”
振江心里一突,想说话,却不知道说什么,只好盯着父亲的眼睛。
司徒乔眼睛再次缓慢地眨了一下。
晌午时分,司徒乔闭上的眼睛不再睁开了。该回应的问题他都已经全部地回应了,这个世界上虽然还有许多的事情令他牵挂,可是他却已经无法再牵挂了。几天后,他在秋月和振江的泪水中,在一路锣鼓鞭炮的护送下,长久地睡在了紫云山上。
三
这个家突然只剩下了秋月和振江两个人了。吃晚饭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了明显的不习惯。对振江来说,突然间少了父亲在耳边的呼呼喝喝,少了他的唠唠叨叨,就像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这顿饭他吃得非常别扭,没吃几口就跑到村场上闷坐着发呆去了。秋月看着他壮壮实实的身影走出门去,心里也觉得格外堵,收拾好碗筷就回到自己房间,从枕头下摸出振南之前写来的几封信,一遍遍看完,也发起了呆。发了一会呆之后,就开始给振南写信,她必须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尽快告诉他。
第二天吃完早饭,秋月担着水桶准备去挑水。振江拦住她,伸手取了秋月肩上的扁担,挑着水桶大步走了。秋月心想,振江真的长大了,这样想着,心里又觉得踏实了些。
午饭的时候,振江突然说:“阿嫂,这些日子你太劳累了,不如你回娘家去歇一段时间吧。反正现在阿爸又不在了,地里又闲着,我自己在家里看着,照顾自己没问题的。你好长日子没回过家了。”
秋月想着很快就过年了,心里有些犹豫。
振江说:“没事,能行的,我反正闲着,也好趁这段时间把房子收拾一下。后面那幅墙要塌了,我过年前把它弄好。一过完年,我打算去外面找份工做。到时我再去接你回来。”
秋月看着他还带着些许稚气的脸,心想,这兄弟俩怎么长得一些儿也不像。振南高高挑挑,脸也是瘦瘦长长的,如果戴副眼镜,秀气得就像个书生了。振江个子比他哥矮一点,却壮实得像个石桩子,脸型也是方方正正的,就算给他戴十副眼镜,也还是像个武夫。她对着这个自己打心眼里疼爱的小叔子微微地笑了笑:“那行,我就回家住些日子。你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也确实惦记着自己的父母了,这段日子以来,她的心总悬在振南身上,她有一肚子的心事想跟阿爸阿妈说说。
叮嘱了振江一番,秋月便收拾了包袱回娘家。秋月家就在海边的一个小渔村里,离回龙村也就二十多里路。秋月满腹心事地走着,耳朵里便渐渐响起了“哗哗”的海浪声。她不知不觉中便走到了那片被红树林包围着的礁石之中。
站在礁石上,她看见浑浊的海水层层叠叠地往岸边涌,便觉得心里头也像这海浪一样荡来荡去,将自己整个身体都刷洗得空空荡荡的难受。这时日头已经贴近了身后的紫云山,将些光影铺在海面上,将海面染得花花的晃眼。这时风更大了,将海水碎碎地吹上了礁石,将她的鞋打湿了。她摇晃了一下,头又有些晕,忙躬下身子扶住身边的石头,几滴海水洒在了她的脸上、她的嘴里,咸咸的。她快步走下礁石,抹着脸上的水。一抹之下,才感觉自己眼里也已经湿漉漉的了。她慢慢地沿着海堤向家里走去,她的脑子里忽然想,清清冽冽、还带着些甘甜味道的檀江水为什么一进了这海里就变咸了?难道是因为在这海边上流眼泪的女人多了?
秋月走了,家里连个晃动的人影都没有了,振江一下子觉得自己成了这个家真正的主人了。他立即着手按照自己的计划修缮房子。他在这项工作中暂时忘记了父亲去世后带来的痛楚和失落,他在这项工作中感受着自己的成长。他没想到的是,秋月走了之后,他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服。他原来以为这是很简单的活,可没想到常会半天连火都点不着,而自己则被熏得眼泪直流。这时他开始感觉到秋月在家的好。
四
年三十那天,振江完成了他计划中的修缮房子的全部工程,他自己感觉到满意极了。这时他便想着要去叫秋月回来看,他渴望听到秋月的夸奖。可又想到今天是年三十,自己说过过完年才去接她的,便抑制住自己的冲动。这时村子里响起了过年的鞭炮声,振江突然想起过年的事,才意识到自己家里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挂鞭炮都没有。看来这个年只能凑合着过了。
正在犹豫着要不要烧火煮饭的时候,虚掩的门开了。振江一下蹦了起来:“阿嫂,你怎么回来了?”他的声音里掩饰不住惊喜。
秋月放下手中的大包小包,抹着额头的汗。她看着家里一点烟火气息都没有,心里就疼了:“你一个人在家里过年,我放心不下,你看你这哪像个过年的样子?冷冷清清的。”她嗔怪道。振江兴奋地领着她一一看了自己的工程。秋月夸奖着他,他的兴奋劲更足了。秋月想,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
过了年,振江就提出出外打工。虽然这两年来,振南从金山寄了不少钱回来,家里的环境比以前好了许多。可振江养家糊口、支撑起这个家庭的意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迅速膨胀。他急不可耐地想去挣钱来提供家用。
振江一去就是一年多,先是帮人盖房子,然后又去了县城的码头做搬运工。期间回来了三次,每次回来都会把工钱交给秋月。秋月说我帮你攒着,将来给你娶媳妇用。秋月也和他说起和谷雨订亲的事情,振江却很冷淡。有一次振江回来,秋月特意去将谷雨叫过来,振江却憋得脸红脖子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谷雨也不在意,照样振江阿哥长振江阿哥短地叫。
谷雨一走,秋月有点生气了,数落振江:“你怎么像个木头桩子似的?你就不会好好和谷雨说话?”
振江不吭声,秋月又说:“谷雨这么好的姑娘,打灯笼都难找。你别不当回事,到时后悔都来不及。”
振江脸胀得红红的:“阿嫂,我没说我不喜欢谷雨,可我就是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你知道,她嘴利索,我嘴笨。”
秋月笑了:“那行,等你下次回来,挑个日子先订了亲,等你哥回来再给你们办婚事。”
振江还想说什么,犹豫了一下,终是没有说。
临出门,秋月将两双新做的鞋塞到振江的包袱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振江,听说前些日子,有一伙土匪打了县城,有这事吗?”
振江说:“是的,现在听说我们檀城兴了好几帮土匪,专门劫有钱人家。上次打县城的就是一帮在紫云山后扎堆的土匪,领头的好像叫单眼豹子,劫了好几户大户人家呢。”
秋月说:“你得小心些,千万躲着点。”
振江笑道:“没事,我又不是有钱人,他们惹我干嘛?”
老榕树下,秋高气爽。女人们纳着鞋底、缝补着衣裳,男人们抽烟聊天,这些日子的话题都离不开土匪打县城的事。秋月则把谷雨拉到身边,嘀嘀咕咕低声和她讲振江的事,讲得谷雨心里一阵慌一阵喜。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不说不来事,一说就灵验了。正当回龙村的老老小小都在祈祷着别惹上土匪的时候,土匪来惹他们了。
五
这天晚上,月明星稀,大部分人都准备上床睡觉了。早睡早起,是村里人几百年来的习惯。一条黑影闪进了回龙村的小巷里,不时将手上抓着的香点着了,轻轻插在几户人家的家门口。不一会,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喧闹声突然从外而至,涌到了这檀江边上安静的小村落。顿时,村里鸡鸣犬吠,像煮开了一锅粥。所有的人都被惊醒了,有几个胆大的偷偷开门看了看,村场上黑压压的一群人,手里明晃晃的刀在夜色下闪着慑人的寒光。
土匪们径直冲向门口插着香的人家,村里几户家里有“金山客”的无一幸免被土匪撞开了门。
秋月也早早被惊醒了,她立即意识到土匪来劫村子了。她虽然心里害怕,但是脑子却是十分清醒。她迅速从司徒乔埋在床下的一个坛子里拿出一把大洋,用布包好放进衣柜,又将坛子埋好。刚做完这一切,门就被粗鲁地拍响了。她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几个彪形大汉手持钢刀就闯了进来。其中一个身穿一件黑色对襟短褂和一条黑色的粗棉布裤子,像一段烧焦的黑木炭竖在眼前,辫子盘在头顶,一只眼睛被一块黑布蒙着,另一只眼睛里透着阴鹫的光,年龄三十岁左右。秋月想,这人只怕就是振江讲的单眼豹子了。她心里一阵阵哆嗦。
单眼豹子半眯着唯一的那只眼睛,盯着秋月看了几眼,对身边的土匪说:“这家有人在金山,搜仔细点。”几个土匪立即翻箱倒柜搜起来,很快就将秋月藏在衣柜里的那包大洋搜了出来。单眼豹子却不动手,盯着秋月看,看得秋月心里一阵阵发慌。
单眼豹子忽然笑了,撇撇嘴:“想不到这破村子里还有这样的大美人,好,今天算是意外收获了。兄弟们,这家不抢了,把这个女人给我捎上,到我们寨子里享几天福去。”说完哈哈大笑走出门去。
不待秋月反应过来,一块布塞进了她嘴里,几个土匪按住她绑了个结实,抬起就走。秋月心里一慌,一阵哆嗦,晕了过去。
土匪像一阵风似地消失了,村子里的人涌出家门,聚到村场上。一清点,有八户人家被劫了。司徒祖铭家里几乎被洗劫一空。阿力婶藏在水缸下面的一坛大洋被抢了个精光,他儿子阿炳想去抢那钱罐子,却被土匪一刀砍在后背上,鲜血直淌。
司徒永堂见秋月被土匪绑架了,忙叫过来两个后生,吩咐他们:“你们俩赶快跑一趟县城,去码头上找到振江,让他赶快回来,一起想办法去赎秋月。记住,别让他一个人胡来,先把他叫回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