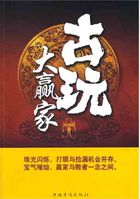一
司徒成林一直咬紧牙关忍受着冈崎正一的长刀在自己胸膛上划来划去,他看见自己的血从光滑、白皙的皮肤下慢慢地渗出来,像一串串红色的汗珠。他觉得这些红色的汗珠正一点一点地聚拢,最后会在自己的胸前汇聚成一簇红色的花景。他觉得这应该是一幅红梅迎春的图画。多么美,多么壮烈。想到这里,不知怎么,他的思路突然跳跃到那位已经香消玉殒的酷爱梅花的民国才女石评梅的身上。最近他正在读她的小说《匹马嘶风录》。他想起她在自己爱人的墓碑上刻下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那是多么悲壮而慷慨的爱情啊,那是何等的侠骨柔情啊!我司徒成林当此国难之际,愿以一腔热血唤醒沉睡的国人,换来后世之景仰,也不枉此生了。阿妈,我是真正的男人!阿琳,我保护不了你,那是过去的我,今日的司徒成林要成为保家卫国的血性男儿!这样想着,成林睁开紧闭的双眼,伸手轻轻地在自己血迹斑斑的胸前涂抹着,将一串串的血珠涂成一朵朵梅花的模样,嘴里竟然蹦出了跳跃的旋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冈崎正一和全村的村民们都不知道这个文弱书生为什么突然会唱起歌来,也不知道他在唱些什么。但是,冈崎正一已经觉得很不耐烦了。他不再理会这个怪异的年轻人,他看到他身后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和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紧紧搂着三个孩子,正惊恐地望着他们。冈崎正一朝那三个孩子轻轻地点了点,立即便有两名日本士兵冲上前去,将三个孩子夺了过来,将那个拄拐的老人一脚踹翻在地。
冈崎正一嘟哝了一句:“先杀一个。”话音一落,一把锋利的刺刀深深扎进了司徒成林两岁的小儿子肚子里。孩子哭都没来得及哭一声,就软软地瘫倒在了地上。
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尖叫和骚动。成林嘴里的旋律被叫声打断了。他这才从激情的畅想中回过神来,看清楚躺在地上的儿子。他的眼泪立即涌了出来。这时,他听到面前这位穿着笔挺的日本军服,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日本军官冷冷道:“我给你一分钟时间,接着就开始杀你的第二、第三个孩子,还有你的女人。”接着那个日本人抬起手腕,看着手表,嘴里开始数数。
司徒成林满腔的激情像突然遭遇了一场暴雨,所有悲壮的英雄主义的畅想立即荡然无存。他才知道自己的热血遇到冰冷的刀枪时,立即便会无法抵抗地被冷却。胸前那朵朵红梅很轻易就凋零了。泪眼模糊中,他看见自己的妻子扑在小儿子身上,也如小儿子一般一动不动。他还看见又一把亮得晃眼的刺刀在大儿子的肚子前比划着。两个孩子放声大哭,一声声地揪着他的心。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力地跌坐在地上:“放开我的孩子……那两个人藏在……那里。”他伸出手指指江边的那一丛灌木。他的眼泪将他胸前的梅花冲得凌乱模糊。
冈崎正一刚抬起手,那个跌坐在地上,还在喘着粗气的老人突然扯着嗓子大叫:“阿炯,发现你们了,快往江里跳。”一边喊着一边爬起来举着拐杖朝冈崎正一扑过去。冈崎正一拔刀一横,何成彪翻倒在地,肚子上血如泉涌。二十多个日本士兵叫嚣着往灌木丛方向扑去。
这时,村场上几十个声音齐齐大叫:“发现了,快往江里跳!”紧接着,灌木丛中一片乱动,接着传来了两声水响。
冈崎正一拔腿就往江边奔,却听到身后一阵骚乱。回头一看,一个须发皆白,光着膀子的瘦老头竟然端着一杆枪,挺着明晃晃的刺刀,嘴里骂骂咧咧,脚下跌跌撞撞地向自己冲过来。冈崎正一大吃一惊,也无暇多想,拔枪便射。老头子身中数枪,仍向前冲出几步,才一头栽倒在地上。原来司徒永堂见老伙计何成彪惨死,想着儿子跳到江里生死不知,司徒盛才和振江的小孙子又无端被杀,心里难受。他再也忍不住了,提起手里“大碌竹”就朝站在旁边的一个日本兵头上砸去,夺了他手里的枪,却不知道如何摆弄。便把心一横,端着刺刀就朝那个当官的日本仔冲去,心想扎死个日本当官的,比打死几个小兵强。毕竟年岁大了,年轻时候的身手使不出来了,还没冲到冈崎正一身边,就中弹倒地。
冈崎正一的枪一响,扑向灌木丛的日本兵都愣了一下。就这么缓一缓,跃入江里的两个人已经游到了江心。冈崎正一一挥手,一阵密集的枪响之后,江面上浮起一片血色涟漪,扩散开来,如江面上漂着的一片红浮萍。
二
残阳如血,流淌在高高的紫云山间,将满山的苍翠染成了一片橙红。几缕余晖穿林而来,散落在回龙村的村场上,如缝在地上的几块大补丁。而此刻在回龙村的村民心上,正有千百块补丁等待缝合。司徒成林已经彻底呆滞了,坐在地上,只知道默默流泪。他的妻子仍紧紧地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垂着头,像一枝已经枯干的莲蓬。何成彪仰天躺在他们身边,睁大双眼。肚子上喷出的血将他的衣服湿透了,他那张老树皮一般的脸上还挂着浑浊的泪水。在何成彪的头顶处,是司徒永堂的一只鞋,他在冲向那个日本军官时鞋掉了。他此刻躺在地上的姿势仍是一个学武之人的姿势。他的白头发、白胡子杂乱地竖着,包裹着他的脸显得很小。但是此刻他的嘴张得很大,仿佛还有一肚子的恶气要汹涌而出,又仿佛仍在破口大骂:“当年我砍了那么多洋鬼子,就不相信收拾不了你这个‘萝卜头’!”
到了端午节那天早上,沈雁行终于醒过来了。振江和秋月惦记着沈琳和华光的安全,便交代司徒常发小心照顾着沈雁行,两人便匆匆往家里赶。振江一直没有将县城里满大街在抓华光的事告诉秋月,免得她心里添堵,但是这两天来,他自己心里却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总觉得有一大堆蚂蚁在心尖尖上爬着似的。沈琳和华光是他现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亲人。他不敢想象如果他们俩出了事,自己将如何承受?
两人心急火燎往村里赶,还没进村,便听到“八音锣鼓”奏出的阵阵哀乐。“谁家死人了?”两人心里嘀咕。
进了村,远远便看见司徒盛才家素幛白绫布起了灵堂。两人都以为是司徒盛才他妈死了。走近了,才看清是司徒盛才的像。两人正在惊愕中,从灵堂后面钻出一个人来,正是住在他们家隔壁的司徒宁生。司徒宁生一见他俩,就带着哭腔叫道:“叔啊,婶啊,你们去了哪里呀?家里出大事了!”
何成彪的灵堂是乡亲们七手八脚帮着临时搭起来的。何成彪在国外打拼了大半辈子,随振南回到回龙村定居后,过了十多年安乐日子。他平时为人豪爽义气,心底里将回龙村当成自己的家乡,再加上手头有些积蓄,村里谁家有个急难,他总是慷慨相助,因此很得乡亲们敬重。在振江和秋月眼里,早已经视他如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成林的小儿子则是振江和秋月最宠的,才两岁多,长得圆头圆脑,非常可爱。两人一听这一老一小突遭横祸,心里就像被烧焦了一样灼痛。
振江在何成彪的棺木前刚跪下,突然想起一件事情,立即站起身来,粗着嗓子大吼道:“成林,你过来!”
成林一身孝衣,低着头走到父亲身边。他已经隐隐知道父亲要问什么了,单薄的身子微微颤抖。乡亲们也都被振江那一嗓子惊动了,怔怔地望着他。
“我问你,阿炯和陈少锋两位小兄弟现在在哪里?”振江瞪着儿子。成林垂着头,不敢开腔。振江更怒:“你哑巴了,说!”
成林头上大汗淋漓,支吾着。
振江一连追问了几遍。司徒宁生见成林被逼得脸色惨白,心里不忍,插话道:“叔,他俩跳到江里之后,日本人朝江里开枪,那枪声像炒豆子似的……他们八成已经……江面上都是血……”
振江一听,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只觉得一口气提不上来,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众人忙去扶他,又捶背,又捏脖子。振江一挥手,拂开众人,指着成林,却说不出话来。
众人都不知道如何安慰他。秋月含着眼泪,轻轻拍着他的后背:“他阿爸,你别这样……”
正伤感间,却听见屋后有个一身白衣的汉子大步奔来。他一边走,一边扯着嗓子大叫:“司徒成林,你这个千刀万剐的汉奸、软骨头、乌龟王八蛋!阿叔说过,谁出卖郑炯兄弟,我一定要捏死他……”来人正是司徒永堂的儿子司徒汉。他跳入江中后,仗着水性好,潜到对岸的葵林里藏了起来。待远远见到日本人撤出村子之后,又潜回家中,才知道不仅郑炯和陈少锋死了,连父亲也被日本人枪杀了。他心里又悲又怒,听说最后日本人逼着成林供出了郑、陈二人的藏身之地,又想着如果不是司徒成林说出了二人藏身之地,父亲也不会惨死,更是怒火满腔。他本来就是个急性子的人,二话没说就找上门来和司徒成林算账。
司徒宁生见状,想起司徒汉的话,忙奔过去想拦住司徒汉,却被司徒汉一把掀翻在地。原来乡亲们见到振江家一老一小惨死,非常可怜,便商议暂时别让振江知道是成林最后供出了郑、陈二人的下落,以免他难受。各家都知会了此事,单单漏了跳入江中的司徒汉。
三
司徒汉一见成林,便猛扑上去,掐住成林的脖子。众人慌忙七手八脚扯开司徒汉,将他按倒在地上。他嘴里仍是破口大骂。
振江这才知道郑、陈二人之死是因为儿子抗不住日本人的威逼。原本心里就悲伤难已,此时更是羞愧难当,像当街被人剥光了似的。他脸色铁青走入屋中。秋月跟着他进屋,却被他将门一扇。门重重地撞在秋月头上,撞得她眼冒金星。
紧接着,众人看见司徒振江大步走出屋来。手里抱着几块红漆木牌。他走到何成彪的棺木边。将手中的木牌一一摆好。随后,跪下身子,对着一排木牌磕起头来。他磕得很缓慢,像身上压着几百斤的巨石。他的头一俯一扬,头顶的白发在众人的眼前一跳一跳。众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都屏住呼吸看着他,连司徒汉也不闹了。
磕完头,他手撑着膝盖慢慢地站起身来,回头看着儿子:“成林,你过来,也跪下。”
成林面色惨白,抬头看了父亲一眼,心像要蹿出来似的。他看见父亲的眼睛通红,像两团烧旺的炭火。他心里害怕,挪着步子走到棺木前,双腿一软,扑倒在地上。
“成林,棺木里躺着你契爷爷。这几块都是我们家祖先的牌位。这是你伯父,这是你阿爷,这是你太爷……”振江一块一块地指着给成林看。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异常平静,甚至有些有气无力,“成林,你从小跟着你阿妈生活。你阿妈送你去读了很多书。可惜,这些书你都白读了,司徒家做人最重要的一本书你没读。”他指指蹲在地上的司徒汉,“你阿汉叔大字不识几个,但是,他却知晓这本书,就是司徒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骨气,你呀,白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呀。秋月,你害了孩子呀。”
秋月在旁边看着,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只是流眼泪。
“成林,别的道理阿爸不会讲。但是,阿爸知道,我们司徒家祖祖辈辈就认忠义二字。我司徒家族有祖训,你成亲的时候我对你说过。其中第一条就是报国忠君!”振江轻轻地摇摇头,眼泪又下来了,“成林,今日你已经酿成大错,违了这第一条祖训,阿爸也救你不得了。”
成林越听越害怕,这时忍不住大叫:“阿妈!”
话音未落,振江手一抬,一把短枪已经顶在了成林额头上。
全村人都大惊,秋月尖叫着扑上前去。
振江黑着脸大喝:“不准过来!”
秋月深知他的性子,不敢再往前扑,嘴里却苦苦哀求:“振江,他爸……你千万别……我们就这一个儿子……我求你了……”
振江却不理她,仍是盯着眼前那黑沉沉的棺木。嘴里像是在喃喃自语,又像是对儿子说话:“这回我们都错得厉害了。我们出卖了爱国义士,那我们就是汉奸,就是秦桧那样的人……成林呀,你护不住他们,阿爸不怪你。可你不能出卖他们,就是我司徒振江家断子绝孙,都不应该呀……算了,不说了,阿爸送你上路吧……”
秋月听着他的话,整个人像掉进了冰窟窿,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声嘶力竭地哭叫着:“司徒振江,你……你敢杀我的儿子,我……我和你拼命!”秋月性情一向柔顺斯文,和乡里乡亲从没红过脸。这时突然像发了疯似的,振江也不禁有些愣。
秋月拨开在旁边扶着她的乡亲,朝振江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去。她脸色苍白,嘴唇哆嗦:“司徒振江,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这个儿子,从他生下来,你关心过他多少?你教了他什么?《三字经》说,子不教,父之过。就算成林有错,都是你的错!这次日本人来,成林自己也死了儿子,你以为他不难受?你看看,那孩子才两岁多,就躺在那里。如果成林不说,日本人还会杀他的儿子,你司徒振江就真的要绝后了!”秋月抖抖索索地伸出手,解开成林的衣服,“你看看,看看成林胸口上的这些血印子,你数一数,日本人在这里划了那么多刀,成林都没有说。他已经算得上顶天立地的男人了,你还想他怎么样?”
振江看着成林胸口的血印,张张嘴,眼泪却流进嘴里,咸咸的,眼前一片模糊。就在这时,他看见站在面前的秋月身子往地上倒,忙伸手去扶她。谁知秋月却突然伸出双手,死死地拖住他持枪的那只手,嘴里大叫:“成林,快跑,别回家来!”
司徒宁生见状,也朝身边的两个年轻人一使眼色。几个人也扑上去,将振江按倒在地上。振江被他们牢牢按着,挣扎了几下,却哪里还动得了?他双目含泪,嘴里还在大声叫道:“司徒成林,你要敢跑,你、你……只要我死不了,一定要抓你回来,给两位义士陪葬!你们放开我!司徒成林!你这个软骨头!你跑不了!”
秋月喘着气,站直身子,恨恨地说:“司徒振江,你是个冷血动物!成林没你这样的父亲!我……我现在就和成林一家离开这里!你要杀成林,就先将我杀了!否则,我和你没完!”说完,一拉还在那里发愣的成林,“走,让他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发疯。”
振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匆匆走下山坡,走出村去,心里一片茫然。头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磕着,脸上、嘴里都是泥。
当天晚上,振江病倒了,连走几步路也觉得脚软。何成彪的丧事就由司徒宁生领着一帮后生张罗。第三天,华光和沈琳回来了。两人得知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都是悲伤不已。华光自小和何成彪感情就好,更是心里难受。两人又结伴上山去拜祭了一番。
休息了两天,振江觉得身体好些了,见到华光和沈琳回来了,心情也稍微释放了些。这时也顾不得再追究成林的事,便立即领着沈琳上山去看沈雁行。
沈雁行身上还像裹粽子一样缠着厚厚的纱布,不过,已经能够靠在床上吃东西了。父女相见,自然免不了一番悲喜。沈琳问起父亲受伤的原因,才知道在过去的半年里,父亲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种种凶险,如果不是振江相救,已经命丧黄泉。
原来,日本人在大亚湾登陆前夜,沈雁行随所在部队赶赴惠州阻击。结果抵抗了不到两天,部队就接到撤离的命令。这自然让沈雁行恼怒不已。在出发之前,他已经安排妻子田谷雨领着一双儿女随着司令部的一帮家属飞往重庆。他自己下决心随部队死守南粤大地。他认为这是一名军人的神圣使命。那愈来愈近的炮声让他亢奋。自从七年前从江西“剿共”回来之后,他便一直被闲置起来,远离了战场。这让他痛苦。一名职业军人听不到枪炮声,闻不到硝烟,就像一名骑手永远只能跟在马屁股后面走,没有机会在马背上驰骋一样。接下来的两天,他所在的部队在增城略作抵抗之后,又撤入了广州城内。他以为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死守广州,和广州共存亡。他为此专门写了一封慷慨悲壮的诀别信给谷雨,表示自己的决心。他在信里说:“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已决心将根深深地扎在这抵抗外侮的最前线。我便是这南国大地上的一株木棉,被风雨摧筋断骨,也要求得一刹那间红花满天的灿烂。”
他的这封信刚刚寄出,却又接到命令,让部队撤离广州,开赴粤北。这一道命令如一把刀插进了他的心头。他终于爆发了,见到当官的就发难骂娘。他的这种情绪引起了很多士兵的共鸣。特别是那些广东籍士兵,更是一路骂声。但是,骂归骂,他还是不得不跟着部队走。
不料,部队走到花县时,却突然遭到日本人袭击。一个团的队伍被冲得七零八落。沈雁行领着十多个粤籍士兵乱冲乱突,杀出包围。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聚在一片桑林之中,共同作出了一个决定,不再跟随大部队后撤了,学共产党的办法,回去和日本人打游击,死也要死在家乡的土地上。一路上,他们又收留了十多名被打散的士兵。就这样,他们打打藏藏,辗转到了檀城。之后,他们以天露山为依托,坚持和日军周旋了两个多月。
“这半年,我们最少杀掉了几十个日本仔,够本了。”沈雁行望着女儿,虚弱地笑笑。沈琳却看见父亲眼里闪动着泪光。
四
我最最亲爱的阿哥:
你好!
我不知道这封信还能否及时地到达你的手上。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的通信已经中断了,这封信我是通过加拿大的一个同学转寄过来的,可能在路上要耽误很长的时间。战争让一切正常的东西都可能变得不正常起来,包括对你的思念。从广东,我们的老家被日本人占了的那一刻起,我便变得格外地思念你和家乡的亲人们。我每天在三藩市郊那座贴满蚝壳的海滨教堂里为你们祈祷。
你现在怎么样?长成了什么样子?菱儿给我描述了好几次你的样子,我都觉得她在讲述一个陌生人。我想快点见到你,越快越好。记得小时候,我常趴在你的背上在唐人街的大街小巷里转悠。我们会在关帝庙前呆上大半天,看着那个驼背的叔叔炒米饼直流口水。前些时候,我又去了一趟那个地方,他还在那里炒米饼,不过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我回味着你将我背在背上的感觉,很温暖,很惬意。如果我们下次见面,我一定要你再背着我在唐人街上走。
菱儿和我们的小弟弟华强现在也都住在三藩市,他们都很好。华强已经一岁多了,跑起来摇摇晃晃的,像只可爱的小鸭子。看着他,像看着一缕在大地上跳动的阳光。我心里觉得多了一份踏实和希望,我看到阿爸的生命在这块曾经让他流血流泪的土地上延续。
今年是美国开国150周年,尽管战争的浓云此时正密布在亚洲和欧洲的上空,但是美国人似乎还打算好好庆祝一番。纽约世博会依然如期举行。美国人为了这一次所谓人类的盛会而排山填海,不惜巨资投入。他们似乎要证明,人类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在三藩市的唐人街,却连续两天举行了华人和亚洲国家侨民共同参加的集会。我和八金叔叔一家也都去参加了。大家表达着一个强烈的意见:在亚洲、在我们的祖国,正上演着人类最丑陋的、充满罪恶的一幕:侵略。你们在欢庆的歌唱时,侵略者的刺刀正扎进我们兄弟姐妹的胸膛,这就是人类的盛会吗?那天,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我想起你和振江叔叔。
振江叔叔和秋月阿妈都好吗?你留在家里照顾他们挺好的。虽然只是在很小的时候见过振江叔叔,虽然从来没有见过秋月阿妈,但是我已经无数次地听说过他们的故事,在我的心里,他们被塑造成充满浪漫和传奇色彩的人物。我有时甚至不敢相信,这么可敬可爱的人就是我的亲人吗?阿爸曾经在信里对我说,虽然振江叔叔没什么文化,日子也过得很穷苦,但是从做人的品格上来说,他是我们司徒家的骄傲。阿爸说他就像一座山,永远坦荡,永远不低头。阿爸是个很骄傲的人,能够让他彻底敬佩的人非常少。我想,等战争结束之后,我一定要回来和他们一起住上些日子。这些年一个人在美国,我太想和亲人们在一起了。对了,你问问振江叔叔,林德子叔叔和红荔阿姨在国内住了几年,期间是不是和振江叔叔闹了些什么不愉快的,为什么他们回美国后总躲着我?我听说他们从中国回来了,去找过他们两次,他们都避而不见。听说最近他们还举家搬到西雅图去了。真的很奇怪,要知道,以前他们一家一直当我是亲女儿一样。
因为不知道在战争中我们的通信还是否能够顺利抵达对方的手中。杜甫的诗写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何况这是一封越洋的家书。因此写起来,就不愿意搁笔,总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说。以前我和阿爸每隔几个月就通一次信,有时,上一封信还在路上,就又忍不住提起笔来了。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结婚了。我的丈夫也是一位华人。原本一直想等阿爸哪天回美国时替我们主持婚礼。但是……后来八金叔叔做主,说再不嫁,人家就不要你了。我说阿爸去世了,但是阿哥回来了,是不是等阿哥做主?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长兄当父。八金叔叔一听,就气哼哼的。他似乎对你还有些意见。但是你别怪他。他是真心真意对我们一家好。几年前,他听说你和你的亲生父亲在日本,竟然一声不吭就带着阿喜婶婶去日本找你。他就是希望我们一家能够早日团圆。阿爸去世后,他也变得脾气越来越坏了,动不动就喝醉酒,还经常动手打人。阿喜婶婶说,他只有在见到我的时候才会眉开眼笑。我知道,在他的心目中,阿爸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他常和我讲起与阿爸相识的过程,他说,他和阿爸完全是两种性子的人,最后却成了心里最亲的人。
说起阿爸,鼻子又忍不住酸酸的。你有时间,多去看看他。他去世的时候,一定是满心的委屈,满心的不甘。哪怕战争迟来几天,让他听一声那火车的长鸣也好。人生就是这样,希望越大,遗憾也越多。我不知道在家乡的土地上,还能否找到那条铁路的痕迹。战争结束后,我要沿着这条已经消失的路轨慢慢地走,用图纸将这条已经消失的铁路画下来,世世代代留下去。阿爸上次将秋月阿妈的父亲当年亲手绘制的那幅《檀城地图》寄给了我,叮嘱我要保存好,传下去。我总希望有一天在这幅图上添上阿爸的檀江铁路,让这幅图上留下阿爸的脚印。因为那是阿爸的心路。不写了,眼泪又忍不住下来了。
愿上天保佑我的祖国,我的家乡,我的亲人们!
代向振江叔叔和秋月阿妈问好,你也多保重!期待着战争后的相聚。
妹妹:依枝
华光读完信,蹲在地上发了半天呆,一只狗将他的鞋子叼出老远,害得他一阵猛追。他想着给妹妹回封信,但是他的中文水平远逊于依枝,写了几行,就写不下去了,只得搁了笔去找振江。
秋月护着成林离家已经十多天了,振江依然怒气未平。一连几天都划着船在江面上搜寻,希望打捞到郑炯和陈少锋的尸体,却一无所获。
华光劝他去将秋月接回来,振江身上湿漉漉的,坐在江岸的青石板上,粗声粗气地骂道:“接什么接!接她的命!”郑炯与陈少锋之死,而且因为自己的儿子而死,是他一生经历的最伤心,也是最感到耻辱的事情。华光无声地望着振江,心里也是一阵阵难受。他不知道自己在成林的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扛得住。两人在江边坐了一会,觉得无聊,便准备结伴上山去看沈雁行。这些日子,沈琳回广州去了,山上只剩下司徒常发在照顾着沈雁行。
正要走,却见司徒汉与司徒宁生高声争辩着走过来。司徒汉冲着振江粗声粗气道:“振江哥,你是在外面闯过的人,全村人里我就服你一个,你说句话。这回日本仔来,杀了我阿爸和成彪叔,还有瘸子和你的小孙子,这仇是结下了。要不找个机会报仇,我们都成了乌龟王八蛋。我司徒汉咽不下这口气!”
振江看着他那张黑炭一样的脸:“你打算怎么样?”
司徒汉哼了一声:“还用说,拉队伍,和这帮混蛋干!宁生说去投军,参加部队打日本仔。我看,不如我们自己弄起一支队伍来。要打,我们就在家门口和他们打!我打听过了,在周边四乡,有好几条村都拉起了队伍,人人手里都有枪,天天秘密训练。”
当天下午,司徒汉和司徒宁生就联络了十多个胆子大的后生,聚在南楼里开会。那天,大多数人都目睹了司徒永堂等人之死,上了年纪的心里担心害怕,但年轻人心里都憋了一肚子气。
经过几回商议,大家都同意成立回龙村村民护卫队,推举振江做队长,司徒汉做副队长,组织训练。报名参加的有二十多个人。按照司徒汉的意见,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就是拉出去打日本人。但是他的意见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认为这支队伍就是用于保护乡亲,保护家园,不应该去向日本人挑衅。大家为此事争吵得很厉害,司徒汉更是拍着桌子骂娘。后来还是振江发话,说不管将来去不去打日本人,首先自己要练好兵,要会舞刀弄枪,将来才能派得上用场。对于这一条,大家都没什么异议。
第二天早上,全体队员就开始安排训练。训练的地方选在村后山林里的一处空地。司徒汉负责训练大家舞刀和拳脚功夫。振江和华光负责教大家打枪。可全村只有振江有一长一短两支枪,只能一个一个地教。华光弄了些树枝当枪,教大家练瞄准。振江心里有些发愁,大家手上都没枪。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人,这支队伍一点用处都没有。过了两天,问题又多起来了。训练的时候不是这个请假,就是那个早退。再加上司徒汉性子急,动不动就骂人、打人,队员们忍不住就和他吵。振江忙着做和事佬,也觉得心里烦。
这天,振江心里惦记着沈雁行,便交代司徒汉和华光继续领着大家训练,自己上山去看望沈雁行。沈雁行伤好得差不多了,可以扶着拐杖自己行走了。振江愁眉苦脸地和他说起村里成立了自卫队的事情,自己不知道怎么训练。沈雁行是个带兵上了瘾的人,一听这事,立即接口道:“这还不简单,我去帮你训练呀。”
振江一听,眼前一亮。对呀,沈雁行带了半辈子兵,训练二十来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
司徒常发在一旁听了,也很兴奋,表示自己也愿意加入回龙村的自卫队:“反正大家都是司徒家的,只要是打日本人就行。”
沈雁行当了教官,情况立即为之改观。半个月下来,这支二十多个人的队伍和以前变得完全不同了。除了穿着乱七八糟,手里没枪之外,队员们的行动、言语都颇有些正规军的味道。这半个月里,振江拿出以前阿哥留下的一点积蓄,找人打了一批砍刀,每人发了一把。然后又和沈雁行一起琢磨出一套简单实用的刀法教给大家。练了些日子之后,沈雁行端着枪和队员们拼刺刀的时候,每个队员都能够舞着刀抵挡一阵子。
五
这段时间,沈琳回来了一趟。见到父亲伤势痊愈了,沈琳也放心了。这些年父女俩聚少离多,原本有许多话说。可不知为什么,两人一坐下,便开始争吵,令振江和华光都非常不安。为此事,以前谷雨没少生沈雁行的气,说他是屎炕里的石头——又硬又臭。明明心里最宠这个女儿,可就喜欢和她吵,在她面前摆架子。谷雨不懂父女俩的根本分歧所在。自从中学的历史老师被国民党杀害以后,沈琳一看见国民党那身军服就反感,在父亲面前经常会放肆地发泄自己的不满。而在沈雁行眼中,自己身上那套军服和那枚“青天白日”的徽章是那么神圣,是他人生理想和追求的归宿。自然,两人一碰面就会吵起来。沈琳离家几年,后来又回到了广州。沈雁行察言观色,知道她加入了共产党,心里更是异常难受,试着和女儿谈了两次,都碰了软钉子。这次他死里逃生,再见到女儿,心里既感慨,又酸楚。今天的沈琳显然已经完全不再是以前那个承欢膝下,言笑晏晏的小公主了。她的脸晒得黑黑的,剪着干练的短发,笑容里多了几分沧桑和成熟,神情里透着一种做大事的忙碌和疲倦。他知道,这个女儿,当年自己从枪林弹雨中抱回来的这个女儿在逐渐离他远去。他已经无法将她留住了。
这一次的争吵依然缘于两人不同的信仰。起因是沈琳听说回龙村成立了村民自卫队,父亲担任了自卫队的教官,便突然提出,何不组织这支队伍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檀江抗日大队,共同去打日本人。
沈琳话还没说完,沈雁行就暴跳如雷:“我沈雁行的女儿,堂堂一个国军中校的女儿已经走上了一条背叛党国的道路,造起了国家的反。今天要是我同意你将我一手训练出来的这支队伍又拉进共产党,那我就更成了党国的罪人!”
沈琳没想到父亲反应如此强烈,愣了好一会,脸涨得通红。半晌才冷冷地说:“阿爸,沈中校,这么激动干什么?不错,从小你就拿你们那一套教育我,我也一直以为你们那一套就是国家的理想,民族的希望。但是,事实怎么样?你难道还没看明白吗?你有你的道路,我追求我的信仰。你矢志不移,我也今生无悔,就不必多说了。将来我们两党如何共存,如何发展,那是大人物们的事情。我们也犯不着为此伤了父女感情……”说着,她眼泪夺眶而出。
沈雁行别着头,望着屋顶的燕子窠,一动不动。
振江和华光一直在门口提心吊胆地听着他们父女俩争吵。这时,见沈琳出来,眼里还含着泪,振江忙站起身:“琳儿……”
沈琳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没事,振江阿爸,您放心好了。我们两父女吵了十几年了。没事的,他不会真生我的气。我知道他心里是最疼我的。”她轻挽着振江的手臂,走在门前的山坡上,“振江阿爸,去将秋月阿妈接回来吧,您别生成林哥的气了。我了解他的性格,他原本就懦弱,以前总被我欺负。这次已经是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担当了,他能够如此,已经不容易了。”
振江摇摇头:“琳儿,你别替他说话,我要是饶了他,司徒家列祖列宗饶不了我。将来见了他们,我抬不起头。”
沈琳望着他那张如老树皮一般的脸:“阿爸,成林哥也是个人,也是个父亲。他眼睁睁看着儿子惨死,他怎么扛得住呀?这个世界能够当英雄的只有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都怕死,怕失去亲人,失去财产。您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您那样。”她凝望着宽阔的江面,“其实,我也怕死,每天这样在刀尖上过日子,我也怕。最害怕的是哪天日本人将我抓了,羞辱我,将我摧残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比死更可怕。我有时也想,如果哪天我碰到了成林哥上次这种情况,日本人也用我的孩子的生命,我的亲人的生命来威胁我,我又能不能扛得住呢?我也不知道……”
振江道:“你不同,你是女人……”
沈琳一笑:“好,不说这些了。”她朝屋里努努嘴,“您劝劝我那个阿爸,让他到重庆去,千万别让他在这里发疯。他打仗上瘾,要是硬拉着你们这二十多个人的队伍和日本人碰,会害了大家的,记住了。”
振江迟疑地点点头,他忽然意识到沈琳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他们将来必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两人说了一会话,沈琳执意要走,振江便将华光叫过来送送她。他是有意想撮合一下他们俩。
望着两个年轻人并排走下开满野菊的山坡,振江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一阵秋风扫过,没有半点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