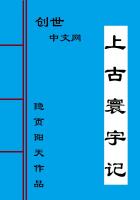“你确定这东西有用?”
“这么沉还能没用,你拿着试试?”
干瘦少年从雀斑少年手里接过铁块,想用单手称一称分量,结果超出了预计,根本抛不动。
他为了掩饰尴尬只好阴笑道:“行!就这个了。”
雀斑少年也说:“就不信他不疼!”
两人随即来到一处巷角,探出头找到了那个走在街边的目标。
那是一个身高六尺有余的高个少年,只是脸上的稚气与他的身高并不相称,总给人一副纯净懵懂的感觉。少年身穿粗麻布衣,头发也用麻巾随意扎成一条马尾,他微垂着眼帘,手上提着一壶酒,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
雀斑少年候在转角处,等到目标的脚步声临到极近处,忽然壮起胆气一喝:“就是现在!”
话音刚落,干瘦少年就用尽双手力气,将铁块砸了过去!
沉重的铁块划出一阵低沉啸音,然后砸在了高个少年的脚上。
没有惊呼,没有疼痛。
铁块像打在了棉花里,稍稍陷进去一点,然后又从那只脚面上滑落,朝一旁赶上几步想要来补一脚的干瘦少年滚去,正好将他狠狠绊倒。
恍若无事的被砸者轻咦了一声:“阿贾你干嘛趴在地上,是不是摔倒了?王二麻子,你怎么不扶扶他。”
王二麻子已经惊呆了,被对方扶起来的阿贾也没有什么写在脸上的感激之情,而是一脸恐惧地看着他。
“怪物。”王二麻子怔怔说道。
阿贾看看对方的脚,又看看自己仅是被绊到就肿起的脚上的红包,像是傻了般说道:“怜生是个怪物。”
念叨着怪物的两个少年仿佛忽然惊醒,飞也似地逃离了面前名叫怜生的少年,只是那声“怪物”还巷深处不断盘旋着,无比刺耳。
怜生挠了挠头,有些无奈,忽然对着他们的背影喊道:“对了,阿贾,你娘还叫我喊你回家吃饭呢!”
看着那两个背影的窘迫样子,怜生不知为何开心了一些,眼帘也拉开了一点。他提着酒壶,轻快的步子走出了镇子,回到了后山岭的自家草屋中,然后在进门的时候又恍然沉重了几分。
破旧草屋内的陈设十分简陋,外头是一张凹痕遍布桌沿的圆桌,侧堂的香案倒是干净的很,最里头是张木板床,床脚放着一张矮脚桌。
床上有一个人,老人,不知是睡是醒。
怜生不知搬来什么东西放在床畔,好让自己坐下,又将那壶酒放在矮脚桌上看着,默想这壶又能喝多久?
他转头看向床头老人的脸色,心中黯然。
恐怕没有多久了。
……
……
这天,床上的人醒了。
那是怜生的爷爷,穿着一身脱了毛的敞胸破袄子,长发杂乱而随意的散在席枕上,脸色十分的苍白破败。
怜生看到醒来的老人喉头一动,赶紧端起碗凑到他嘴边,他知道若是慢上一点,老头子又要扯着已经沙哑的嗓子开骂了。
老人先是拿鼻子嗅嗅,然后用微不可察的嗓音问道:“……就这么些?”
破碗不大,里面的酒水更是只有碗底浅浅一层,倾斜之下,晃荡出些许光泽。
怜生挠了挠后脑勺,“上次去镇上打的秋白酒,就剩这么点了。将就一下,反正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其实老人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虽说春寒料峭,饮酒暖身。可像他这样每天日出饮三升,醉卧一昼,日落饮四升,梦死一夜的日子总归是极伤身子的。而且他的脾气又极差,因少酒而动怒伤肝的例子不少。
不过话一出口,知晓爷爷脾气的少年立时低下头来准备挨骂。
今天老人似乎转了性,他只是看了一眼少年,然后默默地含住碗沿将那半碗秋白饮尽,等到面颊上升起些许红意,才依依不舍的松开。
怜生将破碗放回桌上,轻轻地叹了口气。
老人从前并不如何饮酒,若是要喝,也只是饮上几蛊奶奶亲自做的果酿。因为从小到大,家里都是奶奶最大,他和自己向来是以奶奶马首是瞻,奶奶不让喝外头那些酒家的酿造,他自然是一滴也不敢沾的。
那个阳光普照的清冷午后,自己亲眼看着奶奶眼中的光泽一点点消失,直到最后一刻奶奶握住自己和爷爷的手依然是温暖又温柔。等那只手也滑落后,本以为早算是一介男子汉的怜生终于没忍住,哭得泣不成声。
爷爷更是夸张,直接在地上扯着嗓子打起滚来,先是呜咽后是叫嚎,继而不知从哪里拿出藏了不知多少年的酒坛子。
奶奶走了,所以爷爷开始狂饮。
饮时泪流,醉后打拳,精疲力尽时便往地上一躺,在梦中呜诉。
怜生不得不自己做主将奶奶的后事办了,然后又不得不照顾自暴自弃后生活一片狼藉的爷爷。
可惜不论是烧火做饭还是务农打猎,年少的他都只跟奶奶爷爷学了一半。
特别是打猎,从去年起这山里的虎兽精怪便像是学聪明了,只要他一进山,就像是老远就能闻到他似的,远远的便发了疯往深山里躲,使得他常常一无所无获。
他去求教爷爷,却只得来他一句不满的“笨蛋”。实在是有一次太久没有猎物,家里没钱买酒,菜里又没肉的时候,后者才“大发慈悲”地指点到,“你打猎只学会了蛮横的打,却没有学会巧妙的猎”。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爷爷你还是没说怎么才能抓到他们啊。”
斗胆顶嘴的怜生不出意料地被爷爷赏了一顿脑瓜子。
他的记性确实不好,不像爷爷是个老人精,少买半斤酒的事儿都能记着心里,时不时用来做教训他的话头儿。
而且让他有点惭愧的是,匆匆三年,他竟已经快忘了奶奶的模样,除了那只温暖的手掌之外,唯一还算得上印象深刻的便是奶奶手艺菜色的滋味了。
这和相思酗酒成疾的爷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他一直没有怨言地照顾着爷爷,任劳任骂,在所不辞。
对于爷爷是否也有那么一天,他早有心理准备,特别是无论如何也劝不动他的酗酒后,他连真正的后事准备都做好了。对于这一点,老人自己都没什么忌讳。
爷孙两沉默着,怜生又将那只破碗拿到手摩莎着,似是在犹豫着怎么开口。
老人今天的脾气出奇的好,先开口道:“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怜生点点头,微张的眼帘垂得更低,“爷爷,你什么时候走。”
怜生口中的“走”自然不是普通的下床走走。
老人沉吟了良久,然后无半点流连道:“待会儿吧。”
待会儿吧。
待会走吧,或者说待会就死吧。
老人意会且简洁地给了回答。
怜生有点吃惊,更有点伤心,脸上满是黯然的神色。
他只好将碗重新放回到桌上,又正了正坐姿,“柴草都在草棚子里备好了,热水我待会就去烧……您还有什么话,现在赶紧说吧。”
听到孙子如此认真地说着对自己后事的处理,老人竟觉得有点好笑,他偏头朝厅堂里望去,他的老伴,怜生奶奶的灵位正立在香案上,香案底下便是她的骨灰瓮。
灵牌是怜生托人刻的,木料是南疆的香灰古藤;骨灰瓮是怜生找人制的,其实不是陶器,也是用香灰古藤做的木瓮。
而奶奶的瓮一直没有下葬,便是怜生知道要等爷爷。
老伴生前可没嘱咐后事如何如何,但老人知道,怜生做的是最合她意的。这孩子虽然记性不好,看起来也不灵光,却总能在懵懵懂懂中做最正确的事。
老人难得生出了对他的宽慰之情,道:
“怜生……我走之后,把我装在那酒坛子里……而且,一定要和奶奶葬在一起!”
“酒坛子也早就准备好了,爷爷。”怜生语带悲伤道,“咯,一直在我屁股下面坐着呢。”
“……”
“啪!”
……
……
怜生不知道自己又做错了什么,只是看起来已经老大宽慰的爷爷突然就豁出半条命来打了自己一脑瓜子。
话说自己总挠后脑勺,而且常被人叫“傻孩子”,是不是因为给爷爷揍出毛病来了,怜生看着渐渐安静下去的爷爷,有些不着边境地想着。
不只是奶奶,去镇上的时候,酒家的老板娘,皮草行的商大叔也总喜欢叫自己“傻孩子”,他总觉得自己应该不算真的傻,只是懒得去思考一些东西,长这么大总是直来直往的按直觉做事,好像也没吃什么亏。
就这么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又握住了爷爷的手。
真的好粗糙啊,十岁后就再没认真地握过这只粗糙的大手了。
真的好冰凉啊,爷爷的手何时也这么冷的陌生了。
怜生觉得眼眶有点湿。
正当他想抹一抹的时候,手中握住的手忽然略显不快地挥动了一下,“小子,还是把果酿酒拿出来喝吧。呃,有点冷。“
这是回光返照吗?怜生想。
很快他便知道自己错了,继而感到很委屈,像是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悲伤情绪变成了镇子上旺财的狗粮。
奶奶的果酿酒不知用什么果子酿的,味道很苦,即使后味有些回甘,还是难称佳酿,在怜生看来,确实是比镇子上的秋白差远了,难怪爷爷不喜欢喝。
不过此时床榻上的爷爷再如何边饮边哼哼着这酒如何难喝,老太婆你的破手艺等等,怜生也无法像平时那样违心地附和几句。
……就这样一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
怜生一边生怕爷爷哪天嗝屁的神不知鬼不觉,不敢稍稍远离,一边却很无奈地看着爷爷苟延残喘地在鬼门关前耍酒疯。
诸如“我待会就走。”的话说了无数遍。
然后就会补充上“贼老天,老子不想死!”之类的肺腑之言。
偶尔会有“死亡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高墙。”这样发人深省的名句出现。
整体上仍然会按时用胡话吩咐着怜生:“我饿了,上酒。”
……
……
“爷爷,如果死亡是一堵墙,你现在是不是卡在墙根儿了啊。”怜生的脸色有点发苦。
“闭嘴!”爷爷怒道,“上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