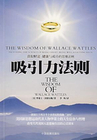2.前、后赤壁賦
狂草书。纸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内容是宋代苏轼的两篇散文。据考证,此卷为祝晚年杰作,千古绝唱之文,经生华之笔,构成变化万状的“图”堪称“双绝”精品。此卷下笔变化丰富,行笔沉着痛快,信手而作,随意而行。正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所说,祝允明草书“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结体上也大小相间,修长合度,引领管带,疏密成趣:纵观全卷,神采似行云流水,飞动自然,形迹如行立坐卧,意态朴素。
四、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唐寅以绘画最为擅长,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明代四大家,又称“吴门四家”。著有《六如居士集》。唐寅书法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頫,此幅更见受李北海影响,俊逸挺秀,妩媚多姿·行笔圆熟而洒脱,唯笔力稍弱,钩挑牵丝绵软,结构亦略趋松散。
其代表作品是行书七律诗轴。
行书七律诗轴:纸本,高146.5厘米,宽36.2厘米,共四行,释文是:“龙头独对五千文,鼠迹今眠半榻尘。万点落花都是恨,满杯明月即忘贫。香灯不起维摩病,樱笋消除谷雨春。镜里自看成大笑,一番傀儡下场人,漫兴一律,晋昌唐寅书。”
五、王宠
王宠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子、雅宜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王宠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山水,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很高,而尤以书名噪一时,为明代中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楷书初学處世南、智永,行书师法王献之,到了晚年形成了自己风格,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他是继文征明之后的著名书家。
其代表作品有:
滕王阁序:小楷。疏朗空灵,皆不与时人同。极为疏淡恬静圆润虚灵,有晋人遗意。
送友生游茅山诗:草书。疏朗萧散,俯仰多姿,饶有情趣,不失为高格调的佳作。
六、张瑞图
张瑞图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官至大学士,善画山水,草书气魄宏大,笔势雄伟。清代秦祖永说:“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桐阴论画》)《评书帖》云:“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人神,自是不朽。”
其代表作品是:后赤壁陚
后赤壁赋:行草。该作能把横直笔画密集在一起,纵横牵掣,大折大翻,给人以极少使用圆转用笔的印象。在章法上,他依靠点画的疏密来体现字的节奏感,由于翻折的运用,横画得以突出,加上其行距拉开,形成字紧行疏的特殊行款,黑白对比十分鲜明,与王宠、董其昌的清疏典雅风格不同,大有咄咄逼人之势。
七、宋克
宋克字仲温,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号南宫生,洪武初年任凤翔府同知,博涉书史,喜欢走马击剑。《明史·文苑传》称他“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杨慎评他的真、行书在明代应数第一。宋克直承赵孟頫,他所写的《李白行路难诗》笔墨精妙,风度翩翩。楷书有钟、王法度,但是过于流丽圆熟,当时就有人说:“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詹氏小辨》)
其主要作品有:唐宋诗卷、急就章。
唐宋诗卷:今草。是他三十四岁的早期作品,杂有章草的笔意,锋芒毕露而精神外耀,然而也因此遭来“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卞”之议。不过从每个书法家都应该追求自己的个性这一角度出发,这些贬词恰恰说明宋克的草书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而所非之处也正是宋克学古能化的明证。
急就章:草书。是他四十岁时临皇象的得意之作,但与皇象的《急就章》又“貌合神离”,给人活泼清新热情奔放的感觉,笔画粗细变化强烈,较之赵孟頫写的《急就章》更为生动精彩,富于感染力。
清代书法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覊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一、清代早期书法
自明末以来,董其昌的书法被认为是二王嫡派,多受推崇。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固然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你学来我学去,日子久了,董书被演绎得精巧妩媚、局狭寒俭,令人生厌。即在明末,一些有识见的书家如黄道周、倪元路便想跳出藩篱,不只走二王、董其昌的老路子。
到了清初,康熙帝也崇尚董其昌,董书的身价一下子又高了许多,学董之风依然盛行。著名的书家有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等,而叫朝的遗民,却不随从学董的风尚。他们在继承明季书风的基础上,拓1疼了学习二王书法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离渔等,河南孟津人,曾经宫至明朝的礼部尚书,后来却投靠清廷,人品遂为人不齿。但王铎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尺幅都比较大,起宅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像一件奔腾壮阔、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我们就能发现,王铎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铎对嘴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第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傅山(1606~1684),原名妯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阳曲(说太原)人,他的草书以气势胜,恢宏壮美,宕逸浑脱。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江西鹵吕人。他的经历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书法学董其禺,秀逸潇洒,晚年用笔圆劲,书写速度较慢,掺入了禅家的虚静境界和超脱梢神,于沉雄浑沦中寓郞勃傲然之气。他的书法尤其寄寓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王朝的郁愤。
针讨当时又甜又熟的书风,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美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以力矫时弊。他振聋发聩的吶喊刺激了陈袭日久的书法审美定势,为后来碑学的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极其有力的支持。
整个来肴,清初的书法是明季的延续,承接了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帖学传统,故可称帖学期此期有书名者还有郑簋(1622~1693)、宋曹(17世纪)、王澍(1668~1743)、沈荃(1624~1684〉、汪士錠(1658~1723)、等。其中郑簠的隶朽很有特色,横画的波挑很显眼,秀丽多姿宋曹的草书在当时很有名,但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趋于简单。
宋曹(1620~1701)字彬臣,号射陵,自号耕海潜夫。大纵湖北宋状(今属盐都县)人,其著作传世的有《书法约文》《草书千字文》《杜诗解》、《会秋堂诗文集》等。
宋曹曾人明朝的“中书舍人”,明亡之后,即隐居盐城南门外的汤村,筑“蔬坪园”,借口供养老母,几次拒绝出任清朝官吏。清康熙元年(1662),下诏举他为“山林隐逸”,他以母老固辞。59岁时,清政府又以纂修明时,征举海内明儒,要举他为博学鸿词,他仍坚持不赴。一个曾是明朝官员新乐侯刘文炳的弟弟刘文召,在明亡之后,整天漂泊江湖。他就劝慰要奋发应回故乡去做事,他在心中写道:游山半载不如归,到处骊歌事事违,纵有绨袍何足恋,莫将落魄与人看。
可见他崇尚气节的可贵。后来,两江总督于成龙特地迎请他到南京,纂修《江南通志》,他处于事业考虑,勉强应命,但完成后,坚持不列自己的姓名。晚年,他仍过着隐居的生活,以吟诗写字自娱。诗风以杜甫自诩,书必杜诗,以表示对清朝的不满。康熙四十年(1701),病故与“蔬坪园”,终年82岁。
二、清代中期书法
康熙帝崇尚薰其昌,乾隆帝推举赵孟頫,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作为二王一路最重要继承者的赵、薰,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渐渐走向平庸和刻板。而这种诠释又成为馆阁体的主要依托。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整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宫样书体,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是都没有达到像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
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溢趣味和馆阁体的板刻僵化,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在朝书家以刘墉、翁方纲为代表,他们科举出身受过馆阁体的“洗礼”,因此可称是从馆阁体内部杀将出来的。他们倡导对唐法的回归,反对光洁、方整的馆阁流弊。在野书家以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为代表,他们从汉代碑刻隶书中吸取营养,力图摆脱时风。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他的书法以行书著称,用笔浓厚,而内含骨力。人称“浓墨宰相”。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他的行书得力于董其昌、米芾,运笔柔润意蕴婉美喜用淡墨,人称“淡墨探花”。他们两人与翁方纲(1733~1818)、梁同书(1723~1815)并称为“清四家”。此时的帖学名家还有永理(1752~1823)、铁保(1752~1824)、钱灃(1740~1795)等。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郑變(1693-1766)、李輝(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年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郑變的书法揉多种书体于一炉,看似歪七扭八,毫无章法,但却有奇肆之气。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纳天下之书于一格”(启功语)。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一方面笼络汉族官僚地主,网罗汉族宿儒学士,一方面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義、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濟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