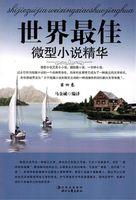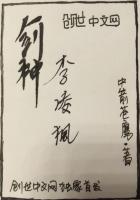一
日本鬼子第二次入侵福清县,占据了不满八个月又撤退了。虽然在夜间,军舰上的探照灯仍然不时地划破这片沿海的丘陵地上空,继续骚扰平民百姓。但在白天,那恶魔般俯冲式的轰炸机已少见了,反而是不必拉警报的飞机,三架、六架、九架,成阵、成队,在高高的云端,自西向东飞去。不看报纸的福清哥们也知道,那是同盟军的飞机,无不拍手叫好:“好呀!狠狠地炸,叫日本仔也尝尝炸弹的味道!”
受尽苦难的人们,要出口气了。他们期待着胜利而且充满信心。最兴奋的莫过于那些从福州市流亡到渔溪的艺人。唱戏的、说评话的,虽然此刻他们仍挑着小担或蹲在街边叫卖,但回到福州城的第一件事已拟订:“到水部温泉,在‘汤池’里泡他半天,再叫一壶茉莉花茶,躺在竹椅上慢慢品尝。嗨!那我就是神仙啦!”
“不要忘了,出了水部,就近到东街‘四海春’吃一碗米粉肉!”另有人补充道。这些满身爬着虱子的流亡汉们,说得唾沫四溅。
阿海一家也为胜利快要到来感到高兴,但不及其他流亡者那么兴奋、雀跃。他们并无搬回海口或龙田的意愿。渔溪这地方,虽然不是他们三个大人的摇篮地,祖宗的神主牌都不在这里。但这里有林府、曾家亲密来往,跟左邻右舍也相处得十分和睦了,又开着一家生意兴旺的“龙海之家”,“哪儿去找这么好的福地?”美玉母亲常这么说。当然喽,胜利了,他们也有具体的收益:那就是不会再有紧急警报拉响时,食客跑了且“忘了”回来付薯粉钱的事。
胜利前夕,渔溪镇像一锅快煮熟的番薯粥,社会活动空前热闹。说实在点,论抗战贡献,渔溪在福清五镇中,可能是倒数第一,但论三青团与国民党争夺胜利果实的激烈程度,可评个正数第一。因为死人的事也发生了。
为扩充实力,家在乡间的国民党镇党部主事们,把放牛娃与大财主都拉来做党员。林孝祖很热心,他把三兄弟及所有长工的名字都写上。虽然,林继祖毫无兴趣,从不参加什么会议与活动,但他的名字显赫地列在前头“示威”,让县党部书记长印象深刻。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干们,都是店头老板。他们把街上的众生,小至十二三岁的剃头店拉风扇的学徒,老到七八十岁的杂货店老板,统统拉入当青年团员。
阿海没有兴趣入党入团,他认为当年12个人结拜兄弟,况且各怀鬼胎,这么多人结义,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阿海还想到:我在街上加入青年团,岂不是跟岳父、岳叔他们国民党作死对头?单凭这一点,那也是万万不可做的事。但全街都青年团了,就缺这个牛田哥,于是三番五次地不断有人来“收服”。阿海被纠缠得受不了,想用钱应付,因此无奈地对来人说:“我名字不加入,也就是说,不参加活动,但每次‘乐捐’我出双份钱,总可以了吧!”
“这样很好!很好!你忙,我知道,以后开会你不必来,我替你报个‘有’就是了。”他不听阿海再说什么就走了。这样,阿海就成了三青团双料“骨干”分子。但登记在册的名字是“牛田哥”不是正名“王阿海”。不是他自己报的名嘛!
什么事都要出“双料费”,三天两头地有人来收钱,阿海感到莫名其妙的烦恼。他跟曾殿臣对酌时叹道:“胜利、胜利,这样胜利了岂不更麻烦!”
曾老赶紧作阻止的手势道:“嘘!此话传出门外,你就变做汉奸了!”他呷了口酒继续说:“我住在街后,也算街上人,照他们的说法,老夫也应加入青年团!可是我靠给人家主礼、主祭过日子,那林、陈、郑、郭乡间国民党,都是大户人家呀!不怕你笑话,他们是我的饭碗、衣食父母啊,得罪不得。”
“街上人逼你老人家了?”阿海关切地问道。
“怎么说好呢?他们说:‘你不加入青年团,就是要加入国民党与我们作对。要不然,难道你要加入共产党?’”
“他们要给你扣红帽子!”
“这是用赶鸭子上架,赶牛进屠场的话来吓唬我。”
“那你怎么解脱?”阿海用了南少林术语。
“我说,七十几岁的人了,入青年团不成笑话?可是他们说,杂货店老板快八十了,比你还老呢!”
“那你无路可逃了?”
“有!”老头子再呷了一口酒,神秘地笑着说:“我告诉他:孙连长说,蒋委员长没有叫七八十岁老人参加青年团!因此,我怕得罪委员长,将来日子难过,还是请你饶了我吧!”
“你真问过孙连长?”
“还用得着问吗?”
“万一他去查问连长呢?”
“他不敢!我早就注意到,这位王先生跟什么芝麻绿豆官都亲密,却不敢接近孙连长。”
“那为什么?”
“全渔溪人都知道他是蒋委员长的学生,那大概是他自报家门……”
“啊,我明白了,孙是黄埔军校的真货。”阿海醒悟道,并奉承了一句,“姜是你老的辣!”
曾老听了阿海的称赞,得意地呵呵大笑。
“那他不怕有朝一日被拆穿,下不了台?”阿海顺口问问。
“不过,王某此人,你别小看,他有一套真真假假的手段。说是蒋的学生,未必是真的,但他上头必接了什么线,不然不敢如此。”
阿海对现今官场上的事,所知有限,如果有一点消息的话,也多半是从曾老那里听来的,因此他期待着长辈多说些形势。曾老对阿海,也的确是知无不言。
“前天郑老告诉我,王先生在他家吃酒时说:蒋委员长在峨眉山埋伏了十万精兵,是处女兵。一挨到胜利,就开出山收拾共产党。”
“十万未婚女兵?”
“不不!训练有素并全师满员,且不曾开过战也自然没有缺损的叫做‘处女兵’。这是王先生原话,我七十几岁了,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么个说法。”
阿海不在乎这新名称是从那儿来的。他知道渔溪这地方,消息特别灵通,但也是出“乡下圣旨”的地方,其用语跟金銮殿里的御旨未必一致,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先生你武侠小说看得多,少林拳,武当剑,那么,峨眉山用的是什么兵器?”阿海用比喻的言语请教。
“听说全副美式装备,包括牙齿,只差个假鼻子!”老头子说着,惨然地摇了摇头,感叹道,“胜利,胜利!胜利了还要国无宁日哟!”
阿海木然地望着曾殿臣,脑子里回荡着老人家的最后一句话。他最担心的是郁牛弟的安危。这种割不断的义气,拆不散的情怀,使他对未来感到恐惧,不知所措。该怎么让小弟知道这个重要信息呢?来无踪去无迹啊!到哪儿去找他人呢?阿海此时倒希望,游击队真的使用他这“龙海之家”作联络点,那就可以及早给小弟提个醒。
曾殿臣见阿海魂不守舍的神态,以为只是这后生仔对胜利后的局势忧虑很深之故。这位“老世故”用先迁就后劝解的方式说:“日本仔派兵来打中国人,美国仔出钱出武器,让中国人打中国人,遭劫的都是我们百姓。”他停顿一下,未等阿海说些什么,便紧接着说,“不过,你也不必把局势看得太绝望。胜利了,那山匪、海盗总可以清除吧。到时候,你跟美玉就可美事成双了。”
“已照你老人家说的做了。”阿海迟疑片刻,不好意思地说。
曾殿臣觉得自己说过的话很多,到底哪句话这小子照做了?老半天他才想起那句:“有些事可做不可说”的警语,不免大笑道:“你这小子也真‘绝’!”笑过之后,老先生宽容地继续说,“如今也不怕什么,自从那位姓罗的改当福清县长之后,阿头那帮人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但他突然想起一句话,便补充道,“噢,忘了告诉你,据进善的小舅子说:张四回村庄了,郁家贵回海上。他们是散伙了吧。”
“他们散伙不散伙,不及他回到海上重要。在山上,他是困兽,在海上,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哪!”
这一点,阿海自然了解得比曾老先生多。
二
郁家贵回到海上,真是如鱼得水。在他跟着老五郁大乐去见了那位姓柴的大队长之后,就四处走走,探访许多龙田乡亲。有时是五弟大锣陪着去,多半是他自己去。他打听到一个绝对有用的消息,那就是本岛头人之一,金支队长不爱女人爱金子。没想到海上人还是这么缺金子,像老五那样,连个金戒指也没见过!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那山里的“番客姆”们,一听枪响就“自动乐捐”,比海上机会多。又加阿头说话算数,每次出阵回来,点完收获之后,立即论功按座次分发奖赏,自己口袋里自然就满。想当年自己在海上也有过收获,但上缴后发下的只是粮饷,有时偷偷扣点下来,还要冒着被告黑状的危险。看来山上、海上各有千秋。不过,郁家贵断定,眼前正是用点金子买下支队长,谋个好职位的难得机会。
郁家贵到支队长所在的门前,报称有事要见“表兄”。但金队长被乡亲麻烦厌了,破口骂道:“轧你老母!”
用闽南话骂人,大概是参照《千字文》,四字组合,有独创性,与福清话按统一的三字经“国骂”不同。支队长在骂出口后抱怨道:“我穷困时,亲戚都死到哪里去了?今日却一表三千里的都来了,我有多少表兄弟?请韩信也点不过来。不见,不见,你跟他说,‘老爸’睡午觉,不见客!”
郁家贵早想到了会有这一招,便对勤务兵说:“请转呈金‘司令’,说他表弟有件硬货,求表兄辨个真假、论个成色。”
郁家贵这一招十分有效,他立即被叫进去。他拿出一枚总有三钱重的金戒指,假惺惺地说:“请教内行,这货成色?”
“好好好,好货,好货。”姓金的只看一眼,便用手心掂掂分量。郁家贵一眼看穿,这不是鉴赏金制品的人,他不懂此道,不像龙田街那些专门收集康熙铜钱、自来火盒、香烟壳的“怪胎”。他只是贪财,那就更好办了。
“听说晚上在灯光下才能辨别真假,司令你留着慢慢地观赏,我还有一副金钗,也不知……”
“你明天统统拿来,统统拿来!”姓金的差点说出:轧你老母,韩信点兵,多多愈善,你看过戏吗?但他说出口的却是:“表弟!你明天……噢,你姓什么?”
“敝姓郁,‘小字’姓。”
“不小、不小,我渔溪人也知道姓‘余’的在牛田这地方是大字姓。这样吧,你明晚报个‘余表弟到’,就可直接进来,跟我酌两杯。噢,忘了问,你是那一部的?”
“柴大队长彪下,行伍的!”
“噢,很好很好,不过明天你来,我会提醒你,不迟不迟。”
支队长卖个关子,倒叫郁家贵心里七上八下。他后悔太早把金钗说出口,如今口袋里没有什么硬货能打动这姓金的了。想来想去,想到了他手头还有一些“红鸡公”和“乌鸡母”,那是福清哥们压箱底的上海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眼前不能用了,但无人怀疑将来能用,因此是个宝。他想好,下次把它带着,但要见机行事。
金支队长到底姓什么、名什么,底下人不太清楚。有人说他原名叫陈爱金,当初拉队伍抢劫时,看轻国币,看重金银,因此被人戏称姓金的。如今他被人叫做金支队长,奉承点的就叫他金司令。他喜欢人家叫他司令,但也同时提醒:“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轧你老母,千万不可在我表兄面前叫我司令。他郑德民才副司令,这岛上那姓林的头鸡(儿)也不敢自称司令呢!”
说他是郑德民的表弟,那可能真是一表三千里的关系。郑说的是福清话,金的确也说福清话。但金在紧急关头,嘴里骂出的都是闽南话,连敬酒也是那句:“轧你老母,给我干了!”他跟手下柴大队长有点不和。据说他是遗腹子,寡母养育长大的,因此他特别敬重寡妇。但那人称柴和尚的柴大队长,从来未成过家。此人翻墙入了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横扫,不分寡不寡的。这一点支队长实在很反感,但又拿他没办法。
第二天,支队长看到郁家贵果真带来了金钗,心中一热,在大半碗番薯烧的鼓动下,亲切地说:“我们表兄弟不见外,我提醒你,莫看那个柴和尚,雷(鸟)面孔长得像块‘八饼’,但他在副司令那儿,红得很。你扳不倒他,不要去碰他。”
“你是他上司,又是司令的表弟,他总得听你的!”
“那自然,那自然。我是说你,你不可去碰他就是了。”姓金的不肯丢面子。
“难道他也是郑司令的表弟?”
“那倒不是,这个我晓得。要知道,这和平救国军是各路人马凑合成的,哪个当头鸡的都要有心腹的‘天九牌’。姓柴的他会打烂仗,上阵时,枪响之前,先把自己的衣裳衫裤脱光光,驳壳枪一挥,大喊:‘要吃荤的跟我来,冲呀!’他自己打前头,多少次中弹,都被那个叫做黑皮的勤务兵给背回来,不死,命大。”
“他为何要自己脱光光?”
“这要问你们牛田街的薛某人,他最懂。那年我们队伍进牛田街之前,姓薛的一家早就逃到渔溪去投亲。林秀才家是他的远亲。我渔溪人,知道林家村像铁桶,谁攻得下?但这次林秀才也怕被他连累,因为号称郑德民部下的人马去攻过林家村。不过,薛的好朋友罗县长的队伍恰驻扎在林府,罗就近替他说情,林府人才勉强收留了他。”
郁家贵希望能避开这个攻打林府的话题,但没等他开口,金支队长就继续说:“别人我不敢说,我表兄做人,我知道。他哪里肯去攻打林家村!攻了,林、郑世代冤仇,两姓十八代子孙都要骂他。他若是那么傻瓜,当得了副司令?”
郁家贵深感这话扯得太远,对自己无益且很危险。怎么办?把红鸡公、乌鸡母抛出来,换个话题开条新路吧。但他还是想慢一步,先试探一下深浅为好。于是他说:“承蒙表兄如此重要的提醒,这意思是说,你表弟我,在柴某手下要乖乖地伺候他,不可多跑司令部来,以免为难表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