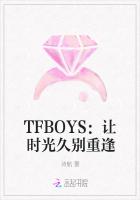六、差异性的混合
为什么在同一个组织中需要有不同的文化呢?查尔斯·汉迪认为,组织中的工作往往有很多种,而每种文化一般只适合处理其中的一种,这样组织就不得不融合不同类型的文化,以适应处理不同类型的工作。
汉迪将组织中的工作分为下面三种类型:
稳定状态的工作
开发类的工作
星号类的工作
“稳定状态的工作”指那些可以预知,也可以加以设计的工作。我们可以用体系、惯例、规则和程序来处理这些工作。在典型的组织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作量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开发类的工作”指的是那些处理新情况与新问题的工作。在许多这样的例子中,其结果可能是产生了一个新系统或新法则,以确保下一次再有类似情况发生时,不再成其为问题,而仅仅是稳定状态下的一个小事件。假若做得好的话,这类工作能增进组织适应环境的能力。
在很多组织中,负责这类工作的小团体在职称上会加上“开发”这两个字,比如“产品开发”,“系统开发”、“房地产开发”等等。
不过,并非所有的新问题都属于开发性的工作,有一些问题,查尔斯·汉迪认为用“星号类工作”来描述最为恰当。
“星号类工作”属于另类,它们是那些规则手册之类所无法处理的情况,是适合用直觉与速度,而不适合用逻辑分析来解决的紧急问题。
上述各种工作类别都有其对应的符号和管理之神。管理之神与工作如果搭配错误的话,管理上的混乱就会发生,而其结果便会令组织毫无效率可言。
稳定状态的符号是一个正方形,角色式文化的阿波罗神是它的神。
开发性活动需要一个富创造力的核心组织。拥有解决问题能力的雅典娜是其女神,代表符号是⊙。
星号情况自然就是由星号*来代表。在这里,宙斯和狄奥尼索斯同享尊荣(这种相互的联结也产生了一些混乱)。
当上述这些活动以一种适当的形式联结在一起,并拥有共同的目标或方向时,“管理”也就因应而生。
其象征符号如下。
所以,“管理者”必须在自身之中包含这四种文化,他必须能在适当的处境中效仿适应这个处境的管理之神。如果你想知道管理的魅力何在,回答便是:四个神的同时召唤。
倘若某些管理者看起来很疲惫,那他们有可能才刚刚经历过四种文化重叠的冲击——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
当然,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尤其是在疲倦或精神压力增大时,人们一般都会回归到他们自己所喜爱的文化。也因此,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所组成的各类团队,往往会有受到他们所喜好的文化束缚的倾向。
个人或组织开始受到文化制约时,他们便会去界定工作的性质以求符合自己的文化倾向。
宙斯型的人会将开发性的问题视为召唤个人介入组织的星号状况。
阿波罗型的人会让每件事物都能够被套用在规则手册中——尽管很显然,这可能是最复杂的做法。
雅典娜型的人喜欢创造,他们有时甚至倾向于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研究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法,或是设计一些虽然完美无缺,但在执行起来代价非常昂贵的解决方案。对雅典娜型的人来说,“达到要求”本身并不算挑战,只有对于阿波罗型的人,“达到要求”才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
这使得管理几乎变成了一件混杂不堪的事。
地毯店中的宙斯
汉迪的太太曾在空闲时做过室内设计师与装璜师。
那时候,她常常数落说管理问题根本不需要用到管理学院那些繁复细密的理论来解决。
她说:“只要有一般常识和读写的能力就可以了。”
她还说:“看看我的那些地毯问题。上个礼拜我订了一件‘红地毯’,要他们在‘星期二’送到‘京斯顿’。而他们却在‘星期四’送了一件‘蓝’地毯到‘瑞奇蒙’。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她补充说:“我连络了在店里的佛瑞德,劈头盖脸骂了他一顿,接着我们就闲聊起来。他向我保证说:‘没问题的。比尔会开货车去,拿回那条蓝地毯,然后把红地毯在今天下午送到你的顾客那里。’而且他们真的办到了。他们总是能在‘第二次’的时候把事情做好,然而这样一来付出的成本肯定就非常大了。所谓效率是指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把事情搞定。
当然,汉迪的太太是对的。
但在第一次就把事情办好,必须要有一个查核与控制的系统来核对订单、送货单、运货时间表和日期。
这一切都相当简单,但却需要一大堆琐碎的纸、档案和存根。至少对佛瑞德来说,这些都是乏味的事。
经营这家批发商店三十年来,他喜欢把事情记在脑中。这么一来,他就可以把他的时间用来发号施令、处理问题、解决争执、安抚生气的顾客、分派驾驶等等,这一切都是通过他个人的介入来运作的。
他认为所谓的“幸福”,就是安在窗户旁、大门边和桌上的三部电话同时响起,又都需要他马上处理——“这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有权力又有价值。
他是一个会破坏稳定状态的宙斯型人物。一个正方形中有一个星号,两种不适合的文化混在一起,等于加重了经济上的负担。在这个例子里,比尔的货车多跑了一些原本不必要跑的路程。
由此可见,到头来组织常常会将错误的文化放在错误的地方,也就是依人们偏爱的神来界定工作的性质,而不是依工作的性质来指派适当的管理之神。
即便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犯这种偏爱某个神的毛病。比如说,一个狄奥尼索斯式的人,要他每天去做家务这种千篇一律的琐事,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若果真要他去做了,原本平静的家庭定会被他搅得一团糟,因为他善于机变的天性如果没有正事可做,他便会制造一些小小的乱子,如活泼好动的孩童一般。
以下是更加混乱的管理的例子:
开发性核心组织可能会被要求,去解决在稳定状态下所有系统之间,彼此相互协调与联系的问题。否则,星号类状况会产生,而这时就需要宙斯型的人介入了。
但是,如果宙斯型态的行动过多,则稳定状态和核心以及星号之间,就会产生对抗,因而使得稳定状态本身失去许多力量。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提到的符号,神庙的梁柱会受到一种文化“干裂”(dry rat)情况的影响。在希腊神庙式的组织中,太多的企划案是个危险的信号。
为了把成本降到最低,阿波罗式的组织可能会试图将“每个东西”,甚至包括开发性的工作,都予以标准化与系统化。阿波罗型的人倾向于用过去的情况来指导未来。
举例来说,阿波罗式的计划将不过是“投影设计”(projections)的委婉说法。“合宜的管道与秩序的建立”会使创造力萎缩,并使得雅典娜或宙斯型人物的精力,转向打击该系统。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型的组织出现了跨部门合作小组的风潮。在许多例子里,这些小组自然地变成带有雅典娜任务式文化的创造性核心组织,这些小组的工作人员都很年轻,有才干而且满怀激情。五彩缤纷的未来,仿佛马上就要从他们身上蹦跳而出。
很不幸地,这并没有对那些主流派组织(也就是稳定状态中制作与产销,或是行政管理与服务等组织)产生什么震撼性的影响。这些核体组织就像是悬吊在希腊神庙檐下的大黄蜂巢。
从地域性来说,这些小组通常就像是在总部大楼边缘地带的房子;而在架构上,这些创造性的核体则是由最低阶层的管理者来进行管理。这些小组常会觉得跟那些处于稳定状况的同事比起来,无论是在会议、课程或集会上,跟其他的创造性核体组织——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核体组织,沟通要容易多了。
这种在“组织上的缺乏关连性”,使得这些小组在后来几年的经济紧缩时期,很容易成为被切除的部份。
在相互竞争猎取才智之士时,大型组织通常每年都会吸收不少年轻的大学毕业生、MBA人才或专业人士,储备在他们的人力资源库里。这些新兴的人才通常接受的是解决问题模式的教育,属于比较典型的雅典娜式的人物,这些人如要保有其兴趣与热情,就必须在解决问题的核心组织里去从事开发性的工作。然而对许多大型组织来说,真正重要的管理职位是在稳定状态的部分,这些组织的高层领导者为了显示自己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度量,往往会将那些刚吸收进组织的雅典娜式人员,放在稳定状态的梁柱底下当见习生,“扎扎实实地磨炼几个月”,磨来磨去,将这些年青人的创新精力都磨灭了,于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转变成了阿波罗式的人物,剩下几个不愿改变自己个性的,只有到别的组织去另谋发展了。
星号是很有趣的情况。
它们往往在你一点都没有想到的地方出现:不是在组织的“顶部”,而是在中间地带。
在组织的顶部,“决策”通常有深远的含义——它们比较适合由雅典娜式的核心组织来研究,能将一些开发类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
星号情况则通常会在人际问题的两难中被放弃——在所有情况中,这是让人最不喜欢去预测或规划的情况。个人的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争论、不同团体间的相互对立、私人的危机、重要的遴选或升迁决策——这些都足以产生星号工作的小火花。当然,它们也可能在董事会与会议厅发生,在工厂或办公室发生,但不管在次数或比例上,跟上面提到的情况比起来,都不是那么重要。
宙斯应当统辖的是监督者或中级管理阶层,要不就是像售货员、小车司机等,那些当规则手册派不上用场时,得运用自己创造力单独行动的人。
不幸的是,宙斯型人物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一不小心陷身于组织的中阶与边缘地带。宙斯型人物多半身在组织的顶端。不过,时代正在快速地改变。有些组织中,以总裁团、三至四人的执政团这种顶尖人物组合(或核体组织)来运作的概念,已越来越普遍。这是因为他们了解管理最重要的任务,是一种开发性的任务,而非可以单凭个人力量即能完成任务。(不过,一个族群首领在礼仪上和使节上的义务,还是留存了下来。一个宙斯型人物就如同某种宪政体系中的君主一般,适合正式地代表一个组织去参与外界的活动。)
因此,“差异”对组织的健全而言,是必要而且有好处的。追求单一神的“一神教”,对大多数组织来说,都是错误的。然而神的选择与混合绝不能随便,把错误的神放在错误的地方,将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痛苦万分,使组织的效率低下,甚至没有效率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