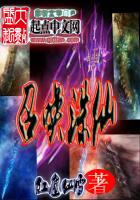本章导读
“联合”意味着不同的个别团体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下结合起来,使用某种共同的身份。联合的目的是借用保持个别团体的小规模,或至少保持其独立性,使之变大,是一种自治和合作的结合。“联合”意味着不同的个别团体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下结合起来,使用某种共同的身份。联合的目的是借用保持个别团体的小规模,或至少保持其独立性,使之变大,是一种自治和合作的结合。这是组织长期以来缓慢地、辛苦地发展出来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尽量利用两个团体的优点——大团体使他们在进入市场和金融中心时能打出一面漂亮的旗帜,也使他们无需耗费耗时以扩张规模;而小团体则使他们拥有自己所必需的伸缩性,和每一个团队成员越来越渴求的“共同体感”。
一、联合的性质
联合并不意味分散化,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分散化意味着中央委派某种任务或职责给周围的团体,然而却仍旧控制着大局,中央做计划、委派和指导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仍会发现那种阿波罗式组织的高度一致性:一个组织越是分散化运作,中央机构的信息流出量和流进量也越大,表面上看起来中央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实际上中央非常清楚各团体的进展情况。而且新科技使得信息更能大量而立即地流畅,使人更容易想到对组织采取更进一步的分散化,至少是理论上的分散化。
然而联合制是不同的。在联邦国家,个别的州是最先创立团体,各州结合在一起是因为有些事情在合作时可以比单独行动时做得更好(国防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中央的力量由周围的个体以一种掉换委任的方式赋于。因此与其说中央指导或控制个体,不如说中央协调、影响个体,为个体提供忠告和建议——所用这些协调、影响、忠告和建议,都是在跨国公司总办公室里经常使用的字眼;跨国公司常常由于子公司在地方上的优先权而被迫采用联合制。
因此,联合组织是推力倒转的组织、创造力、驱动力和精力大部分来自个体,而中央所拥有的则是从侧面来看较低的一种影响力。瑞士可以做为一个运作中的联邦制的典范。这个国家平静而繁荣,在很多方面是欧洲其他国家所羡慕的。理所当然,我们会认为瑞士的政府一定是人人赞扬的,而其总统的大名必定是家喻户晓。然而说来滑稽的是,即使瑞士总统主持一个高峰会议,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立即说出他是谁,或者更准确些,说出他以前是何人,因为在瑞士,总统的职位是采用轮流制的。瑞士的总统被看成是一个主席,一个协调团体的主席,这个主席引导而非指挥国家事务,职位虽然重要,但从侧面看来并不高。
以管理上的术语来说,联合组织是一种松紧组织。中央牢牢地握紧某些决策——经常是有关如何使用新的盈余利润、如何安排新人的职位,以及何时任用新人等等关键性的决策。这使得组织得以塑造长的策略,得以经由高级主管影响这些策略的实施。这是一种其他机构早就熟悉的方式。有一次汉迪问英国一所较负盛名的独立学校的校长如何改革这个学校。“我选出会议的主席和各系的主任;我拨款装设一些新设备”他说,“然后我以十年的时间等待成果”。
我们一定会问,联合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不是自动地,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也不自觉地,或经过深思熟虑。再一次,这个耐人寻味的非连续性又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生活。联合制是被强迫发生的,因为缩减的组织核心不能应付因运作分散化而大量流入的信息。当三叶草成型时,当一个较大的组织长出更多、更小的三叶草时,组织会尝试从核心管理这些三叶草;他们会依赖新科技提供所有必要的消息。新科技没有令人失望,但讯息为了有用仍然必须由人亲自诠释。更多不同的讯息需要更多人诠释,假如我们不要让这些讯息无用地被堆在电脑输出纸带堆里或藏在不为人知的电脑记忆库里的话。然而说来矛盾的是,如我们所见的,组织正尝试缩紧核心,并削减其幕僚。到了最后,他们必须停止自中央寻求信息,必须停止从中央管理一切,必须开始放手。那时分散化就变成联合制了,这是一种非连续性,这种非连续性的重要性没有被人了解,也因而没有被许多主管加以发挥利用。
“你公司的总办公室里有几百个人?”查尔斯·汉迪问一位要求他解释联合制的朋友,他是一间跨国公司新上任的高级主管。“十五人,我想”他说“这就对了”汉迪有点得意洋洋地说,“联合制的要点就是拥有小型的枢纽,然后让其他部门真正地做事情。有了这种联合制的想法,你就不需要让一千五百个人把伦敦的上空闹得不得安宁了。”
“我说十五人”他回答,“不是一千五百人,你知道,”他纵容自己解释下去”我把所有的运作都交由独立的公司处理。我们在中心收集他们的盈余,将这些盈余投资到新的机会中。我们观察他们,看他们是否制造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制造的盈余。倘使他们没有,我们就给上层人员施加一点压力,最后则以别人取代他们。新冒险和新人物,这就是我在中心所关注的事情,而我只需要一些足智多谋、一些精明干练的人来协助我。”
“你不需要我”汉迪说,“你自己已经发现了组织的联合原则”。
“我管这个叫常识”他回答。
十五个人绝对无法精密地控制大约三十个不同的公司、分部,及厂矿的运作,他们甚至没有时间阅读拿到手的信息。到了最后,他们最好不要去尝试那种什么都要插一手的管理,而只是将全幅精力贯注于那些他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和那些只有他们才应该做的决定。组织的核心领导集团越小,办事越有效率;组织的核心领导集团越大,人浮于事的“松懈”现象就会产生,对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是极其不利的。
二、中央的角色
一份在1988年为国家经济发展局(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ffice)所做的研究报告,对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些电子企业做了严厉的批判。这份报告说,和它们在日本、德国及美国的竞争对手相比,这些企业的成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这份报告提示说,这种缓慢成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公司所采用的法人组织结构。这些公司已将自己分割成个别的企业,然后让这些企业决定自己的策略。结果常常是短视而狭隘的想法。作者在此暗示的是只有大的组织才能做广泛且有远见的思考。
如果这些公司的确让个别企业思考策略上的问题,那么他们就误解了法人式的联合组织。这就好比美国让各州去决定个别的国防政策——到了最后,没有一个州保卫了这个国家。倘使你把中央看成一个银行业者,收进盈余利润,并做有价值的投资,那么你就忽略了联合组织大部分的益处。联合组织的目的是让事物在维持小规模时变成大规模。
中央绝不只是一个银行业者。只有中央可以想到下一个年度报告之外的事情,或者,引用家庭企业者的话说,可以观望坟墓之外的事情,只有中央可以思考可能连接一个或数个自治部分的整体策略。让局部决定重大的策略等于将未来抵押。
然而在联合组织里,中央并没有掌握全局。逻辑上,我们很容易想到中央决定长期性的策略,然后将这些策略交由局部执行。但是这种逻辑令人联想到旧式操纵式的管理,令人联想到分散化工作的交托和控制。这不是政治理论的新语言,不是人民和共同生活体的新语言。联合组织的观念是要中央代表局部行事,倘使产生的决策欲自我执行的话——这是必要的,因为中央没有人力来操纵。
这一切必须有一个新的法人团体形象,即中央的确是一切的中枢,不是高级职员或总办公室(一个逐渐从法人组织中消失的说法)的一个礼貌性的代称。中央必须把握新人和新的盈余利润的关键性功能,但是决定策略时必须和各部份的代表协商,必须考虑各部份的意见。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都是极有道理的——中央变成各部份代表的集会,各部份代表在集会中为整体联合组织行事,然后各自返回各部,为整体做自己范围内的工作。
所以,管理联合组织中心者绝对不能像是君王一般的人,因为君王可操纵一切,而且对于贵族政府有偏好,这样凡事一人说了算的独裁似的管理方式只会导致整个组织的毁灭。联合组织中心必须是一个进行说服调解的地方,一个通过辩论得到协议的地方。当然,指挥是有其必要的,然而被指挥的是主意,不是人。较大的跨国公司往往比其他的小公司更早变成联合组织,因为这些公司必须和拥有自治权的国家进行交易。这些公司已经开始设立三头统治,或甚至是委员会,来管理中央。
查尔斯·汉迪问一位新上任的一家跨国公司的主管,成为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的主管,成为(就某一意义而言)我们其中最伟大的一位实业家的感觉是什么?“事情并不是你想像的那样”他回答,“我刚刚还在会议桌旁忙得团团转,暂时我做的工作只是安排小组入座,因为总要有个人做这件事呀!”
在1984年,拥有三百多个公司(从铁路到地产)的日本东京集团那位具有非凡号召的老头子后藤信郎辞职了,由一组人取代他的职位管理公司,于是东京集团在转眼之间就从君主制转换到联合制。
在这些组织里,中央有自己的幕僚,他们关注的事情主要是未来,计划和可能性,以及工作纲要和选择。他们在中心向政略上的前辈提供建议,后者许多是在各部工作,而非中心,而且他们逐渐必须依赖影响力行事,而不是正式的权威,或绝对的权力。在许多组织里,中心已经变成一个训练未来领袖的地方,因此在委任于其中一个局部之前必须先向全体开放。
由于组织正在发展中,目前我们尚不易见到纯粹的联合式法人组织。日本的组织一向比较接近这种法人组织。最近,约翰·纳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法人团体再创新》(Reinventing the Corporation)一书中曾引用一段三井公司山下勇的话:“今日最佳的法人组织结构包含一个小型的决策中心,做为这个中心的辅助的是许多最新式的设备。”然而新语言又一次预告了新的行动。一位高级主管最近曾为他的联合公司的中心做了不同的形容,包括“老饕的好向导”(说明哪一个子公司最擅长何事)、“交通警察”、“交响乐团指挥”、“诠释者”、“批判者”,以及“啦啦队队长”等等。在被人问及他自己扮演什么角色时,他说:“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当一名使节,我们在外面必须竞争,但是在里面必须合作。”这些话简洁地说明了联合组织相互依存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每一个局部都需要中心和其他局部的协助,才能生存。然而太多的相互依存可能会导致离散,变成一种不同局部的任意聚合,一种积聚,而不是联合。
很不幸地,与其采用被误解的联合制倒不如没有采用联合制。联合制被误解时变成一种没有效率的分散化,会被人看成是一种没有领头羊的法人组织,或中空的公司,或者引发类似英国经济发展局那份有关英国电子企业的报告中所做的批评。了解中央的角色对于一个正确的联合组织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联合组织也必须了解“从属原则”和“倒翻的甜甜圈”这两个观念,因为结构本身不能制造联合组织。查尔斯·汉迪特别使用这些比较怪异的说法是要暗示这些组织需要新的思考方式。我们不能再采用和我们的父母们相同的想法。再一次,非连续性要求人们进行颠倒式的思考。
三、从属原则
联合组织不只形式不同,成员的个人修养也和别的组织成员大不相同。这种组织要求管理人和被管理的人采取一套不同的态度。这就是一个关键性的非连续性——不是结构上的改变,而是管理哲学上的改变。
这个哲学的特色可以用“从属原则”来形容。大多数人并不熟悉何谓“从属原则”,但是罗马天主教徒则不然。在罗马天主教里,“从属原则”长久以来就是传统教义既定的一部分。教皇李奥十三世(LeoⅩⅢ)首先阐释了这个教义,但是后来在1947年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时发表的教皇通论〈迈向四十年代〉(“Ouadragesimo Anno”)里,这个教义又被提出来。“从属原则”的倡导人认为“一个规模较大、阶级较高的组织霸占规模较小、阶级较低的组织能够有效完成的工作是不公平的、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是对正规秩序的侵扰。”窃取别人的决策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