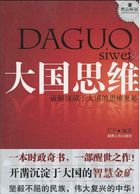一旦从这个意义下的理由着眼,价值多元论与价值相对主义便告分家。自由主义的独特观点正是从价值问题的这个「理由」面向出发的,而不是如伯林、韦伯一般,先设定了某种价值理论。自由主义重视这个面向,是因为理由这个因素涵蕴着个人选择的自主成分(而非选择的结果),而自由主义必须着意维系自主成分。价值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客观的地位具有甚么「价值因子」或「价值成分」,更在于它乃是特定人的特定选择。尊重个人,意思是说必须尊重每个人的选择的权利,也就是不以一己的好恶成见压抑对方的选择机会与选择结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尊重乃是尊重一个有理性反思能力的自主人,它还带出了理由在判断价值之高下好坏时的重要地位──自由主义相信人的选择带有评价性的理由。因此自由主义并不是仅仅坚持价值多元论;它更坚持人们要为自己的选择结果与其间的是非善恶高下之评价,相互提供理由。自由主义若是单纯强调「价值多元」,忽视「理由」这个面向,那就是误解了自己的面貌,放弃了自主性的要求。
在自由主义看来,价值多元论说的是:每个人选择的结果不会一样,因此选择所认定的价值呈现极多样。但是自由主义会跟着强调,选择不可能仅只是表达欲望偏好,而是受到了理由的决定性影响:理由是一项选择的构成性因素;理由的差异,乃是造成选择之间差别的最重要因子。唯有从选择的理由,才能判断所选择的价值为甚么真有其价值;而理由也只有经过相互的交代与诘疑,才能取得其可信度、证明其妥当性。选择若是没有理由,或者其理由所反映的只是当事人的恣意偏好,那么该选择或许仍属于权利的范围,却无所谓价值,并不可能跟其它选择「一样好∕一样对」。无庸赘言,你的理由是不是能成立,是不是经得起别人的检讨,甚至于能逐渐发现他人的理由更合理、更高明,也就是说他人的价值选择比你合理、高明,都无法决定在先,而只能在这样一种说理过程中逐渐呈现。●134◆
当然,这不是说「理由」便可以豁免于价值相对论的现实考验。但是理由之所以成为理由,正好不能局限于所选择的一阶价值本身的特色,而是要联系到对说理双方都成立的共通价值,理由才能发挥功能。选择者必须用对方能够理解与同意的立场,来说明自己根据甚么标准或者考虑做出该一选择。通常,这样能为对方理解与同意的立场并不是一蹴可就,而是需要反复的深化与扩张,找到的标准与考虑对他人才具有说服力。但是这个过程,以及其所设定的目标,却是必要而且合理的,因为价值即使多元,但是人们做选择却不是仅在意价值本身的内容,消极被动地受制于「不可共量」,而是有背景来由、有目的、有原因、有动机、更有当事人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自我认识作为根据和脉络。这些,构成了特定的评价脉络,其健全与合理,正好是当事人需要展现辩解的。妄想否定这些因素在评价中的角色,便根本没有理解甚么叫做评价、何谓选择、以及价值之间的比较如何进行。这情况下即无说理的可能,从而价值多元论才会沦为主观恣意的价值相对论,甚至于虚无主义。
可是显然,要让这样的价值选择及其理由有可能,便需要假定超乎一阶价值本身的理由是可能的。而这种能够针对不同一阶价值展开「共量」的理由,岂不正指向所谓的「普遍」吗?能让两个人讨论谁的价值选择更高明的「理由」,一定是超越了当事人双方选择的理由;在这个基本的意义上,该理由已经具有最雏形的普遍性了。当事人也许不会很快在理由上取得一致,因此他们会继续争辩、寻找更普遍(意思是说更能迫使对方承认)的理由。这种理由会跨越文化、社会、时代等等,其普遍性也就更高。那么,有没有彻头彻尾普遍的理由?伯林认为有。他强调一种跨越文化、时代、族群等等的普遍人性:他说,有一些理由我们必须拒绝,因为在「人」的意义上它们是无法理解的。●135◆但即使在这个最高程度的普遍性之外(或者之下),价值多元论一旦设定「理由」的概念,便也设定了普遍主义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乃是结合在一起的。
不错,届此只是问题的开始:我们应该对这种「理由」意义上的普遍主义再多做些说明,尤其应该将它与「实体」意义上的普遍主义──也就是历史上乃至于今天以「普世价值」名义出现的各类普世理想──做适当的区分。很多普世价值,表面上看来以某种超越性的、或者宗教、形而上的源头为根据,彷佛以实体的方式存在;其实,它们乃是理由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所承认的妥当理由,其普遍性足以作为最高层次的理由,支撑较低层级的价值选择。它们之所以具有这个地位,很可能如伯林所言,来自我们对于「人」的某种根本理解。但由于这个问题过于复杂,在此只能存而不论。●136◆
以上的分析如果成立,无足以证明施特劳斯心目中的客观终极的「本身即善或者对」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但足以证明,多元论不需要坠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多元论不能轻易否定掩盖,那么若不得不从多元论出发而仍得到客观、普遍的价值判断,我们便应该循追寻理由的途径发展经营其间的结合。政治哲学完全不需要像施特劳斯一样,在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与绝对主义、客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作非此即彼的抉择。相反,政治哲学是可以同时认定多元论与普遍论的。
三、美好人生、社会正义、多元论
一旦将多元论与普遍主义结合,并且面对多元情境下的说理必要,要求我们的价值选择满足理由意义下的普遍主义之要求,便会产生一个状况:在任何一个时刻,我们所认定的终极价值,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诘疑与理由。易言之,个人的价值认定即使在主观上具有绝对的力道,客观上却仍然属于临时性的(makeshift),并且当事人在「投入」之余,不得不承认这种临时性格。而既然终极价值不能免于这种临时性格,那么仰仗终极价值来提供意义与价值的个人生命,又如何可望确定地「美好」呢?
1.美好生命与个人自主
对于「美好生命」的问题,施特劳斯有明确、直接的答案:尽人之「性─自然」(nature)即臻于美好人生。●137◆这个说法,在今天的规范伦理学中通称为完美论(perfectionism)。完美论认为,「性─自然」指一些内生于人性而界定或者构成人性的性质、使人成为人、活得像人的特质,例如某些能力或者活动;而美好人生,即系于将这些性质发展到最高的程度、让人性的核心特质得以充分实现。●138◆换言之,借着发展人性之中居于关键地位的某些特质,俾使人成为完满的人、充分实现人性的可能,即臻于美好的人生。而那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需要的性格特质,便构成「善」或者「德性」。
对于这种完美论,本文不拟细致全面地讨论。对比于上述终极价值的临时性格来说,施特劳斯似乎也注意到,他这种关于善的说法其实是后设性质的,只是为人类求索「善」指出一个方向,并没有指出善(或者「性─自然」)的内容;因此他时常区分「拥有」真理与「追求」真理:哲学乃是「追求」,而不是「拥有」。●139◆那么,他是不是会承认,上述所谓的临时性格,也适用于我们在任何一刻对于「善」、或者对于「性─自然」的认识,──即使他坚持这些概念本身乃是全然客观而恒定的?
施特劳斯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直接回答;至少没有追究一种临时性的善观对他整套哲学的涵蕴;刘小枫则说到哲人与先知的不同在于「哲人的审慎悬置了对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断定」,像是也接受了某种「临时性」。●140◆不过,分析地说,无论是不是认为终极价值受制于某种临时性,关于甚么是「终极价值」、甚么是美好人生,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个概念还受制于另外两项至为根本的条件:一是所谓的「认可限制」,另一则为「可修改的限制」,对可能的善概念形成了规定。这两种限制都涉及维持个人的自主,看来仅能说是「现代」的产物;可是必须注意,它们的理由并不特别局限于现代,而是因为「有价值的生活」这个概念本身便要求人不可能只是某种价值或者某种生活方式的容器,它规定了美好生活不可能在无意识中完成;质言之,有价值的生活一定是包含自主性这项因素的生活。结果,这两项限制迫使美好人生的概念始终保持着其临时性格。
认可限制(endorsement constraint)不难理解:任何关于美好人生的概念或者构想,无论其客观的妥当性如何无疑,都必须经过当事人的认可,才能取得充分的「美好」地位。换言之,假定某种人生的构想客观言之──例如根据神意、根据自然、根据历史规律──确实是最美好的,但若是无意识、或者受强迫、或者出于误解而过这种人生,比起经过当事人的理解与认同、采纳而过这种人生,其美好当然要打折扣。假定信仰某一宗教会带来终极的救赎,换得最美好的人生,可是我却在既不明白其奥妙、又心不在焉的状况下草草接受该信仰,我能算是获得了美好人生吗?所谓「幸福的傻瓜」──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活出了美好的人生──是不是在逻辑上即不可能?这情况之下,是不是他可能很快乐或者春风得意,但是他的人生仍然称不上「美好」?
至于可修改的限制(revisability constraint),同样强调当事人的自主追求这个因素,并不外在于美好人生或者终极价值之概念,而是其中的一个构成部分。「美好人生」这个概念有其内在的一种紧张性格:我在当下认定的美好人生,无论内容为何,在概念上(逻辑上)便注定不会等同于真正的美好人生。为甚么?因为必须承认、并且实际容许,对于美好人生由甚么构成,当下的想法也许有误、更可能改变想法。如果我只知道(或者只能)死心塌地地接受某种关于美好人生的理念,既无怀疑的动机,也没有改弦易辙的余地,我岂不无异于该一理念的容器或者承载者,岂还有评价、考虑、选择的可能?可是一个在这种意义上被剥夺了选择与改变可能的生命、沦为某信念之承载者的生命,岂有可能还是美好的?在这个意义上,「美好人生」这个概念,原本就应该是临时性的;它的有待更正与发现,跟我们所认定的价值观之有待诘疑与提供理由,在含意上其实如出一辙,相互呼应。●141◆
用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分析方式,指出「美好人生」理想由于必须以人的自主性为其构成条件,因此必备这种暂时性格,对自由主义抱有怀疑的读者当然不会满意。笔者自己也不禁要琢磨,人类面对一项生命的理想时,终极而言究竟是「选择」抑或是「被选择」?坚持自主性在美好生活里的构成地位,「终极价值」会不会就沦为鱼与熊掌,即使鲜美至极,却并无终极性可言?●142◆但是如果祇坚持终极价值的客观与超越地位,个人的理解、判断、踌躇、追寻竟然只扮演偶然的、外在的角色,与他的生活之道德意义并无本质上的关连,岂不是根本忘掉了这究竟是谁的人生?何况,一个人面对某种超越价值时的投入,若是没有一丝怀疑与挣扎的成分,岂不正因为缺少了个人即使「令神发噱」●143◆但却适足以表现尊严的一个阶段,而显得廉价猥琐?这个问题太过于棘手,更涉及了人类如何面对「超越」的议题,在此必须悬置。不过上述的关于人生理想之临时性格的基本想法,对于我们的道德论述与政治论述,仍然有着可观的启发,不能忽视。德沃金曾用概念分析指出,「当下所理解、信仰的美好人生,不会是真正的美好人生」;麦金太尔则用完全不同的分析指出,「人的美好人生,乃是用来追求人的美好人生的生命」●144◆。这个想法,即终极价值与美好人生等概念,不可能是一种具体的状态,而只能是一个涉及不断追寻、学习、发现、更正等过程的暂时性结论,可能有两方面的启发。
一方面,对于向往「美好人生」、追求「人生意义」等等而以为有现成答案「在那里」的人,上述想法是一种警惕与针砭,可以减少人类的自大与妄想。作为人类,在人类极有限的条件与限制之下,期待终极价值与美好人生以完整、具体、确定的方式在生命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出现,不仅如上所论证,在概念上不可能,其实徒然反映了人类一种童稚的自大傲慢(hubris)。试想:以人类生命的短促、加上道德能力与认知能力的有限,居然期待「美好人生」以其全部的确定性、客观性、不容置疑的地位在某个时空被我们掌握,岂不是如井蛙论天、夏虫语冰吗?我们对人生应该抱持甚么样的期待?──这个问题牵涉深远广泛,在此无法深论。但是上述多元论与普遍主义的结合,毕竟有助于提醒我们应以更谦虚的态度面对人生的将就(makeshift)性格,也是值得进一步参考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