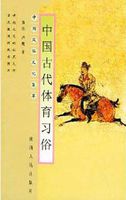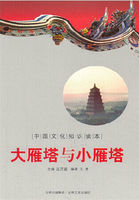高延的第三本书,我觉得值得一看,就是Universismus(《天人合一》)J.J.M. de Groot, Universismus, die Grundlage der Religion und Ethik, 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en Chinas. Berlin: Reimer, 1918. ,这其中最重要的思想便是天人合一,但是在美国要想取得成绩的话千万不能提到这本书。这本书写得很好,他试图说明中国语言、文化、建筑等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人合一的理念。虽然这本书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肯定会有一些问题,但如果你想真正了解天坛的话,需要看这本书。高延关于中国建筑的描写可以说是空前的,美国汉学家不同意Universismus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不包含主语和宾语之间的统一(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高延认为,Universismus是中国宗教伦理学的基础。这本书在1918年用德文在柏林出版,一共400多页,现在依然可以买到,可以知道其生命力之强大。美国人认为高延的书不值得看,里面包含战争的观点,但是德国学者,包括我在内,觉得应该一看。叶乃度是一位民主德国重要的汉学家,所谓共产主义的汉学教授(communist professor of Sinology)?我不清楚。叶乃度评价高延为“殖民利益的走狗”(a lackey of colonial interests)R.J. Zwi Werblowsky, edited by Hartmut Walravens, The beaten Track of Science: The Life and Work of J.J.M. de Groot. Asien und AfrikaStudien 10 der 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2,p.32.,是“江湖骗子”(charlatanry)Ibid.,还搞什么“帝国主义的煽动活动”(imperialist agitation)Ibid., p.33.。我还记得我们1978年在西柏林开现代汉语讨论会的情景,当时邀请一位民主德国的学者来参会,但是他拒绝出席,说我们这群搞帝国主义学术的学者所组织的会他是不会参加的。我们当然不是搞什么帝国主义学术的,只是当时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好罢了。说实在的,叶乃度对高延的这种评价是有失公允的,是否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现在很难讲。没有人像高延一样那么系统、深入地研究过19世纪的中国宗教。他在非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经过谈判将苦力直接从福建运送到东印度群岛:“I brought about free emigration of Chinese labour to the East Coast of Sumatra, thereby rendering invaluable service to the prosperity of that colony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Tobacco cultiv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were thereby freed from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English Straits Settlements.”(我实现了将中国的劳动力自由移民苏门答腊岛东海岸,从而长时间服务于这一殖民地的繁荣,使烟草种植及其他行业,从其所依赖中的英文海峡殖民地中解放出来。)Ibid., p.49.当时的中国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高延帮助他们去马来找工作谋生并非是完全错的,他了解劳动的辛苦,匈牙利人也曾这样描写当时的劳动:“men died like flies, the fit ones cleared away the dead and continued the lifeanddeathstruggle.”(人死了就像是死了只苍蝇一样,健康者将之清除干净,继续着生与死的斗争。)Ibid., p.37.注释1。当时的荷兰很有钱,他们的财富来源就是亚麻,那是谁帮他们获得巨额财富呢?是中国人、中国的劳动力。
附录11.5
Eduard Erkes (1891—1958)
中文名:叶乃度。中文译名:爱德华·埃克斯、爱德华·艾克斯、爱德华·何可思。
德国汉学家。著名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的高足和女婿。在莱比锡大学研究《招魂》,获得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起任莱比锡大学教授。希特勒统
治时期,由于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被迫离开大学,直至1947年莱比锡大学恢复东亚系,方被请回,继续执教。1950年兼任柏林洪堡大学的汉学教授。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的宗教、哲学、社会制度及宋玉作品翻译等。
这本书有些地方我不是很能理解,比如说“Chinese cooliebrokers”(中国的苦力经纪人),是那些剥削中国苦力的中国人,在那些劳动力从新加坡转往马来的时候,不是外国人而是他们的同胞利用他们发财。“There were two possible sources of supply of Chinese labour”Ibid., p.39.,意思是有两种渠道可以获得中国的劳动力,并且中国官员会帮助他们:“The one was the weak and corrupt but still functioning Chinese ‘Empire of the Middle’”Ibid., p.39.(其一是软弱和腐败仍然在中华帝国中起着作用),那当时果真会有protector of ChineseIbid.(中国人的保护者)吗?当时中国人要求在荷属殖民地设立自己的领事馆,高延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害怕领事馆里的中国人会更厉害地剥削自己的同胞。这么说有证据吗?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老师可以出国教书了,当时他们在西方的工资很高,但80%要上交给领事馆,所以他们就成为中国新式“苦力”。那时,这些在国外教书的老师们常常抱怨说,我们不要找领事馆,出了问题我们可以自己解决。
这本书中还有很有趣的一点是对台湾的介绍。台湾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地方,清朝很晚才对台湾表示关注。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台湾是在17世纪80年代年才属于清朝的,清朝在19世纪末才派遣首位官员去台湾,那里居住着少数民族。那为什么后来在台湾会有说闽南话的大陆人呢?这与荷兰有关系。台湾在1626—1664年间是荷属殖民地,大陆人和台湾当地人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在日本人进入台湾以后,大陆的劳动力不再能进入台湾,但是不要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As late as April 1889 the Deli notebook mentions reports that 263 coolies on board the S. S. ‘China’ has forced the captain to land in Singapore where they went ashore.”(直到1889年4月,德里公司的记录还曾提到,S.S. China号邮轮上的263名中国苦力胁迫船长在新加坡靠岸并从那里离船上岸。)Ibid., p.40.S.S. China号轮船系英国格拉斯哥Fairfield船厂为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所造,1889年6月下水,当时主要航行于旧金山、横滨和香港之间,美西战争期间成为军方运输船。战后几经易手,直到1925年报废。德里公司系荷兰商人Jacobus Nienhuys于1869年所成立一家烟草公司。以上的事例说明他们有办法不去自己不想去的地方。那现在在国外还有中国的劳动力吗?有,在非洲,中国政府派遣很多劳力去非洲,钱都给劳力吗?不一定。19世纪的中国人很喜欢去开放的通商港口,那里给他们提供了赚钱的机会,但是很可惜,也常常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比如走私。
那么中国是唯一一个出口劳动力的国家吗?不是,如果你们看过席勒的《强盗》(Die Ruber, 1871)的话,就会知道在18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君主为了发财,也会将自己的子民送往需要士兵的美国,席勒想要通过这部话剧来批判那位君主,所以席勒也无法在那个地方待下去,会有人去逮捕他。
中国人会剥削中国人,那非洲人呢?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the shipment of African slaves has changed the demography of America. That of Indians to East Africa has enabled the new sovereign black states to demonstrate their own version of racism.”(对非洲黑奴的贩运已经改变了美洲的人口结构。印第安人被贩运到东非,为一种新的黑人的自主国家提供了条件,并显示了他们自己的版本的种族主义。)Ibid., p.38.作者的意思是说那些中国人在非洲也不怎么受欢迎,会有人欺负他们,真的是这样吗?可能是,但我不希望是这样。“The kidnapping of coolies for labor as far away as South America clearly was common pract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 such extent that it even gave rise to a sobriquet which Giles felt it necessary to note in his Dictionary as “zhuzai”a term applied to the coolies who were kidnapped and taken to Cuba, Peru and else where. ”[用来劳作的苦力像从遥远的南美绑架而来,在19世纪的中国显然是常见的做法,甚至到了这种程度,翟理斯感到有必要在他的字典收录了一个绰号“猪崽”(zhuzai),用来指那些被绑架到古巴、秘鲁以及别的地方的苦力。]Ibid., p.42.注释10。“Many Chinese from Amoy, Swatow, etc. came to Sumatra to earn a livelihood, and many of these workers could return to China with their savings.”(许多从厦门、汕头等地来到苏门答腊谋生的中国人,这些苦力中的很多会将自己的积蓄寄回到中国。)Ibid., p.47.所以在马来做苦力的人是可以回国的,当时从厦门坐德国的船去马来需要两个星期,在新加坡转船的时候需要交给经纪人钱,否则他们会受到欺负。
高延受到了批判,特别是受到了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学者批判。高延批评自己的老师:“His teachers, saw and lectured only about ‘the outside... There was not a single reaching out toward the soul or spirit of the natives.”(他的老师,看到和演讲的内容只是“外在的东西……没有任何一点触及到了当地人的灵魂或精神”。)Ibid., p.75.高延要求汉学家和中国人住在一起,这样才可以既从外部又从内部观察到中国,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对的。我曾经告诉过你们,我的第二个古代汉语老师翁有礼,既没有到过中国,也不和中国人来往,我觉得这样是有问题的。高延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他所研究的中国宗教却使他不能够喜欢,很奇怪,他在厦门待了很久却不能喜欢那里的宗教,总是说“迷信”。有些人批判高延,将中国人的宗教称之为“迷信”,是在进行帝国主义活动,总是显示其自己的优越感,这显然是不对的。其实鲁迅也这么说过,你查《新华字典》的时候,很多词也会被解释为“迷信”。我告诉过你们,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西方汉学家愿意跟中国人在一起,说要是跟中国人在一起就会受到歧视。从这一点来看,高延是进步的。在高延看来,中国对待宗教是宽容的,基本上不会发生像欧洲那样的宗教战争,虽然这本书的作者怀疑高延的观点是不无道理的,但我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高延不喜欢道教、佛教,或许也不喜欢儒教,但如果他什么都喜欢的话,那他究竟喜欢什么呢?所以在他的身上充斥着矛盾。还有一段他写的英文:“Although my stay in China is extremely attractive to me because of the treasure of information which I am collecting, a stock that grows daily, none the less a life of exile in the filth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here nothing is ever cleared, which spreads stench in all directions, where in the winter you suffer from cold and in the summer you toil and travel in unbearable heat, where privation, strain and poor food are my daily lot — that life becomes intolerable to me in the long run. In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I have to be on my guard all the time and against everyone, for hostile assaults hang like a sword of Damocles over the head of every foreigner. The net result is that one becomes filled with an unsurmountable repugnance against the population.”(尽管对我来说待在中国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因为我看重我收藏的资料,它们每天都在增多,我仍然在世界上肮脏的国家过流亡的生活,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曾被清理过,恶臭传遍各处。在冬季,你遭受冰冷,而在夏天,你在工作和旅行中必须忍受酷热。穷困、天性以及粮食的匮乏,我每天遇到很多——就长远来讲,生活对我来说变得无法忍受。在该国的内部,我必须要随时对自己进行保护,并与每个人为敌,因为敌意的攻击像挂在每一个外国人头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的结果是让中国人成为了充满着令人厌恶性格的人群。)Ibid., p.24.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很脏,本书作者也因此说他是种族主义者,真的是这样吗?这段话没有公开发表过,是他日记中的一段,在他的档案里找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把他未发表的东西用做批判的材料吗?我们知道我们都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比如妈妈会骂自己的孩子,但是很快就会忘记并和好,朋友之间也如此。夫妻之间有时还会互称“讨厌”,有些北京人也会这么说。当然,他说得太过分了,有些情况也没有考虑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