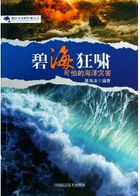而诡异的是,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理念两种“救市”策略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均陷入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2008年触发全球金融海啸的美国房贷金融机制倒塌开始,以贪婪嗜血的华尔街投行为对象,以“占领华尔街”为象征,作为西方社会自由中最基本的一种自由、在美欧畅行多年的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资本等相关利益集团操纵下,日渐滑向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极端轨道,因而遭受了空前的批判和抵制,被广泛认为是导致社会利益结构失衡、贫富分化的祸首,也是民生的敌人。这种观点在欧美已形成了相当普遍的共识。奥巴马政府推动全民医保等左倾政策,巴菲特呼吁对富人增加税赋等,都是对此的一种积极呼应。
另一方面,如果说过分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引起的抵制,更多地只表现为经济文化问题的话,一段时间以来的欧债难题,却相当严重牵涉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更深刻的社会痼疾。希腊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之所以政府债台高筑,直接原因是社会福利支出严重超出政府财力,换言之,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根本难以支撑社会的高福利,政府只好借债度日,国穷民富乃是这些国家的一大特色。在社会主义色彩浓烈的欧洲,不仅上述南欧国家,即便是富裕的北欧、西欧诸国,包括丹麦、挪威等,实际上都不同程度遭遇高福利尾大不掉的长期困扰。在民主或代议民主之下,政客要得到更多的选票,就必须得到尽量多的民众支持,不断慷国库之慨大撒金钱,当然皆大欢喜,是获得选票的最有效手段。久而久之,无论民众还是政客都形成一种惯性,不管经济局面是好是坏,社会福利只能增不能减(谢无愿,2011)。
这两个方面在性质上是矛盾的,至少从政治逻辑上看,要排斥某些经济自由成分,政府政治上必须加大福利主义及经济社会主义的政策取向;而要解开政府债务死结,却又必须更新既有的制度,排除民主运作中为无原则福利主义所支配的习惯。美欧如今均陷入这样的艰难纠葛,当然二者的境遇有明显差异,在美国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前者,在欧洲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后者。这两个难分难解的方面,使美欧社会在两难中陷入严峻的考验。
政治没有万全之策,制度不会完美无缺。自由或平等、效率或公平、程序或实质、放任或干预,何者为先?如何更佳?偏重某一端,是左右两派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永无结局的争执。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论争,两端理论都可以逻辑自洽,但都不具有可证伪性。重要的是创造出一种机制,能保证政治环境不至于永远只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另一部分人,能对各种价值取向开放,社会系统可以在左歪右倒中保持动态平衡。
四、 第三条道路的福利思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这就是“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一度占据主导地位,曾使欧洲各国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陷入困境。其中又以英国工党的状况更为糟糕,在在野30多年后,其影响已日渐衰微。而新自由主义在它占上风的20年里既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成就,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后遗症。欧洲各国民众普遍要求消除新贫困和社会犯罪等现象,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已经十分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在90年代后期再度上台执政后,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英国首相布莱尔上任伊始,就提出要革新社会民主主义,摒弃老左派的国家管制、高税收等做法,从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股巨流中吸取活力,走第三条道路。布莱尔的主张一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立即纷纷响应。随着英、德、荷、意、法等国的工党、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先后获得执政权,以及获得执政权的这些党的领导人在1997年至1999年间三次召开第三条道路研讨会,第三条道路的思想便广为传播,其政策便付诸实施。
第三条道路理论寻求的是超越传统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与新右派之上的中间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它嵌入到了国家主义结构中,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以知识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而新自由主义遭到拒绝,是因为它造成了混乱,损害了社会道义基础。第三条道路是糅合了双方的优点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哲学,但一般认为,第三条道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其不涉及政治运动。虽然第三条道路有时被人说成是“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但支持者认为,第三条道路采用市场和私人部门的解决办法,和社会主义传统不再有多大关系。
以布莱尔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福利改革的新思路、新观念。主要内容有:
第一,在主张维护经济自由的同时,把平等和社会正义当做与自由同样重要的原则。要实行一系列福利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扩大社会福利,既强调国家干预不可或缺,是自由与繁荣的必要条件,以克服市场自发运行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又要求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
第二,以争取社会民主、经济民主作为策略,把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国家不再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工具,而成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权力共同体”。
第三,倡导积极的福利,主张用“社会投资型国家”来取代“福利国家”。第三条道路主张对福利国家进行根本的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压缩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变消极的福利制度为积极的福利制度,使之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平衡。对于社会分配制度,第三条道路强调不能靠事后的社会再分配来谋求结果平等,而应该把再分配的重点放在提高教育和职业培训、扶植青年和弱势集团、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上。
福利政策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就业导向的转变。“第三条道路”主张应改变过去固守的传统观念,转变就业机制,把过去“追求平等的目标”的就业导向转向“创造平等的机会”,强调要以更多的协调、更多的改革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制定能够鼓励工作自立、放弃依赖社会的政策,推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为人们创造更大的经济活动空间,使每个公民既愿意行使劳动的权利,又有发展的机会。为有劳动能力者提供工作条件,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懒汉。解决失业问题的重点不再是简单发放救济金,增加失业补贴,而是变社会支出为社会投资,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
2.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第三条道路”从积极福利理念出发,主张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废除福利国家的按固定年龄强制退休制,把老年人视为一种尚能承担责任的资源而不是只知享受权利的负担,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能工作的继续工作。在养老金来源问题上,将养老保险私有化和社会化,鼓励建立社会性的养老保险公司,提倡个人向其投保,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主张企业、个人、整个社会也都参与,使国家甩掉包袱,推动经济增长。
3.福利对象的扩大。“第三条道路”认为,福利制度不仅要为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和必要的技能培训,还应关注庞大的中产阶级。只有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应该给中产阶级的中下层以抗拒风险的信心,关心其中的上层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并引导其给社会整体以更多的关爱。
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型国家的转变,体现了“第三条道路”对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国家功能的重新定位,认为国家仍然对重大事务负有责任,但解决的方式是通过发挥政府及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来完成。尽管构建社会投资型国家的改革理论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但是,它表明了一种新的开明态度,即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采取灵活有效的做法,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