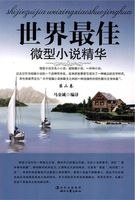又是一夜连绵雨,偌大的上海城到处都是撇不开擦不净的阴湿,于公馆本有着最美的空中雨阁,现时却已成了一座围中死城,到处都充斥着摧枯拉朽之气,独有那不知人间冷暖变数的夜明珠还依旧在顶尖上转着,亮着。
富丽的洋式别墅像是一夜之间换了模样,主人没了踪迹,来不及逃的下人们全都被关进了漆黑的偏屋里,长排的持枪队伍包围着,似猎犬一样紧盯着,让人不禁发颤。
福兮抱着刚刚出生的小少爷,手上还残留着接生时沾上的血,心里恐慌到了极致,直到找到一个旧木桌依靠方才稍稍平静些。大铁门倏地被人推开,耀眼的光直刺得人睁不开眼,她下意识地去挡,指缝间见是一个身材挺拔的男子被人簇拥着走了进来。
那人身着黑色长衣,脚踏一双铮亮马靴,眉头紧皱,凌厉的眼神似是能将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看穿。福兮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下意识地想要往人后躲,只是刚退了一步,未及定身,便被人盯住了,一把枪实实地抵在她的脊梁上。
“别动!”
她啊地叫了一声,又战战兢兢地回过头来,见那男人已经看向了这边,她魂魄都要被吓散了,喃喃道:“我不动,我不动。”
那执枪的随从见那男人眯着眼睛看那孩子,便上前对他低声道:“这孩子是夫人临走前亲自接生的。”
福兮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方才知道原来这就是他们于家心狠手辣的独狼姑爷,她下意识地将孩子抱紧了些,然后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哀求道:“姑爷,姑爷您行行好,小少爷才刚刚出生老爷太太就没了,您就放过他吧。”
他突然走上前,发狠地拔出腰间的枪来,旁边的下人吓得抱住了头,呜呜哀求。他的声音嘶哑,像是发怒的豹子,道:“说,她去了哪里?”
楔子知道他问的是大小姐,福兮赶紧道:“走了,小姐拿着四姨太给的船票早就走了。”
他的眼睛似是能喷出火来,将抢指在她的头上,“是去哪里的船票?”
福兮摇着头,哭道:“姑爷,福兮也不知道啊。”
他勃然大怒,抬手将摆在旧木橱上的一对白釉红狮贯耳瓶打得粉碎。人群里响起一声声尖叫,他极不耐烦地对唐汉生道:“把这些人全部关进巡捕房大牢里!”
唐汉生道:“是!”
侍卫进来拉人,福兮抱着孩子也要被带下去了,他却倏地伸出手来将她拉住,将孩子抱进了怀里,声音冰冷,“孩子留下,我就不信她能狠下心不管这孩子的死活!”
一束刺眼的车灯光由远处照射到他脸上,门外的人条件反射地拉开了枪警戒。一辆黑色的小汽车直直地冲了进来,石子路边的倒垂灯透过车窗照清那人的脸庞,不禁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纷纷向后退了几步。
仇少白抬起眼来看,嘴角轻轻上扬,他到底还是赢了。
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犹如一张单薄的蝉翼宣,在这冷意袭身的雨夜摇摇晃晃,唯独那眼神透着一股坚定。
他依旧是笑着的,抱着那孩子走上前去,用再平常不过的语气道:“回来就好,穿得这样少,仔细回头生病。”说着,便回头叫唐汉生,“车上有常师傅刚做好的荷叶披风,去给夫人拿来。”
唐汉生尚未动,她却倏地从身后拿出枪来,开口便是冲天斥地的恨意,“仇少白,你我的情义早已被你一点点一丝丝地毁尽了!收起你那假惺惺的关心!”
在场的人不禁面面相觑,怀中的孩子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呵斥而大声啼哭起来。她将枪口对上他的双眉,“把孩子还给我!”
他当真就将孩子小心翼翼地交到了她手上,又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她身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模样,道:“要汉生去拿披风你又闹脾气,这孩子总是怕冷的,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好不好?”
若是往日,她怕是又被他的柔情欺骗了,然而此时,她却笑出声来,“家?我的家不就在这里吗?”复又恍然大悟的样子点了点头,“哦,我记起来了,它已经被你毁了,我的家已经被你仇少白毁了!”
她的双目中渗出红血丝来,只让他的心跟着生疼,却未发现她的手指竟已扣上了扳机,让所有人都未反应过来的一枪,直直射进他的身体。
砰!
那样的清脆,就如是将万支炮信子齐时扔进了这烟雨迷蒙的夜,决绝而骇人。
身后的护卫当即又齐刷刷地举起枪来。他倒退几步,怒道:“把枪放下!”
唐汉生上前扶住他的身子,却被他摇手推开。于初阳单手抱着孩子,举着枪一步步退回到车前,“仇少白,这一枪,是你我的义绝恩断!”
他胸前的血汩汩地冒出,染红了素白衬衫,他轻笑,“真是个傻丫头。”
她不想细念他的意思,复又合上保险,唐汉生惊道:“夫人,不要!”
她却是仿若未闻。
砰!
“白爷!”
守着的人怎么能放任有人这样对他,复又举起枪来。仇少白的眉间已渗出汗来,却依旧挥手,“别开枪!”
“仇少白,我真想就这样杀了你,第二枪,是你我的血仇不共戴天!”
砰!
“第三枪,你我此生孽结,来世莫纠缠!”
他算了她一辈子,赢了她一辈子,这最后一场,是输是赢,她赌的皆是自己的命。仇少白下了禁枪令,所幸她终是赢了,便在所有人的目光下极快地发动了车子离去。
她赔上了这辈子所有的爱与恨,向他开了这狠毒却终是不致命的三枪,那三颗冰冷的子弹,亦在同时全数射进了她的心脏。车子经过他身的身旁,她的眼泪悄然滑落。终了,终了,这辈子,下辈子,她都不可能再回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