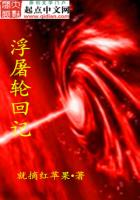孝宗穆皇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
赵主鉴使乐平王苞、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夜攻石闵、李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惧,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杀苞。
石鉴即位,对石闵倒是没有放松革命警惕,采取的策略也不算错,先抚后剿,先麻痹后下手,先封石闵为大将军,武德王,比原来的“武兴公”高了一个档次,而且把“兴”改成“德”,这些事都似乎考虑得很细致。
石闵和大司空李农在混乱中结成一派,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汉人这就不敢肯定了。当时石闵、李农集结在石遵的琨华殿,想来当时邺城一片混乱,石鉴决定浑水摸鱼,派石苞、李松等不打旗号,不亮牌照,夜攻琨华殿,结果没戏。石鉴也好玩,假装不知道这回事,把干脏活无果的石苞、李松等全部杀掉,准备来个死无对证。
在襄国,有石虎的另一个儿子石祗联络姚弋仲、蒲洪等,誓师共诛石闵、李农。在邺城之内,石苞、李松失手以后,“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紧接着,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铢等帅羯士三千,亦欲诛闵、农。
石闵联合石鉴杀死石遵,这是标准的军事政变。此后,事态很显然地向民族对立的方向发展了,导因也可能是石闵的部队民族特性太明显,不管拥护石遵的还是拥护石鉴的,他们对这支杀入宫禁的汉人武装突然感觉到是一种种族威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羯人可能没有这样的说法,但一定有这样的共同心理。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一旦以种族划界,这个首要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石闵和他的敌人很快就意识到,原来以族划界是这么简单明了,对于对立双方的领袖来说,这种族群对立的好处是战争动员极易进行,不利之处就是没有战略意义上的“朋友”,谁都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对立的敌人。
面对众多的敌人,石闵作出了一个可能是必需的选择,那就是动员汉族民众参与战争来扭转自己势单力薄的不利局面。石闵下达《杀胡令》,解除汉人不能自由进出邺城的禁令,宣布“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门”。
民族压迫积累的仇恨,恶劣政治积累的民怨,由《杀胡令》激发起来了。此令一出,“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亲帅赵人以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或高鼻多须滥死者半”。
由仓促自卫迅速演变成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事起猝然,但结果却是事在必然。石闵动员汉族民众对胡羯进行了空前的报复性屠杀,石虎十几个儿子,几十个孙子,除了他自己杀的,兄弟们相互杀的,剩下的最后全让石闵杀了。仅在邺城,被屠杀的胡人就有二十万人。在此后一两年间,石闵和胡羯联军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争,通过战争石闵几乎把原汉人居住区的匈奴人和羯人杀害殆尽。羯人本是小族,人口并不多,遭此一劫,就此灭族。
石闵后来建国号为魏,恢复汉姓冉,我们得改叫他冉闵。冉闵的历史地位,也和好多历史人物一样,因为当下价值观和政治需要的变化,他们的地位也在变化,再次证明“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冉闵现在被称为民族英雄,起码在一些论坛上是这样认为的,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冉闵,汉民族就可能被胡羯灭绝了,中华民族也就没有今天了。纵观世界历史,确实有不少先进的文明被中断了,他们几乎都是被野蛮的民族灭绝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问题,民族之间也一样,文明遇见野蛮,也是有理说不清。不过“如果”和“假如”不能作为证据,如果没冉闵,胡羯是不是一定能灭杀江北江南的全部汉人,这个大可存疑。
一些人对冉闵的敬仰和崇拜,产生于这样的现实背景,他们对当下复杂的国际问题有些不耐烦,希望能有一种痛快的解决方式,冉闵的方式当然是一种痛快的方式。我不认为冉闵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在做石虎的干儿子的时候,民族意识民族自觉在哪里?他想取石氏而代之,也完全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思想,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与民族解放没有关系。他最后是在胡羯的包围之中,突然意识到“民族主义”可以救自己,非要说冉闵是长期潜伏在胡人内部,就等着机会解放汉人,证据似嫌不足。
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都是在被剥削和被压迫过程中产生的,被《杀胡令》动员起来的广大汉人民众有这个觉悟,冉闵本是“民族异己分子”,他是在利用他们。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价值标准来谴责这场民族大屠杀,但是这次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历史定位不能再拔高了,虽然汉人是为了反抗胡人的奴役而对胡人进行杀戮,但不能作为“正当理由”延续到今天。
冉闵作为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不具备穿越历史的价值,不具备现代价值,那些成天叫喊“中美总有一战”、“中日总有一战”的人,最好再找另外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