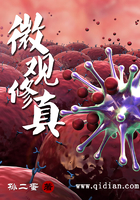野餐前那个星期一的晚上,玛瑞拉满面愁容地从自己的房间里下来。
“安妮。”她叫那个小家伙,后者正在一尘不染的桌边剥豌豆,用戴安娜所教的那种活力和感情哼唱着《榛树谷中的奈莉》。“你看到我的紫水晶胸针了吗?我记得昨晚从教堂回家后就别在针垫上了,但哪儿都找不到。”
“我……下午你去互助社的时候我看见了。”安妮有点儿迟疑地说,“我路过你的房间,看见它别在针垫上,就进去看了看。”
“你动了吗?”玛瑞拉严厉地问。
“动……动……了。”安妮承认,“我拿起来别在胸口,只是想看看好不好看。”
“你根本没权利这么做,小女孩这么好事很不应该。首先你不该进我的房间,其次你不该随便动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把它放在哪儿了?”
“哦,我把它放回梳妆台了。我就戴了不到一分钟,真的。我不是故意乱动的,玛瑞拉。我没想到进你的房间戴胸针是错误的,不过我现在知道错了,以后再不这么做了。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从不重犯同一个错误。”
“你没有放回去。”玛瑞拉说,“梳妆台上压根儿没有胸针。你把它拿出去了还是怎么着了,安妮?”
“我真的放回去了。”安妮说得很急切——很冒失,玛瑞拉想。“我不记得是把它别在针垫上还是放到瓷托盘里了,但百分之百肯定把它放回去了。”
“我再去看看。”玛瑞拉决心公正地处理,“如果你把胸针放回去了,那它还会在那儿。如果它不在那儿,我就知道你没有放回去,就是这样!”
玛瑞拉回到房间仔细搜查了一遍。梳妆台上没有,她认为有可能放胸针的其他地方也都没有。胸针真是找不到了,玛瑞拉回到了厨房。
“安妮,胸针不见了。你自己承认你是最后一个动它的人,那么,你把它怎么样了?马上说实话。你是不是拿出去弄丢了?”
“不是,我没有。”安妮神情庄重,迎着玛瑞拉的怒视,“我绝没有把胸针带出你的房间,这就是实话,就是上了断头台,我也是这句话——虽然我不太明白断头台是什么。就是这样,玛瑞拉。”
安妮的“就是这样”只是想强调她的声明,但在玛瑞拉听来就成了挑衅。
“我认为你是在对我撒谎,安妮。”她严厉地说,“我知道你在撒谎。好吧,你要么说出实情,要么什么也别说。回你的房间去,不认错就别下来。”
“要我带上豌豆吗?”安妮顺从地说。
“不用,我自己能剥完。按我说的做吧。”
安妮走了之后,玛瑞拉心烦意乱地干着家务。她在担心自己的宝贝胸针。要是安妮弄丢了该怎么办?谁都能看出是她拿走了,这孩子却还否认,真是太可恶了!表面上还那么无辜!
“我不知道怎么没有早看出这一点。”玛瑞拉心神不安地剥着豌豆,想着,“当然,我想她不是存心要偷或怎么着。她只是拿走玩玩,可能是丰富一下自己的想象。一定是她拿走了,这很明显,因为照她的说法,她进去之后、我进去之前,那房间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现在胸针不见了,这是确定无疑的。我猜是她弄丢了,因为害怕被罚就不敢承认。想想她竟然说谎,真是太可怕了。这可比她的坏脾气严重多了。家里有个不能信任的孩子,那我肩头的责任可就大得吓人了。狡诈和不诚实——这就是她的表现。我得说,这比丢了胸针更让我难过,如果她说出实情,我不会这么难受。”
那天晚上玛瑞拉不时回房间找胸针,却毫无结果。睡觉前她去了东厢房,但仍然一无所获。安妮一口咬定她不知道胸针的事,但玛瑞拉却愈发认定她知道。
第二天早上她告诉了马修这件事。马修惊慌失措、迷惑不解,他并没有立即失去对安妮的信任,但不得不承认情况对她很不利。
“你确定没有掉在梳妆台下面?”这是他能提出的唯一想法。
“我挪开了梳妆台,抽出了抽屉,找遍了每一条缝每一个洞。”玛瑞拉肯定地回答,“胸针不见了,这孩子拿走了它,还撒了谎。这是明摆着的丑陋事实,马修·卡斯伯特,我们应该面对它。”
“嗯,这个,你要怎么做?”马修可怜巴巴地问,暗自庆幸处理这种情况的是玛瑞拉而不是他,这次他一点儿也不想插手。
“她不承认就不能出房间。”玛瑞拉无情地说,想起上次这个方法取得了成功,“然后我们再商量怎么办。如果她说出把胸针拿到哪个地方了,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但是,不管怎么说,她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马修。”
“嗯,这个,你得罚她。”马修拿起帽子,说,“我可什么也做不了,记得吗,你自己警告过我不要插手的。”
玛瑞拉觉得孤立无援,她甚至不能去找林德太太寻求建议。她一脸严肃地走进东厢房,出来时神情更加严肃。安妮坚决拒绝承认,一口咬定她没有拿走胸针。这孩子显然哭过,玛瑞拉心头一酸,涌起一阵怜悯,但她咬牙克制住了。到了晚上,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已经“精疲力竭”了。
“你不招认就不能出房间,安妮,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她坚定地说。
“但是明天就要野餐了,玛瑞拉。”安妮喊了出来,“你不会不让我去的,是不是?你会让我出去一个下午的,是不是?之后,我会高高兴兴地待在这儿,你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但我一定要去野餐。”
“你不能去野餐,什么地方都不能去,除非你认错,安妮。”
“哦!玛瑞拉。”安妮大口喘气。
但是玛瑞拉已经走出房间,关上了门。
星期三的早上阳光明媚,就像是专为野餐而降临的。小鸟在绿山墙周围轻唱,花园里圣母百合散发出的幽香飘进看不见摸不着的微风中,溜进每一扇门、每一扇窗,像赐福的神灵漫游过客厅和卧室。山谷里的白桦树快乐地挥着手,仿佛在等待安妮像往常那样从东厢房发出早安问候。但是安妮却没在窗边。玛瑞拉给她送早餐的时候,发现这孩子在床上正襟危坐,脸色苍白,神情坚毅,双唇紧闭,两眼闪亮。
“玛瑞拉,我准备招供。”
“哈!”玛瑞拉放下托盘,她的办法再一次奏效了,但这次的成功却让她感到苦涩,“那么让我听听你会说些什么吧,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