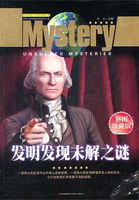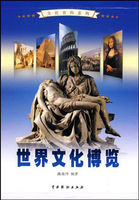工业文明的引进不但需要文化上的调适,而且需要社会组织模式上的调适。而社会组织模式的调适,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工业文明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中,整个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都不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而是为资本家的利润服务的。中国自古以来的手工业产业却没有催生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中国对于工业技术体系的引进,为什么不可以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主义倾向接轨,使之用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呢?
费孝通援引一位在江村负责蚕丝产业改造的负责人(即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的话说:“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为了改进技术,引进蒸汽引擎,必然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工厂集体劳动的变革。电力的使用,又可能使生产过程分散,从而需要工业之间复杂得多的协作。在一个集体企业系统下,生产资料和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为了生产,引进新的社会组织,变革力量也必须传授新的社会原则。在组织新工业中选择社会原则也与变革力量的利益相关。那么工业改革使谁得益呢?变革者的回答是人民。机器用来增添人类的幸福。试图把这些工具引进中国的改革者的责任,是寻找一种正当的办法使用机器。最重要的是,人不应该成为机器的奴隶。”
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年轻时一直脚踏实地地帮助江村居民进行蚕丝业生产模式和技术的改革,是一个满怀热情的社会改革家,也是费孝通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合作者和支持者。费达生的如上叙述,可以看作是姐弟俩共同的想法。费孝通姐弟俩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明确规定了机器和工业生产必须为人服务的价值目标,而不是将机械化、工业化本身看作价值。他们在这方面一直保持清醒,而不像五四时贤,为了强调工业文明对于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就不由自主地将其看作价值本身,并移植和建构一个庞大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来跟传统文化、跟底层群体的温饱和生命相对抗。
正因为费孝通和他的姐姐费达生不是将工业文明当作一种价值体系,而是当作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和生产技术体系看待,所以,在五四以来无限放大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一直是清醒的工具论者,而不是价值论者。他们对于改革者最有价值的提醒是:
不要以为工业的发展一定有利于国家及人民的。
这是对于建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崇拜的五四前贤的石破天惊式的棒喝。可惜这种后来者的智慧声音无法改变五四前贤的激进主义思潮,尤其不可释怀的悲剧性在于,费孝通的后来者也无法听懂费孝通的呐喊。
在费孝通所见证的时代,他反复警示应予避免的悲剧恰恰在他眼前发生,并且伴随他一生。一个“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的“中国工业”体系,在毛泽东时代初步建成。那个时代以所谓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让农民的劳动为工业起步完成原始积累。
他们被集中在人民公社,甚至缺乏基本的人身自由。他们没有权利支配自己的产品,除了留下口粮,其他全部由政府垄断。在若干特殊的关键年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留下口粮,不得不大批大批地饿死——省下粮食供国家出口,以便早日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外汇积累。他们还有十分繁重的徭役,无偿参加铁路、厂房、水库等等工程建设。
再后来,中国在低端制造业上突飞猛进,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加工厂。原先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和来自乡村的破产农民成为这些工厂的劳动力。他们每天十几个小时地伺候着不停运转的机器,工资不但十分低廉还常常被黑心老板拖欠或者赖账,其他权利更加得不到保障。管理部门只对工厂的GDP和缴税感兴趣,对于生产者的生存状态无暇顾及。广大底层群体再一次为中国工业的腾飞付出代价,成为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造成底层群体这种悲惨命运的现实因素极为复杂,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五四时贤所建构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在造成这种悲剧局面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它的不正当性缺乏足够的反省,对于它的悲剧性缺乏足够的规避意识。我们几乎是理直气壮地“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来建设中国的工业体系,来成就中国的强国梦想,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却是起源于五四时代建构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崇拜。此后的民族选择,一直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延伸。
按照西方人建构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无论是中国清末的闭关锁国还是甘地的纺纱织布运动,都是保守的、反动的、逆历史潮流的。可是,殖民者逼迫印度社会走向“逆工业化”的地狱之路,那不是更为反动、更为逆历史潮流吗?可见那些推销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西方殖民者,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言说当作价值准则。实际上,他们一切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有千千万万种批评,其中排在最前列的两点批评是:封闭、停滞。为什么他们最看重这两条呢?因为中国的封闭不利于他们进来掠夺,因为中国的停滞不利于他们把中国卷入他们设计好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而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所有东方世界的任务就是像工蚁一样世世代代为他们劳动。他们将建立这个经济体系的过程,命名为“全球化”或者“世界化”过程。由于有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做基础,他们推销这个后殖民时代的经济体系极为方便,能够得到殖民地精英群体的倾心拥戴。1934年,胡适指出:
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
世界化的主张。……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上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全盘西化和充分世界化进程扫清了障碍,中国社会“封闭、停滞”状况出现了变机,中国从此进入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历程。
五四前贤对于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崇拜与推广,在20世纪80年代,被当时的精英群体放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尤有甚者,80年代的知识精英早就没有了五四时贤对于殖民掠夺者的痛恨和警惕,于是他们在崇拜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同时,对于生产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那些工业强国滋生起国家崇拜。
从20世纪初对于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崇拜,发展到20世纪末对于体现工业文明意识形态的西方国家的崇拜,中国精英群体的百年历程是一个精神日渐萎缩的历程。一百年来的民族苦难和血泪,没有让这个群体强健起来,却让他们黯淡下去。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精英群体跟主要由底层群体承担的民族苦难之间始终留有一丝裂痕。印度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印度精英群体跟民族一起站立起来。当中华民族日后真正崛起时,中国的精英群体很可能只有怀揣着对于西方文明和西方国家的崇拜而一天天趴下。起而担当民族领导责任的,很可能是另一个群体。
我说的是日后,而不是当下。因为在当下,中国精英群体对于西方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和西方国家的崇拜依然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再一次被中国精英群体赋予价值意义,这种错误的价值观至今还在误导着中国社会的GDP崇拜。
持续百年的工业文明意识形态崇拜运动,大大加速了中国进入这个以西方殖民强国为利益核心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进程。这个进程怎么看都有一点主动接受掠夺和控制的意味,我们姑且将此理解为一个苦难民族的无奈选择。当我们心甘情愿地完全“融入”那个体系之时,终有民族觉醒、文化觉醒的一天。到了那一天,我们一定会挺直腰杆扞卫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文化尊严,一定会放开眼界来制定我们的国际战略和文化战略。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崛起的艰难途程之中,它在文化上、精神上的觉醒和崛起,却还得稍待一些时日。我们虽然心情急切,却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