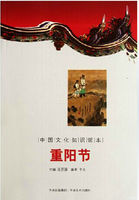不过是为西方非文化群体想象中国和中国人提供的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包括材料和结论,以及材料和结论的关系。虽然史密斯具有漫长的中国经历,可是这并不能保证他能够准确地描述和诊断中国。他从来没有把笔下人物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家庭环境、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予以观察、理解,而只是就那些人物的单一行为表现予以记述和介绍,因而他的所有描述和谈论都是孤立的,跟中国社会、文化基本上无关。作者企图用这些材料来建立一个文化上、国民性格上与西方迥异的“中国”形象,那只能借助主观的想象。西方人群根据这么一个想象出来的文本媒介来展开对于中国的分析和理解,与实际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只能相距十万八千里,只能时不时地推导出一些充满误解、歪曲、歧视、蔑视的结论。
根据同时代人的描述,史密斯是一个性格极其活泼、夸张,言谈追求幽默效果,行为举止不惜以滑稽方式引人注目的人。曾经跟晏阳初一起从事过平民教育的中国教授李景汉说,他“有不少的机会,得以亲聆明氏(史密斯中国名字为明恩溥)的讲演”。史密斯讲演时,“全身随时都是表情,往往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可谓出口成章,威威动人,使听众永无倦容。他是一个大演说家。及到与他接触谈话,则又发现他不只风趣横生……”
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傅晨光先生说:“明氏有敏捷的机智,有锐利的眼光,有作文的天才,长于幽默与滑稽……真可以使他成为世界上大幽默家而有余。”他是“一个人类之讽刺的观察者”。
长于作文、长于幽默与滑稽、大演说家、大幽默家、讽刺的观察者、双手同时以指作声助其语势……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史密斯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公共活动家和喜剧演员,是一个表演性很强的时尚人物和艺术家的结合。如果要在当下语境中寻找类似的角色,只有电视上的小品演员、少女歌手、时装模特以及用说书的风格介绍历史知识的学者等等少数时尚明星堪可比拟。实际上,自从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以来,传教就一直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时尚。
用这样的心态和风格从事艺术事业和公共演讲当然是称职的,但是,用这样的心态和风格从事学术研究,有时候恐怕就难免要牺牲若干客观性、准确性、朴实性。
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和风格研究一个民族,可以肯定地说,那是有失恭敬的。
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个功利的文本
“即使其中若干条可能在中国人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可以称之为中国人的特性,那也不是史密斯这种材料、功力、方法和功利心所能证明的。”——我刚才写下的这个句子中,有“功利心”这个词组。这是我对史密斯写作态度的基本判断。
史密斯作为一个传教士,他来中国的目的非常明确也非常单一,那就是把上帝的爱送给中国人,用基督教拯救愚昧的中国。
不难想见,来到中国后,史密斯看待一切问题,一切人,一切现象,都是用这种传教士的眼光,也就是看它跟基督教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他评价一切问题,一切人,一切现象,也都是用这种传教士的标准,也就是看它接受基督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够跟基督教沾边的,具有接受基督教的可能性的,他就给予好的评价,反之,就给予愚昧的、落后的、邪恶的评价。
中国对基督教的接纳速度,离史密斯等传教士的要求永远还有巨大的距离。为了加快基督教的传播进程,史密斯等传教士喜欢把中国社会的一切都说得一团漆黑(因为没有上帝之光的照耀),而驱逐这一团漆黑的唯一可靠力量就是基督教,就是上帝之光。这样的宗教使命,成为史密斯的功利目的,这样的功利目的,成为史密斯一切言行的出发点。
所以,《中国人气质》所罗列的中国人的26种特性,并不是一个人文学者的文化诊断,而是一个基督徒用心良苦的布道的铺垫。当我们跟着史密斯神父爬完这26级愚昧、黑暗的台阶之后,第27级台阶突然无比宽广、一片敞亮,因为史密斯神父在那里迎接我们,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而站在史密斯神父身后的,就是上帝本人。
《中国人气质》一书的结构,也是为史密斯的传教意图服务的。书的主体内容是描述中国人的26种特性,书前的“绪论”和最后一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的需要”像两张包装纸,将全书的内容包装为一个整体,所凸显的主题还是那句老话:中国需要上帝的拯救。
“绪论”是第一张包装纸。这张纸上写着:“当阻止我们西方人自由进入这一帝国内地的障碍被扫除后,西方基督文明将会发现,展现在它面前的并不是一个野蛮的、尚未开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衰弱不堪、弊病重重的古老文明。不过,这一古老文明仍有一些方面应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将到来的文明竞争中,西方基督文明将不得不在这一富有怀疑精神同时又极为聪明的民族中大力鼓吹升入天国的信仰,使他们相信在公共与个人的伦理道德上,这种信仰能比眷恋尘世的低级信仰提供更有效、更切实的保证。唯有如此基督文明才能为自己在中国开辟一条通道,使自己获得进一步的拓展。”这段话是埃尔金爵士在上海商会的讲话,许多年过去之后,被史密斯引来作为他第一本着作的“绪论”的结尾,因为他认为这段话是“正确的中肯的”。
作者一面强调自己在中国仅仅留居过两个省,不足以了解中国的全面情况,一面又说:“书中所讲的许多特性不仅仅来源于作家个人的经验,而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时候所得经验的总和。”这就是说,这本书是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几百年来所有经验和研究的集中表述,那当然是权威中的权威,无需加以质疑。
作者为了避嫌,特地说明本书“目的不是企图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朴实地报告他的所见。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气质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造的推论,并不假定中国人全然需要基督教”。但是紧接着的一句话却说:“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治疗那些缺陷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作者将他隆重推出的结论含蓄地表述为“一个有趣的问题”,多少显示了他作为幽默滑稽大师的特性。但是这种含蓄的表述方式,这种幽默滑稽大师的风格,即使是身陷此种缺陷中尚未得救的愚昧中国人,也不难读懂。
本书最后一章是第二张包装纸,这张纸上所写的关键词,上文仅仅引述了一半,为求意思完整,我把刚才隐去的那一半补充进来,将整个句子完整地引用一次。作者说:“中国需要的是公正,为了获得它,中国必须有一套上帝的知识,必须对人有一个新的概念,必须重新认识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需要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在家庭和社会中,注入新的生命。那么,就会看到中国的各种需要化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这就是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的一种需要。”
为什么这些在黑暗的东方挣扎的野蛮人,一旦有了基督教就能得到拯救呢?在作者看来,野蛮的东方没有一种力量吸引人们追求光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则时时都在引领人向上飞升。史密斯郑重地说:“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东西不多,只是人格和良心。甚至可以说,两者是一个东西,因为良心即是人格。人们曾评价一位着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就像他的乐器一样——规矩,正直和高贵。在中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物吗?……基督教文明的最美好产物,是它所创造的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罕见……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这样的人生,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他人的利益……”
看来,史密斯写作这本基于传教目的的通俗小册子,是为了引领中国人“创造完美的人生”,以便懂得“把真诚的爱献给了他人的利益”。当然,这“真诚的爱”只有通过献给上帝才能“献给他人的利益”。
此书在西方世界受到欢迎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教徒,都是潜在的传教士。他们看待东方的眼光,看待异教文明和社会的眼光,跟史密斯大致相同。凡是讨论野蛮人的愚昧、黑暗等问题,他们之间太容易沟通、共鸣。
但是在非基督教社会,人们即使认可史密斯的描述有几分诚实,也无法完全接受它的布道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