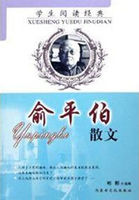徐友渔:两者兼而有之。我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也从马克思的话中得到鼓舞:一个民族要想生存下去,就一天也不能停止生产。我知道,生产主要靠科学技术、靠知识。我坚信知识总会有用,其实,即使没有1977年的高考,我也自信不会前途无望。不过在当时知识一分钱也不值。我1972年回城进厂,不久厂里一台从日本进口的精密磨床使用不好,需要翻译说明书,设备科的人请一位学过日语的技术员翻,他们居然不知道说明书是英文!我利用工余时间花一个礼拜就把厚厚的一本说明书翻好了,交给那个只会日语的技术员,没有一个人来谢一声,更不用说考虑发挥我的一技之长。
但更深层的动力是精神上的,我当时认识很明确:搞“文革”的那帮人想把所有的人都弄成愚昧无知,成为机械服从的工具,他们才好统治,我必须自救。我曾和一些朋友激烈地争论,我批评他们不看书,不学知识,我话说得很过分,我说,喜儿被黄世仁凌辱了还要反抗,要报复呢,我们被剥夺了受教育和求知的天生权利,难道就任意给搞成白痴,怎么一点血性都没有?其实,他们也有所追求,他们认为,“文革”把人弄得残忍、互相仇视,他们追求善与美,没事就聚在一起听音乐,看风景,说窗外河边的树丛像苏里柯夫笔下俄罗斯的白桦林等等。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也不错,但那总带有“享受”的味道,我觉得求真更难,要与自己的惰性过不去。后来恢复高考,他们中有人惊呼我有先见之明。我的追求被这么实用性地理解与表扬,真使我哭笑不得。
学无止境
徐晓:对许多新三届学生来说,1978年开始的大学生活是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一个新起点,是一个大熔炉,许多人在这里锻炼成才。我采访过许多人,他们回忆起当年岁月就激情满怀、感慨万千,你的感觉如何?
徐友渔:我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当然,那时的政治生活是很令人兴奋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批改革的思想先锋在大声疾呼,首批出国考察的人带回关于南斯拉夫和东欧改革的信息,关于西方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还有卢新华的《伤痕》引起的轰动,等等。也有很多琐屑的事情,比如新学生进校后瞧不起原先的工农兵大学生,双方不断摩擦、冲突,还有就是有的同学觉得自己的地位大变,想抛弃在农村或原单位的配偶,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当时看过一篇小说,好像叫《杜鹃啼归》,就是写这类事情,很真实感人。我那段时间,只觉得累,疲倦得要命。进校前小孩刚出生,马上大病一场,我日夜守候,进校后整日精神恍惚,上课只想瞌睡。二是功课重,国家急需教师,学校决定把大班变成快班,三年学完四年课程,用最难的教本,派最好的教师,很多人跟不上,他们上学前在本单位都是骨干,感觉良好惯了,一下子变得悲观苦闷。当然,我对大学本科期间感受不深,主要是我只读了一年就报考研究生,第三学期既要跟上功课,又要准备新的考试,小孩又住院动手术,只觉得累得天昏地暗,心力交瘁。
徐晓:你的专业是数学,怎么报考哲学专业研究生?
徐友渔: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大学报的是生物化学,差点落榜,弄了个走读。但我本来就极喜欢数学,所以接受既成事实一点不痛苦。我自学数理逻辑,第一年研究生这个项目较多,第二年基本上没有,我于是改选相关学科。
你知道,我后来的专业是研究罗素的哲学,没有数学基础是不行的。考研究生时,我觉得自己的兴趣、把握不限于一两个科目,对于一直苦心准备的人来说,社会条件稍一松动,机遇就有的是。我考研时的选择,以及进去后具体专业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深思熟虑,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我觉得,对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可以做的事很多,我认为改变思维习惯很重要。普通中国人的思想往往来自文学艺术、人生体悟,而不是科学和理性,所以往往是神秘主义的、野狐禅一类的东西泛滥,我后来在一部专着中说,中国人应该学习和养成缜密地思维、精确地表述的习惯,清除那种海阔天空、以气势和文采而不以把握问题实质取胜的论述习惯。基于这种考虑,我研究当代英美哲学,目的是想弥补中国传统思想科学理性的不足。
徐晓:你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还是十分高兴吧?
徐友渔:心情很复杂。这个结果应该是在意料之中——因为我从1966年起周围的人都不学习时从未中断过学习,但又像在意料之外——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好消息往往是假的,而坏消息却是真的。有亲友祝贺我时不无遗憾地说,你那个中国社会科学院,没有“社会”两个字就太好了。我明白他们的意思,积几十年之经验,搞社会科学危险。当然,我更明白,不少人对社会科学是否真是科学,深表怀疑。尤其是哲学,在不少人心目中,不过是耍嘴皮子,为任何一种政策作论证。不过事实确实如此,同一些人,证明大寨道路唯一正确可以,证明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也可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搞哲学,往往强调自己大学念数学。如果有人挖苦说,哲学就是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我只好谦卑地声明,我力争当一个例外。当然,我内心深处没有一点自卑情结。中国人很封闭,他们不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哲学是一大套学问,受人尊敬,并不是宣传。
徐晓:你念研究生时情况怎么样?
徐友渔:简单一句话:乏善可陈。三年研究生期间,研究生院还没有盖起来。哲学系八十个学生,租了通县一个大车店两层住在那里。唯一正规上过的课,是每周逻辑专业的同学上两次数理逻辑课,我也去参加,上了一年。当然,说到底哲学不是靠别人传授知识学得来的,虽然没有课程拘束,我可是抓得相当紧。当然,我很不情愿始终是“自学成才”,很想上课。研究生院总部设在北师大内,借了别人一点房。那里开的外语课极好,我去上过两次,但每次单程要花近三个小时,我只好恨恨地作罢。我恐怕是命中注定什么都得靠自学,而且学一点东西要花极大的代价。我毕业拿到学位后,觉得研究当代西方哲学,不到外国去看看怎么行,于是搞英语听力和口语。别人都送到外院去培训了,偏偏我去不成。于是,买个黑白小电视,每天听Follow Me。学到1985年,一位刚从德国回来的学者在所里主事,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搞出国名额公开,凭考试竞争,我通过了本所竞争和教育部统考,去了英国牛津大学。
徐晓:你似乎很乐意在书海里泡,在知识的崎岖小道上攀登。
徐友渔:可能是性格,也可能是对运气不好的过分反应。我看到许多人靠灵感写作,靠自学艰苦卓绝地思索,但不是才气早夭就是走到旁门左道,终究不成正果。我在牛津待了两年,后来又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待一年,我深感花大力气打基础开始耗费太多时间,拿出成果很晚,但最后会感到受益无穷。我可能是在四十五岁之后才不追求像学生那样学习。我认为,灵感和勤奋,缺一不可。
为人与为学
徐晓:你觉得自己十分勤奋吗?
徐友渔:一直不,直到1985年秋天被派到河南去支教,社科院各所的人住在一起,我才惊讶地发现,那些同样是科研人员的人,竟把许多时间用在聊天、买菜做饭、打牌和跳舞上面。直到有人说,和我在一起很感不好意思,我才意识到自己比有些人勤奋。讲师团工作结束时开总结会,大家关系不错,意见提得很坦率。
我记住了别人对我的批评:工作那么认真居然不是党员,而且不写申请!我也坦率地对别人提了一种希望:既然进了社科院,就相当于运动员给选拔进国家队,恐怕大运动量锻炼是免不了的,在国际学术竞技场上,就靠我们去进球了,过小日子的习惯怕是不行的!客观地说,我很想勤奋也勤奋不起来,生活条件太受限制。
每天上午拎着菜篮子上街,洗菜切菜做饭,每天千篇一律,只好安慰自己:权当是调节脑子吧!
徐晓:你是不是觉得生活条件太差?
徐友渔:当然差,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心甘情愿。我1982年毕业,睡办公室,住鸡毛小店,后来一家人住仓库改装的平房,每天都痛感为留在北京工作付代价,住房问题十年之后才基本解决。但相比而言,北京的科研条件、文化气氛是全国最好的。我1995年当正研究员,工资说出来别人都不信,说我骗人。但我想,自己在下乡时、当锻工时发过愿,万一有一天能天天看自己想看的书,只要有基本生活条件就能满足了。实际上,我目前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是比当时设想的好,而学习和研究条件大大超出了当初的想象。只不过一般人得到之后又会要求更高,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个人可以抱“君子固穷”的态度,但从政策角度,并不赞成把搞基础研究的人弄得如此穷酸。我1994年底到海南开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单位经费花光不能报销旅费,我自己掏钱坐火车、汽车,单程就要花四天,而那些当工作人员的小姑娘都是飞来飞去的。1995年去西安开会,又说报销不了旅费,我急了,我说,说实话这点钱我出得起,但堂堂社科院是不是太没脸面了?后来好不容易弄了个特批。就个人而言,我很欣赏“淡泊名利”、“与世无争”这些处世格言,去争什么东西,很累,而且显得自己在计较什么。如果能够双手一挥,痛快地说一声:“我什么也不要,由它去吧!”那是很解恨的。但中国几十年总是斯文扫地,有时因为政治,有时因为经济。你不从每件小事上去认真计较,只图安贫乐道、洁身自好,那就只能听任世风日下,国将不国了。
徐晓:你是不是有“学术至上”的倾向?
徐友渔:学术与其他东西相比,例如政治的冲击,金钱的诱惑等等,我承认有学术至上的倾向。许多年来,我们似乎可以扞卫各种各样的尊严,但很少提到扞卫学术的尊严。学术尊严很难做到,学人的尊严也很难做到。记得我刚到北京时,曾有过短暂的精神危机。我以前多多少少把社科院想成雅典的学园,里面的人虽然不会个个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总应该有点仙风道骨吧,谁知到这里一看,简直不是这么回事,而且往往截然相反!当然,我现在不便细说,而且不一定是社科院的人的过错。我第一次出差,去开全国学术讨论会,一个女同事和她丈夫闹离婚,从办公室追到车站,大打出手,火车为此晚点十多分钟,乘客们议论说:
“还是社科院的呢!”我羞愧极了。你现在到我们院里去看看,墙壁上全是卖粉丝、海米的广告,或“款式新颖,厂家直销,欲购者到×所×楼×号房间”。我不信不搞开发就做不了学问。
徐晓:你是如何看待学者使命的?
徐友渔:表面上我做得还可以,专心致志,专业和兴趣从未变过,但内心一直有些矛盾。这是“独创”和“教化”的矛盾。一方面,研究工作的本质应该是新颖性和独创性,你应该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把属于自己的那点独特的东西端出来,留给后人;另一方面,有时我想,即便是学术,个人那点东西又有多么了不起?如果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都很低下,如果整个学术界水平都不高,你一花独放又有多大意义呢?特别是看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东西满天飞,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导师在那里误人子弟,你会觉得普及是当务之急,提高是下一步,应该让人先掌握基本的概念和知识。这时你会有老一代启蒙思想家的心态,把开启民智、介绍新知放在第一位。当然,有时会产生委屈了自己智慧的感觉。
徐晓:最后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自己新三届这段经历的?
徐友渔:像许多人一样,那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它结束了绝望和期待混杂的状态,为今后能达到的高度和成就找到了一个起点。当然,对我来说,它并不意味着展现了一个知识和思想的新天地,但对于后半生的学术生涯,它可能是一个现实的入口。我理解,对许多人而言,那是成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但我不赞成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荣辱得失作为判断历史的标准。中国要臻于理想境界,还需要不止一次的更深刻的变化,那一段拨乱反正时期,说到底也就是结束荒唐岁月,较为恢复了常态和理性。我担心,这一次变革的受惠者许多已经功成名就,满足于现状,他们开始现身说法,用赞歌和自誉代替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我想,这一代人的经历和成就能不能在历史上值得书写一笔,还得看。
原载徐晓主编:《洗礼岁月》,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