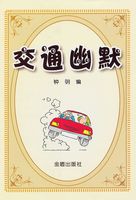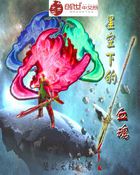下面讲斯大林与左琴科的关系。斯大林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注意左琴科的,只能做一些推测。在他当选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后不久,当时的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科夫列夫于1922年7月3日左右根据他的要求书面汇报了作家队伍的情况,列举了各个派别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说有不少人“处于动摇之中,政治上还没有定形”,并举皮利尼亚克和左琴科为例。如果斯大林相信报告里的话,那么左琴科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并不是太好的。1932年3月,国家政治保安局汇报了一些作家对政府帮助俄罗斯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儿子一事的反应,说有的人认为此事说明斯大林重视旧知识分子在国家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而有的人提起扎米亚京和布尔加科夫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结果问题得到解决的事,说他们也打算这样做,请求允许出国。在这些人当中就有左琴科。斯大林如看到这个报告,肯定对左琴科不会满意。
关于斯大林如何看待左琴科的作品的问题,没有翔实的材料可以说明。诗人丘耶夫在与莫洛托夫谈话时提到斯大林的养子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曾经说过,斯大林喜欢给他和瓦西里(斯大林的儿子)朗读左琴科的作品。他说:“有一次笑得几乎流眼泪,然后说道:‘这里左琴科同志想起了政治保安局,于是改变了结尾!’”这里讲的大概是谢尔盖耶夫后来对三十年代自己少年时代的回忆,经过丘耶夫的转述,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如果确有其事的话,那也只能说明斯大林喜欢读的是左琴科的那些充满讽刺幽默的青少年读物,并不是他的一般作品。
卫国战争爆发后,左琴科积极为报刊写揭露德国侵略者的文章,与什瓦尔茨一起写了表现希特勒的失败的讽刺剧《在柏林的菩提树下》。列宁格勒被围后,苏联政府决定用军用飞机把一批学者和文化活动家疏散到大后方。体弱有病的左琴科也被列入被疏散人员的名单中。上面说过,阿赫马托娃对苏联政府的这一决定非常感激,而左琴科则不同,他愿意与妻子和儿子一起留在列宁格勒,但最后勉强服从安排,到了塔什干。
在塔什干左琴科写了一些讽刺法西斯的文章,编过电影脚本,参加过一些社会活动。但是这里远离前线,要写反法西斯的作品缺乏素材,而且如果对战争没有切身的感受,难以引起创作的冲动,因而他一时感到有些苦恼。这时便想回过头来写早就准备写的一部题为《幸福的钥匙》的小说。他已为此作了很多准备,收集了不少材料,而且疏散时随身带着。他本来打算等战争结束后再写,只有时把这些材料拿出来翻一翻。但是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决定动笔。这是1942年下半年的事。到1943年下半年,这部改名为《日出之前》的小说发表了前七章。作者通过追述自己从童年到成年的许多生活琐事寻找不幸的原因,并且作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终于找到了不幸的根源并用理性战胜它。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的具有某种科研色彩的文学作品。
小说的前七章发表前后,曾得到一些批评家和学术界人士的好评。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人对小说提出批评,接着《十月》杂志决定停止连载。左琴科得知后,立即给斯大林写信进行申诉。他首先强调这是一本“反法西斯主义的书”,是为“扞卫理性及其权利”而写的,理由是其中弘扬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揭露了弗洛伊德的唯心主义错误。他说,《十月》杂志曾不止一次地把小说送给斯彼兰斯基院士审阅,院士认为它“是根据现代科学的材料写的,值得发表和重视”。他接着说,小说未发表完就加以否定,停止了连载,这种只根据第一部分作出评定的做法是不公平的。最后他请求斯大林读一读这部小说,或者下令对它“进行更加认真的审定,至少要审定它的全文”。左琴科不承认他的小说有问题,说其中批判了弗洛伊德的错误,因而具有“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这样说既不完全符合事实,又有些牵强附会。不错,小说里有一些批判弗洛伊德的话,但是与此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至于他提出不应该只根据小说的前半部就下结论,这样说似乎有些道理,不过小说的倾向已在前几章表现出来。斯大林对他的信没有作出反应。据左琴科后来推测,这可能是由于斯大林正忙于筹备和参加德黑兰会议,无暇顾及此事。
1943年12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题为《关于对文艺杂志的监督》的决议中提到由于监督不力,以至于“像左琴科的《日出之前》这样的政治上有害而又反艺术的作品得以渗入我们的刊物”。接着《文学与艺术报》发表了德米特里耶夫的题为《论左琴科的新中篇》的批判文章,苏联作协主席团召开讨论杂志工作的会议,会上法捷耶夫把《日出之前》称为一部“反人民、反艺术的作品”。
在巨大的压力下,左琴科被迫承认了自己的某些失误。1944年1月8日,他上书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说他仔细检查后“发现书中有重要的缺陷”,“科学与文学未能得到应有的结合”,“新的体裁是有缺陷的”。他承认“小说不应以现有的样子发表”。他还说,他为小说失败和“不合时宜地进行试验”而感到心情沉重,“聊可自慰的是,这项工作不是主要的,战争年代还用其他体裁写了很多作品”。他请求原谅他的过失,说这是由于“任务十分困难,看来我无力完成”而造成的。他最后说,“十一月底曾冒失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如果这封信已经转交,那么请设法让斯大林也知道他认错了。
而在左琴科上书后的第三天,即1月11日,日丹诺夫在一份请示发表批判《日出之前》的文章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说对左琴科“要狠狠地批,让他彻底完蛋”。于是这篇由戈尔什科夫等四人合写的题为《关于一部有害的小说》的文章便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对小说的批判进一步升温了。也许日丹诺夫在作批示时尚未见到左琴科给中央的上书,不然他的批示的语气不一定会这样严厉。
但是当时毕竟还是战争时期,当局大概考虑到在这样的时候不适于开展大规模的批判,况且左琴科又在一定程度上认了错,因此除了各报刊暂不发表他的作品以及取消他的某些待遇外,没有采取其他的惩罚措施。到1944年底,他的作品重新出现在报刊上,继续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在这之前出版社还出版他的书。不久战争结束。他大概没想到在和平的日子里一场批判的风暴正在等待着他。
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召集会议,讨论《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成为集中批判的对象。上面在讲文学政策时已对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对两人的批判作过详细介绍,此处不再重复。斯大林在会上多次提到左琴科时所说的话归纳起来有以下两点:一是指责他在战争时期当各族人民都在流血时,他没有写一行反对德国侵略者的字,却写各种荒诞无稽的东西,有的东西甚至令人作呕,这些宣扬无思想性的东西起不了什么教育作用;二是办杂志不能迎合像左琴科这样的人的口味,不能把篇幅奉送给他们,对他们不能讲客气,不是社会应当按照左琴科的想法进行改造,而是他应当改造,如不改造,就让他见鬼去吧等等。斯大林的语气十分严厉,甚至使用了骂人的语言,而且有些话,例如说左琴科战争时期没有写过反法西斯的作品,并不符合实际。
关于斯大林为什么对左琴科采取如此严厉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有各种说法。有人认为个人恩怨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根据是左琴科在1940年写的《列宁与哨兵》这个故事引起了斯大林极度的不满。这个故事写的是斯莫尔尼宫的哨兵洛巴诺夫不认识列宁,他拦住要进门的列宁,要求出示证件,列宁一下子没有找到。这时旁边的一个人非常生气,大声吆喝道:“快让他进去。这是列宁!”然而列宁制止了那个粗暴的人,出示了找到的证件,并对哨兵忠实执行任务表示感谢。故事刚发表时,其中对那个粗暴的人的外形作了描写,说他留着小胡子。斯大林认为这是影射自己,便伺机惩治作者。左琴科本人也有这样的猜测。然而即使斯大林读过这个故事并怀疑作者是在攻击他,他也不会只根据这一点在那场运动中选左琴科当靶子加以狠狠的批判。他那样做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左琴科的作品不仅不能起教育作用,而且具有很大腐蚀性,可是他在读者中影响又很大,因而需要进行无情的打击。
左琴科受到斯大林的严厉批评和辱骂后,于1946年8月27日给斯大林写信进行解释,希望求得斯大林的理解。信中讲了他的生活道路,说他“从来不是反苏维埃的人”,1918年志愿参加红军,与白军进行过战斗;说他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从来都是跟着人民走的。接着他讲了自己的创作道路,特别提到了《日出之前》,说自己曾以为它在战争时期也是需要的和有益的,因为它揭示了法西斯“哲学”的根源。他说,并不是他一个人这样认为,几十个人讨论过这部作品,1943年6月中央曾把他叫去,指示他继续进行写作,可是这些人后来改变了看法。他又特别说到短篇小说《猴子奇遇记》,说这是他为儿童刊物《穆尔济尔卡》写的,《星》杂志不告诉他就转载了。大型杂志刊登儿童读物,自然会给人以荒谬的印象。不过他保证,在这个短篇里没有任何寓意的语言和潜台词。左琴科最后说,他写这封信惟一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痛苦有所减轻,因为“在您眼中我成为文学上奸诈的人,成为低级的人或以自己的劳动为地主和银行家的利益服务的人而感到十分难受”。
1946年9月16日,左琴科的妻子薇拉瞒着他也给斯大林写信,不过这封信当时没有寄出去。到1947年下半年,当上面对左琴科的态度有所变化,归还了没收的购物卡,《新世界》与他签了发表《游击队员的故事》的合同时,她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连同一年前写的那封长信托波斯克廖贝舍夫转交斯大林。薇拉在她的这封洋洋洒洒的长信里详细地叙述了她的丈夫的生平、性格特点和健康状况以及他的创作,特别讲了《日出之前》和《猴子奇遇记》的构思写作过程,强调指出,“在他的创作中从来就没有过任何有意的‘幸灾乐祸’、‘恶意找茬儿’、‘讽刺挖苦’或‘诬蔑诽谤’,也不可能有”。信中说到左琴科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精神变态和神经衰弱症,疾病使他以忧郁的和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周围世界,因此他首先看到的是生活的阴暗的、畸形的方面,而看不到生活和人的本性中光明的、高尚的方面,在描写这些方面时他总是碰到巨大的困难。写信的人试图以此来说明左琴科为什么总是写生活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的原因,并且承认有时不免出现错误。最后她向斯大林说明写信的目的,这样写道:
“我写信的目的是为了使您相信,米哈伊尔·左琴科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反苏维埃的人,不是庸俗的和卑劣的中伤者,所有正直的苏维埃人的事就是他的事,他加以密切关注,总是想以自己的劳动给苏联人民带来利益和欢乐,他不是幸灾乐祸地和居心险恶地描写我们生活的阴暗面,惟一的目的是为了揭露、抨击和改变它。
“我写信的目的是为了使您知道真实情况,我把您看得很高很高,我把您的意见视为最神圣的东西。
“如果他在受了突然的和不公道的打击后能恢复过来,无疑将会写出我们祖国需要的和珍贵的东西,他将在您眼中完全恢复自己的名誉。我非常希望能够这样。”
无论是对左琴科本人的信还是对他的妻子的信,斯大林都没有作出反应。
信中提到左琴科与《新世界》杂志签约发表《游击队员的故事》一事。这些故事是他1944年参加了作协列宁格勒分会组织的与游击队员的会见并收集了不少材料后写的,一共三十二篇。1947年9月《新世界》发表了其中的十篇。这些故事的发表是经斯大林允许的,经过如下。1947年4月22日,左琴科给斯大林写了这样一封短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斗胆给您寄上我的一本新书。
我写它不是为了改善我的处境。我是完全真诚地并且希望给我的读者和苏联文学带来好处而写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这本书并允许它出版,我将感到幸福。
请允许我全心全意地祝您健康长寿。
米哈伊尔·左琴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