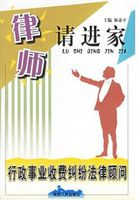为此,《人民日报》编辑部于4月5日和12月29日先后发表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与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把错误原因全部归结于个人性格相反,《人民日报》文章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并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这两篇文章中,明眼人很容易看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斯大林问题还算不上中苏分歧的焦点,最根本的还是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在当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页。]在毛泽东看来,这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子,也是中苏两党分歧的根本原因。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在起草《莫斯科宣言》时,在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达成了妥协,惟独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中共专门写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交给苏共。当时为了维护团结,这个提纲没有公开,直到公开论战时,才作为《一评》的信件公开。
中苏出现分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要求与中国国防部在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并共同使用。7月,赫鲁晓夫又向我国提出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9月,苏联在我国炮轰金门马祖时要求派苏空军部队驻扎福建前线地区。这些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方的严正拒绝。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怒。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通知苏联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单方面撕毁两国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1959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又发表声明,偏袒中印边界冲突的印方,从而把苏中分歧公之于世。中国方面认为,苏联的毁约和声明,是赫鲁晓夫为9月15日访美所献的贡礼。特别是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华,推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中共领导的强烈不满。
中苏分歧的近因是1960年6月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带头组织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将中苏分歧公开化。紧接着,苏联政府于7月16日照会我国,单方决定从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1299名),终止派遣900多名专家。中苏签订的600个合同等于作废,苏联专家撤走时还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重要设备和重要部件也停止供应,致使我国250多个建设项目处于停顿状态,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害,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苏联的这一行动,等于把两党的理论观点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两国关系从此开始疏远。1962年5月间,苏联更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制造颠覆、暴乱事件,诱骗我6万边民逃往苏联,致使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中苏分歧还有一个原因是苏共二十二大坚持修正主义纲领和大反阿尔巴尼亚。1961年10月16~31日的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把二十大以来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加以系统化理论化,概括地说就是“三和两全”:“三和”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是全民国家、全民党。中共认为“三和两全”表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已经形成。二十二大前两个月,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出席,实际将阿开除出华约,二十二大又大反阿尔巴尼亚,开始了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行动。二十二大的这些举措让中共感到,中苏由分歧转向分裂在所难免。
2.中苏论战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影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狂潮中,在人们的头脑极度发热之时,毛泽东的头脑最先冷静下来。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连续进行了8个半月的纠“左”。毛泽东用于指导纠“左”的理论,恰恰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要有关于两种公有制的理论、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理论、关于价值规律和经济核算的理论、关于综合平衡的理论等。毛泽东在运用中也从深度上和广度上发展了这些理论。但是,当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之后,毛泽东认为彭是赫鲁晓夫在中国的代理人,与彭的斗争是一场反修反资的阶级斗争,因而又把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弃置脑后,发动反右倾运动,更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错误推向极端。毛泽东的思考本来有助于中国走回到原本确定的“以苏为鉴”的道路,但是政治斗争却使毛泽东斩断了这种可能扭转局面的积极思考。
我们知道,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斯大林理论已被弃置一旁。但是在中国,中共仍以斯大林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之一,特别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虽然中国提出了“以苏为鉴”的设想,但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仍然在我国的各个领域中实行着,且呈现日益强化的趋势。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了。
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又掀起一股反斯大林的高潮,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纲领。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但也确有积极探索变革之路的迹象。由于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共产党则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中国不是与此时的苏联一道积极探索变革斯大林缔造的苏联模式的途径,反而是与此时的苏联截然相反地走上了继承斯大林缔造的苏联模式的道路上。在反右派斗争沉寂5年后,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重提阶级斗争。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在我国不仅存在,而且十分严重;阶级斗争贯穿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于一切方面;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套把阶级斗争观点系统化的理论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当中共越来越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时,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斯大林时期苏联的阶级斗争行为。
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这次全会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所谓“黑暗风”,即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在2月西楼会议(常委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对经济困难形势的严重估计。所谓“单干风”,就是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和邓子恢的支持意见。批“单干风”的结果,是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在这一决定和全会抓阶级斗争方针的指导下,农村开始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在于“铲除发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农村中这种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的矛盾在新中国成立30年来始终被作为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来对待,多少干部群众因此受到牵累。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领导创立苏联模式时政治斗争行为的重演,这当然可以说是此时中国仍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一个方面。
全会批判的“翻案风”指的是为“反右倾”斗争中错误处理的干部平反,彭德怀当年6月给党中央写的申诉信,以及所谓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特别是《刘志丹》案,株连近万人,再次开启文化大批判之门。1963年,江青开始插手文艺工作,文化专制又盛行起来。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先后就文艺工作写了两个批示,全盘否定了新中国成立17年来的文艺工作及文艺工作领导。一大批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因此受到批判。对文艺界的批判很快又扩展到学术领域,一大批学术权威受到批判。
1963~1964年的中苏公开论战,既是国内政策的反映,又不能不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到国内政策。特别是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对国内政策影响最大。二评对斯大林进行了充分肯定,表明我党要继续坚持斯大林的学说,也就是说要坚持实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三评和九评分别批评了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国内政策,认为这些政策背离了(斯大林定立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是修正主义。三评认为南斯拉夫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解散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个体经营、土地买卖租赁自由、雇工自由、农产品交易自由、国营企业工人自治、共产党改称共产主义联盟、实行民主自治等这些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无疑是修正主义的。九评认为苏联实行了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全民国家全民党,反对个人迷信,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扶植富农经济,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人性论、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议会道路等。对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政策的这些批判,无不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国内的政治取向。全国从农村到城市,无不掀起批判高潮。农村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队批“单纯军事观点”;企业批“利润第一”、“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外交批“三和一少”;学校批“白专道路”、“师道尊严”;文艺界批“黑八论”及一大堆作品;学术界批“合二为一”、“让步政策”、“非阶级观点”、“利润挂帅”,等等。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能找出一大批所谓修正主义论点可供批判。
中苏论战,说到底是中共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通过批判,更加深了中共贯彻实行斯大林领导创立的苏联模式的信念。在政治上,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突出了领袖权威,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快速膨胀,阶级斗争的范围开始扩大,而国家的法律和法制建设却在被忽视而削弱,“突出政治”被强调为“政治第一”,经济建设被摆到次要地位。在经济上,计划体制和两种公有制开始纯化,政治鼓动取代了物质刺激,对外贸易因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恶化而锐减,国家开始越来越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在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专政论开始取代“双百”方针,知识分子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而不断被斗,以思想划分阶级论成为现实。以上特征无疑反映了斯大林领导创立的苏联模式的完整轮廓,当然也含有中国式理解的引申。“文革”前的这十年,如果说始终是“以苏为鉴”的,那么前后的涵义却完全不同。前5年的以苏为鉴,中共总想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后5年则相反,是试图靠近再靠近,因为以苏为鉴的“苏”被认为是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不是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
当然,客观地说,此时中国尽管仍然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但这并非否定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无论如何,这10年的成就是大于挫折的。在政治上,国家是基本安定的,人民是团结的,精神是振奋纯洁的。在3年大跃进后,计划经济在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走上了正轨,经济建设在短暂的衰退后又开始恢复,从1963年起,工农业总产值逐年增长,1963年比上年增长131亿元,1964年149亿元,1965年351亿元,1966年299亿元(比较一下:之前的1961年比上年减少473亿元,1962年又减少117亿元;之后的1967年比上年减少228亿元,1968年又减少93亿元)。就是说,从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影响角度,我们确认了中苏论战时期中国仍然继承和实行斯大林领导缔造的苏联模式,此时中国在质疑的同时仍然继承了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许多做法,但这并不是对此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成就的否定。
在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生活有一些“创造性”,但这种“创造性”引致了社会活动的混乱无序,而不是社会制度的重新建构。仔细分析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生活仍然带有浓厚的苏联模式的特征。在经济上,中国仍然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政治上,中国仍然沿袭着苏联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并且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发起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运动;文化上,中国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样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由于,这个时期政治运动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存在对苏联模式进行继承和调整的情况,但其中的具体情况则很难在本书中进行简单的表述,故只能留待今后再专门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