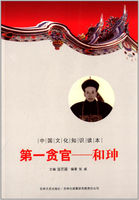在一次由地区专员、“四清”干部、村队干部、牧工代表以及社员群众参加的大会上。父亲大胆检举揭发了队干部严重贪污集体粮食和钱财的不法行为:“上级党和政府社员群众的救灾款我们屎肚子百姓没见上一分,全让队干部私分了……粮库里的几百万糜子都藏到会计的地窖里,这叫什么共产党的干部!简直就是土匪强盗,贼娃子。你们说的好听,要让群众往出抖落谁是贪污分子,啥叫贪污呀!以我马国义看,我不赞成大集体,全给贼娃子干了好事哩,全养活了懒汉二流子了……”
当父亲诉说到火头上的时候,支书马学仁实在坐不住了。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唾沫星子四溅萝卜花眼珠子差点没给气炸了。指头像雨点般地在半空中刮了一阵子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马——国——义!你——是——大——毒草!在坐的群众,你们都听见了,大家要狠批狠斗他呀!”可是,殊不知下面的群众都不理会他。早就怨声载道了,就盼望能有这一天——共产党派来个包青天,好好地讨个公道巴不得把吃人的贼娃子统统赶下去呢!
散会后,社员群众举起大拇指夸父亲,你一言我一语称赞道:“国义,你才是真正的好汉子呢,是有良心的人哪!”
“对,这一下子,才把贼婊子儿骂好了。”
“你可替群众出了口大气啊!”
果然,不过几日,真主有眼哪!一个个贪污分子全都下马了……赔款的,退粮的,抵押财产的,撤职的,让他们倾家荡产完了。
从那个大会之后,多少年来时常挂在父亲嘴边上的口头禅:“一上马家滩,看见大队黑沿锅,脚板子伸下去摸不着,下黄米儿颗颗刮的风,摆的浪,受苦的爹老子喝不上。”如此凄凉的现状渐渐地变了模样。
由于集体牧业规划的变动,我们一家又告别了依恋难舍的牧场芨芨井。搬迁到了离海子井不到一公里的北梁上。
这里也居住着好几十户人家。
为了图省事,父亲不打算新造“干打垒”的房子。有一户人家马耀礼迁到南庄那边了,干脆把房子建在人家拆迁的原址上。
父亲这样做是有一定原因的。
因为,马耀礼的父亲是马玉清,而我父亲的舅舅是马玉德,马玉德和马玉清是兄弟,马玉清自然也就是我父亲的舅舅了。马耀礼和父亲就成了第二代弟兄了。
住下了不长时间,北梁西头的一个八十多岁的人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来到我家里,慢慢地坐在炕沿上,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擦泪痕痛苦地呻吟着对我母亲说道:“这些年头没见你了,家里都过得咋样?我活愚了,不顶用了,儿子、媳妇都不管我了……我炕上坐不住啊!肚子饿得慌,来向你要口吃的……媳妇子,你就别笑话我了!”
“太爷,我不笑话您老人家,都是自己人。”
母亲的眼睛润湿了,哽咽着安慰老人。
然后给老人沏上了茶水,又端上一盘子馍馍和刚刚煮熟的山芋让他吃……等老人吃好了又将剩下的全部装进一条布袋让他回家时带上。
老人起身要走了,母亲又叮嘱说:“太爷,啥时候饿了,您就别嫌弃,常来家里俺给您做吃的。”
老人走了以后,我问母亲:“妈,您为啥叫他太爷呢?”
“唉,苦命的人哪,我是比上你称呼的,老太爷是俺根上的人哪,他叫马宗礼,一辈子只生一个儿马玉华,华爷,华爷和你德爷又是弟兄关系,说起来都是你的舅爷。他们的爹当然就是太爷了……”噢,我终于明白了。
过了好些时间,母亲一直念叨着说为啥太爷就不见面呢?于是,我就一溜风似地跑去看老人家了……
走进老人家的院落,望着一颗将要枯死的老榆树,我的心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万能的主啊,这是家呀!纯粹连羊圈都不如,房檐上全是豁豁獠牙,窟窿天窗,就连天门板都快要散架了……窗户上的碎纸片被凄凉的秋风吹得稀里哗啦响个不停,就在我迈进门槛的那一刻,一群麻雀突然从屋里一拥而出,顿时尘土飞扬,他们一起从那千疮百孔的破窗户飞走了……
怎么屋里全是空的,没人哪!仔细一看炕上才发现炕中央露出半截人来!我爬上炕一瞧全明白了——原来老人睡觉的那个地方,炕面子塌陷下去了……老人掉进灰洞里。我翻开那条破烂不堪的被子时,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弥漫了整个屋子。
主啊!这灰洞竟然成了他便所与住所。
他们儿子哪里去了?媳妇子哪里去了?怎么都不管自己的老人呀?
屋子里什么都没有。枕头上只有一把熏得又黑又脏的空水壶和同样漆黑无比的瓷缸子……
目睹这一非人道的凄惨情景!我哭了……
“太爷,您这是咋了,怎么没人管呢?我摇了摇他的冰凉身躯。太爷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我又闭上了……我想大概是不行了,于是,我便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舅太爷从灰洞中抱了出来……”
当我哭着喊着又从家里把母亲找来时,老太爷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失去光泽的眼睛,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了人世!
后来,我从大人那里得知,老太爷之所以遭遇如此可怜的悲惨结局,是他的儿媳妇最近半个月内根本就不在家。就是在家又能怎么样呢?他(她)两口子平日里一贯都是如此,从不关怀孝敬老人的。
听说老人归真了。两口子才从外面赶回来为老人送葬……
父亲说:“像这样的儿女就是‘卡菲勒’,心里没有老人枉来世上一辈子。”
大哥高小毕业了。回来之后一口咬定说啥再也不去念书了……任凭母亲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也无济于事。一天,他终于找了一个充足的理由告诉母亲:“妈,我的头秃再到人多的地方上学恐怕老师同学都笑话我……所以打死我也不念了。”
实际上,他的头是在很小的时候,不知咋了活生生地就出了些毒疮,后来由于上学念书,经常洗头的缘故,毒疮也就自然消失了……于是就落下个秃头顶。为了遮羞,他经常戴着帽子,用来掩饰自己那点缺陷。也许,他的这种不伦不类的理由和顾虑已成定格,一定终身了!
一年后,父母亲托野麦子淌那边的“活不成”二奶奶做媒,在牛首山下金积镇上找了一个媳妇。亲家马兆斌有点历史遗留问题……解放前,宁夏的土皇帝马鸿逵手下有一个当过机要秘书的重要人物张洪涛。
因张大人被共产党关进了监狱的缘故,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带上了个阶级成分的帽子……这些都是那个特定年代造成的。但毕竟马兆斌也是曾经在府上干过差的人,有一些文化底蕴,见过大场面。加上这场浩大空前的革命运动,他也只好默默认了这一切。
为此,在对待自己女儿的问题上也就不提也就不讲究任何让人难为情的条件了。
若勉强说多少讲个条件的话,人家很通情达理,条件只有两点:一是问亲家要点糜子,二是给儿媳妇扯上一身衣服就大事托靠主了……
就这样,父亲二话没说,碾了两口袋黄米买了点穿用的布料一切从简地把儿媳妇子娶了回来。
结婚不久,大哥和嫂子让大队派到长流水水库大坝干活去了……
曾经在我还没出生之前,父母亲也来这里搞过建设,流过汗,出过力!
就在这一次干革命的劳动中,因大坝塌方事故不断发生,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由于父母提前离开大坝,才幸免遇难。
父亲说:“我和你妈那时在大坝上干活,一千多号人谁也比不上我。别人背土用的是小背篼,我用的是大背篼。被政府评了个劳动模范呢!你妈挣了一身的病也没得个啥……现在这小俩口又走了,不知道咋样呢……”
后来大坝工程结束了,大哥和嫂子也都回来了。因他可算是庄子上屈指可数的有点高小文化程度的人,就在生产队里当了一名保管员。
我七岁时,母亲又给我们生下了一个小妹妹——色丽麦。
她刚生下时,实在小得可怜,仅有父亲一只鞋子那么大!自从有了她,大妹妹可有活干了,整天哄着她玩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因为还是个没上学的孩子,还是别的什么在诱导,对一切未知的世界总感觉像牛粪巴郎哭妈妈——两眼黑黑。越是黑的东西越是充满了童心,对一切未知的东西充满了好奇!成天激荡着幼小心灵的天堂。
北梁西头太爷那桩令人难以磨灭的形像还未退去呢,我又跑到南坡上马赞元爷的家中和他的小孩子尤苏去玩……
尤苏比我大一岁。为啥同他玩?还不是因前几天我望见他挂在身上那杆枪神气十足的样子,真令人羡慕!于是,我就动了心决定和他交个好朋友!说来也挺投机的,他很喜欢我,我们一起到榆树林里打麻雀,玩累了又去那野地里拔红根子,抱辣椒樱,在废弃的土墙上找蜂蜜灌灌……最后冲到荞麦地里追五彩缤纷的花蝴蝶尽情戏耍……
尤苏对我说:“俺爷爷对我可好哩,不信你到家里看。”
啊,一个多么幸福的家呀!古色古香,充满了温馨。元爷手捧《古兰经》端坐在炕头窗台前念念有词地诵吟着经书。元奶奶问我吃饭了没有,我不好意思说,她忙从柜子端出一盘年糕给我吃……我在贪婪地吃着香甜可口年糕的同时,不由自主地小眼睛却被屋里的景物所吸引:足有同我一般高的古青瓷花瓶,乌黑发亮的台座式穿衣镜,镶嵌着一块白色透明水晶玻璃仿佛把整个房子都照得熠熠生辉,装有很多抽屉吊着金黄色古铜环的组合柜一一呈现在眼前!
他家可真是有钱的主。同梁上其他的人家比大不一样,非常悬殊!
晚上,父亲回来,我就把白天看到的这点小小经过说了一遍。父亲就把元爷这与众不同的来龙去脉从头数了一遍:“这个小庄子除了马赞元和马赞成两兄弟是外来户,再剩下的全是你惠安堡奶奶辈分上的亲戚,是同一个祖宗。”
解放前,马赞元从外地逃难来到这儿落了脚之后,雇了一帮穷小子做盐业生意发了财,大把的银元没少赚。他只生了一个儿子。人一有钱就燥的不行行,也学恶霸地主的样子要势力,欺负人……死皮赖脸地请了你舅爷马玉德到惠安堡,掏了三十块大洋,把你亲爷唯一一个女儿买回来,给他的儿子当了童养媳。那时,你姑妈只有十一岁,马赞元的儿子才六岁,连睡觉都不知颠倒——往炕上尿尿呢,天天让媳妇抱进抱出,吃喝拉撒全操透了心……唉,遭罪啊!幸亏解放得早,共产党给元爷定了“土地经营”的成分,家里破了财。
你姑妈就让你舅爷照常送回惠安堡……
后来等大了又让你爷因爱钱把女儿嫁给买家,光彩礼就收了几十块银元呢!
说起买家来在解放前也是开烟馆倒了灶……
不过,你姑爹买义云跟别人不一样,虽然很穷,可人老实,勤快,本分,你姑妈人又年轻,漂亮,俊得……在惠安堡方圆百十里,川里有名,县里有榜,走路是一阵风,站下是一根葱,脸是蛋皮皮,头是燕叽叽,她心肠软,干活麻利,上炕是裁缝,下炕是厨子,不论是绣花、纳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
你姑爹自从国民党部队回来,和你姑妈成了家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围着你姑妈转了一辈子圈圈为啥呢?
因为,你姑妈小时候在马赞元家当童养媳落下一个毛病——羊角疯。有时犯,有时好,犯病的时候一头栽倒在地上连绊带磕,脚蹬手扬,口吐白沫……等清醒过来就和平常人没啥两样。为了养活这个家,你姑爹盐湖里捞盐卖盐,打柴卖柴,驮水卖水受尽了罪……可是能遇上你姑妈那么好的一个女人他一辈子受多大的苦值了不后悔。
听说,现在还是村上的畜牧队长呢!
父亲的叙述真真切切。让我这个只有七岁的毛孩子的内心里掀起了一段不平常的波澜,留下了人生一个更大的问号。
啊,人活着实在是不容易!为啥这世上的人都不一样呢?为啥有的人一辈子就像这海子湖的盐颗颗,又咸又苦呢?
再望一望住在南炕的舅爷一家人,过的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就因为,他曾当过保长,打成了坏分子……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锅头炕洞里没烟火,而荒滩有的是沙柴可是队上就是不让他砍,一家六口人没有柴咋活呢?干望着一把黄米做不成熟饭,逼迫他像做贼一样黑天半夜偷偷地摸到荒滩去背柴。
一旦被发现了抓起来不是批就是斗,让一家人忍受着屈辱和煎熬,就这样过着艰难而又寒心的光阴……
又要搬家了,大队上把我们一家人分到了西边离海子井约六里的野麦子淌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