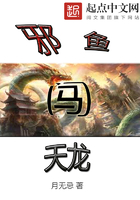每当教室外有老师叫学生出去,我总疑心他要把我也叫去催学费。有一天真的叫到了我。原来是市报的杨记者要采访贫困生。在会议室里,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张纸,让我们把自己的家庭状况和求学经历用抒情记叙文写出来,写得越生动越感人越好,他将把我们的稿子择优刊发,在市报社搞一个“希望捐赠热线”。我扫视着同学们,很多人在咬着笔头艰难地构思,但更多的人像我一样望着空洞的稿纸发呆。我知道这里有老师安排的全身名牌的“贫困生”,他们可以把它仅仅当成一次作文来看待,但我不行:谁可以轻描淡写地揭自己心头的伤疤?现在我最不愿去的是那个会议室和教师宿舍。走到这两个地方的时候就像走进了到处是摄像机的房间,每一寸皮肤都有被曝光被偷窥的尖锐疼痛。你听我说,父母总是习惯在我上学时塞给我一包茶叶或木耳,对我说:“去送给××老师吧,经常走动走动,或许能把学费免了。”我唯有顺从地把东西塞进包里,因为我只要一拒绝,父母便会火冒三丈,我又怎么忍心再惹他们生气?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在同学们疑惑的目光中提着礼品穿街过巷,然后徘徊着敲门,见到老师后放下礼品就走的尴尬感觉呢?毕竟父母也曾像小学生似的坐在老师面前,双手放在膝上,堆着笑脸,一遍遍求着老师担保晚一点交学费。看着孩子在自己面前受苦和看着父母在自己面前受辱,哪一个更残酷?
只要学校通知放假,我就兴奋得不行,盼着快点回家。每当我走近家门的时候,会有短暂的犹豫,我怕见到父母过度劳累而佝偻的背,怕见到他们缠满胶布的手。而当我真正到家之后,所有的不适又马上消失。我只想多做点家务事弥补一下什么,或许是自己让他们过度操劳的不安,或许是自己欠下的太多的亲情债。然后,我上学时,妈妈又会塞给我一大堆鸡蛋、板栗、核桃、木耳……“这是你自己的,这是给你老师的……”如此,周而复始。一次,爸爸赶了很远的路来看我。看到他站在校门口,头上包着白头巾,提着帆布袋时,我真的很高兴,根本没在意同学们成分复杂的眼神。而爸爸却再也不来看我了。他说给我丢了脸。唯一的一次,我忍着泪对他说:“你是我爸爸,穿得再差也是我爸爸,谁敢笑话我们,谁会穷一辈子……”
“谁能穷一辈子?”在被贫穷纠缠的日子里,我唯有用这句话安慰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时常想起在我上学时给我两块钱车费的老奶奶,想起17岁吐血死去的姐姐要我读书时的坚定眼神,想起老师送的那包温暖我一冬的衣服,一边愁着明日三餐一边安慰着自己。
然而当我迷糊着醒来的时候,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新的失望正在等着我,可地球并不因我自以为水深火热的苦痛而不转了,这世界正常得很。
所以我唯有将曾经的耻辱、反抗、抱怨、诅咒化为记忆的沙,让它沉在时间的河里,以此保持河水的清亮。所以你看到的我只是一个有着很多不愿让人提及的往事,有点虚荣,斤斤计较,孤僻,同时又勤劳、善良、俭朴的普普通通的贫困生。
然而,谁能贫穷一辈子?
淤泥里开出的花儿
文/安宁
这是一个孩子眼里的世界,一个在黯淡里依然知道要快乐成长的孩子的世界。
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便习惯了家里被来找父母讨要公平的人挤得满满的,他们在窄窄的房子里大声地吵闹、怒骂,甚至有时候会与父母打起来。我在一旁边写作业边听着这样一场高潮迭起的闹剧,有时候会对着那些想要揍我父母一顿的人笑笑,他们也是对父母一贯的占人便宜的毛病没办法了吧,否则不会在临走时看见我殷勤地给他们开门,怜爱地冲我叹口气。而我,在他们瞬间柔和下来的眼神里,会觉得开心,好像那种被别的小孩子鄙视的痛苦,亦跟着消散了一样。
我的父母做小本生意,从来都缺斤少两,最起码的公平,在他们心里,没有一点概念。就是每年交学费,他们也要跟老师讨价还价,让我在同学们面前跟着他们受尽了白眼。他们那么自私,连我这个小孩子都能明辨是非的事,在他们口中,却偏偏要争出几分对他们有利的歪理来。我所能做的,唯有在他们一次次让我在人前觉得尴尬为难,甚至委屈受辱时,奋力地让自己从这种泥泞里跳出来,朝着自己想要的有芳香的道路,拼命奔跑去。
但还是有跳不出来的时候。读大学以前,我永远是班里最后一个交学费的人,不管我用何种方式与父母嬉笑着要钱,他们都会一律冷冷地回答:没钱。他们只是觉得不舍,白白地把自己挣的钱交给别人,宁肯拖到最后,让钱在自己口袋里焐得烫手了,才一脸不悦地拿出来。我也永远都是那个朋友最少的学生,不管我怎样拼命地往周围的小圈子里挤,都无济于事。他们总是很尖刻地就当面对我指责说:我们不想要骗子和小偷的女儿!我想给他们解释,尽管我的父母是坑蒙拐骗的人,但恶习是不会遗传的,我和他们中的每一个女孩子一样,善良、上进,懂得给人关爱。这样的解释,奏效的时候并不是很多。大多数时候,我一个人孤零零地骑车上学,在路上他们对我给予他们的热情招呼,理也不理,便嘻嘻哈哈地飞驰而过。我从没有对加入到那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团体里去失望过,我相信父母甩给我的东西,我会干干净净地甩开去,像骑车时将路上的积水欢快地溅出去很远一样。
那是我最忧郁也最快乐的时光,我会因为在菜市场上,看到父母被人揪住衣领还据“理”力争而觉得哭笑不得,亦会因为能始终笑着将那些来找父母“算账”的人,一个个地打发走而感觉到开心。我记得偶尔会有男生在路上截住我,和我说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废话。尽管他们没有写情书给我,只是喜欢与我天南地北地闲扯,但我却为此会兴奋上很长的时间,不是为女孩子都向往的爱情,而是因为这样地被人嘲弄,还能有人喜欢。那是一段像莲花一样向上努力生长的过程,周围皆是淤泥,可是当我被赋予了生命,我就不会辜负这一段生机的旅程,而且,开出一尘不染的洁白花儿来给世人看。
我在读到高三的时候,已经有三四个可以心心相通的朋友。他们去我的家里做客,从不会因为父母的冷淡和自私而对我心生怨恨,他们知道我是与父母不一样的。甚至后来母亲因为偷了附近工厂的器具被拘留了一个月,几乎成了小城人人皆知的新闻,但我的这些朋友,还是进门来礼貌地喊母亲“阿姨”,还是鼓励我报考最喜欢的英语。我的真诚和无忧,感染了他们。
后来我读了大学,身边没有人再知道我人品糟糕的父母;但每有朋友要去家中做客,我还是会把父母的待人习惯和盘托出,我只是想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看到我父母的为人,请不要因此怀疑我对他们的诚意。我无法选择出身,但我可以选择自己走路的方式。难过的时候我最喜欢看一部叫《蝴蝶》的法国电影,影片里那个叫莉莎的8岁小女孩儿,她被单身母亲一次次忽略,但却从没有哭闹过。她依然是一个快乐的小孩子,永远不会去想悲伤,永远知道只有想办法,才能让大人明白自己,让陌生人喜欢上自己。片中主题曲的歌词,我几乎倒背如流。
“为什么漂亮的花会凋谢?”——因为那是游戏的一部分。
“为什么会有魔鬼又会有上帝?”——是为了让好奇的人有话可说。
“为什么木头会在火里燃烧?”——是为了我们像毛毯一样的暖。
“为什么大海会有低潮?”——是为了让人们说:“再来点。”
“为什么太阳会消失?”——为了地球另一边的装饰。
“为什么狼要吃小羊?”——因为它们也要吃东西。
“为什么是乌龟和兔子跑?”——因为光跑没什么用。
“为什么天使会有翅膀?”——为了让我们相信有圣诞老人。
这是一个孩子眼里的世界,一个在黯淡里依然知道要快乐成长的孩子的世界。而我整个的年少时光,即是这样走过,且在我融入这个社会的时候,开出让身边每一个曾经鄙视我的人皆真诚惊叹的无瑕莲花来。
爱西藏的男人
文/裘山山
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
一般人爱西藏,都多多少少能说出自己的原因。可是我知道,有一群人,他们爱西藏没有理由。
三十八年前,有位西藏军区的领导病倒在工作岗位上,他是边修路边进军,爬雪山数十座,趟冰河数十条,流血牺牲走上高原的英雄群体中的一个。他的妻子孩子进藏看他,他被担架抬了出来,送到北京治疗。
他的儿子,一个正读高一的青年学生,看到父亲被抬上飞机的时候,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在西藏当兵!说到做到,这个儿子在那片土地上一干就是二十五年,从一个士兵成长为一名大校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