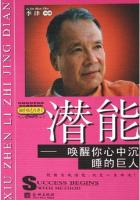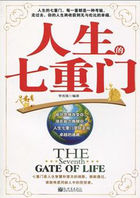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中央集权的人,但是,秦始皇所建立的中央集权政治,基础并不巩固。在秦朝灭亡以后,项羽便曾一度恢复分封制,先后分封了十九个王。刘邦在和项羽争夺帝位的时候,为了争取有实力的人的拥护,对于一些有功的将领和一些有很大实力的地方贵族,也封他们为王,例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臧荼等等。各个王在藩国里,有很大的独立性,他们直接控制着人民和土地,实质上就是地方割据政权。在取得天下之后,刘邦又东奔西跑,花了很大的气力将这些异姓诸王一一剿灭,为此,刘邦自己也丧了命。
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因为自己新朝廷的实力不能到达全国各地,又认为自己本家的子弟是可靠的,因此就分封了许多同姓子弟为王,把他们分封到各地去。西汉时期,全国大约有五十六个郡,但直属中央的仅仅十九个,在各个藩国手中的却有三十七个,这种枝强干弱的局面在汉初几十年中央和地方实力都还弱小的时候,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
汉初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封国之间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中央需要地方的封国来支持形式上的刘氏政权,防范外来或外姓势力颠覆刘家的天下,这在铲除吕氏家族势力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地方需要中央的册封来确认他的合法地位,并以中央作为自己统治的后盾,因此,它们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所以,这时候的博弈应该是刘氏和潜在的威胁刘氏政权势力的博弈,从图可以表明,中央和地方应该是合作性博弈。
西汉前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汉初建国时,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百姓财力匮乏,急需休养生息的情况采取休养生息,不与百姓争利,清静无为的治国策略。
这种策略在汉初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过文景之治,西汉已经是国富民强。但在汉中央政府的力量强大的同时,各地藩王的势力也比以前大得多了,他们各自发展势力,拥地自雄,这就使中央和各藩国的矛盾尖锐了起来。在三十税一的政策下,商人和地主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各地都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豪强势力。利益的驱使,使中央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才能解决当时的矛盾。
汉武帝十六岁时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那时候掌握大权的是他的祖母窦太后。窦太后崇尚道家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实际上是一个保守现状的守旧派。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死去,汉武帝才解除了施展政治抱负的障碍。
汉武帝为了把一切大权都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使自己的政治抱负能够顺利地实现,首先便是削弱丞相的权力。丞相本来在行政上总理一切,地位很高。这时候汉武帝就将原来在他身边只管拿拿文书的尚书或中书(用士人称尚书,用宦官称中书,职务一样)的地位得到提高,终于使丞相成为有名无实的职位。汉武帝以后的汉朝的历代皇帝,直到东汉,“中书”或“尚书”都是中央发号施令的机构。
在把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到自己的手里以后,为了使王权得到彻底的贯彻,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这就面临着和藩国直接进行一场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汉武帝采取了主父偃建议的“推恩”办法,命令藩王们不能把封地仅仅传授给继承王位的长子,而必须划出一部分来分封给其他子弟做诸侯国,并且规定这些诸侯国不再受藩王的管领,而直接由各地的郡来管辖。这样一来,藩国的土地越分越小,小的只有三五个县,大的也不过十几个县,势力越来越弱,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对抗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还用种种借口来剥夺侯国封君的爵位。汉武帝每年八月会诸侯于庙中,诸侯必须出金助祭,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借口列侯所献黄金分量和成色不足,夺爵一百零六人。据统计,汉朝初年因功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年)就只剩下了五人。经汉武帝自己封侯的有七十五人,而其中六十八人后来被剥夺了爵位。因推恩法而封侯的各藩王子弟一百七十五人,在汉武帝手里失侯的也有一百一十三人。
为了同样的目的,汉武帝又加强了原有的监察制度。汉朝初年,中央政府虽然因沿用秦朝的制度设有御史大夫,但废除了负责监察地方的监御史。汉武帝贝Ⅱ把监察制度大大加以扩充,并建立了“州刺史”制度。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道,设置了一个司隶校尉和十三个州刺史,分别负责中央和地方的监察工作,对各郡国进行严密的监督:监督的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包括地方豪强和郡太守是否遵守中央法令,是否互相勾结称霸逞强等等,此外,州刺史还有直接行使“治断冤狱”的司法权。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还建立了一套选用官吏的制度。汉武帝以前,中央政府的大官,多是功臣或功臣子弟。这样,官吏的来源很狭隘,而新兴的地主阶级随着力量的加强,他们迫切要求政治上的地位。汉武帝通过“察选”、“荐举”、“征召”等各种方法“破格用人”,把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大量提拔起来,充当中央和地方的官吏,从而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汉武帝还设立“太学”,通过学校来选拔官僚。
这样,汉武帝就把秦以前已经开端,秦始皇曾经加以发展的官僚制度大大加强了。用从“民间”(实际上是地主阶级中间)选拔出来的官僚来代替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没有被废的王侯只是“衣租食税”,地方豪强的行为也受到严密的监督,秦始皇开始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汉武帝这时候才算巩固了。
汉武帝体制改革的最大特色就是剥夺了世袭藩王、功臣贵族的权力,从中小贵族中选拔人才,实行任期制,而废除终身制。这事实上也就是一场二。维护帝王的权力,而与地方势力展开的博弈。对汉武帝来说,他有加强中央集权和维护现状的两种选择,地方势力有反抗和服从的选择。汉武帝加强集权,地方反抗,中央必须付出一定代价,但中央势力已经得到大大加强,最终会胜利,单个地方势力已经无法抗衡,对抗诸侯只会身死国除;不反抗,还能够“衣租食税”或享受朝廷俸禄,保存一定的利益;汉武帝不加强中央集权,维持现状,中央获益相对小一些,地方如果再反抗,诸侯利益只会彻底废除;不反抗,利益自然会较加强中央集权大一些。汉武帝之所以要加强中央集权,是因为国家的统一,必须改变那种政出多门的状况,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威。他之所以能够大量地剥夺藩王、诸侯的爵位而没有受到武力反抗,是因为在他父亲汉景帝时,地方势力在最强的时候,爆发了一次“七国之乱”,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和中央对抗,也仅仅持续了三个月。而武帝时期,中央实力进一步加强,地方武力反抗也是自取灭亡,彻底失败;而不对抗,还能最低限度的保存自己的利益。用图则可作如下表示:
汉武帝时期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汉武帝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势力由建国初期的合作性博弈转变为非合作性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汉武帝成功地改变了博弈规则,最大限度的加强了中央的权力,将地方势力压缩到最低限度,而博弈取胜的关键点就在于他在最佳的时机展开博弈,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他成功了。
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博弈的核心,就是围绕着一个规则,各方或者合作,或者单干。其实,就算是没有合作的博弈,也是要一个规则的,那种情况下,规则的作用就在于制约各方朝着最大的利己目标发展,而又不会采取互利的形式谋求各方的利益。
如果把这一规则推而广之,就可以发现,在完成同一项任务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变化或者执行者关注重心的改变,这项任务中也会出现不同的预期目标,那么,如何把这些预期目标进行统筹,就是一个博弈的问题了。而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不同的工作重心下,调整思路,修改博奔规则。可以说,在不同的阶段,因为重心不同,所以要完成的目标也不同,因而这些不同的预期目标,就可以看做是一个个没有互利关系的单方面利益。那么,如何让这些单方面的利益得以实现,又不会因为一个目标而牺牲其他方面的利益呢?这就需要在调整规则的时候仔细考虑。
对规则进行调整和修改,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出发点,这就是在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如果既定的目标都被抛开,那么,由此带来的所谓“变通”或者“灵活”,就不是进行博弈的规则调整,而是朝令夕改、政策混乱。
在《列子》中,有一个讽刺修改既定目标而行事的故事:一个养猴子的人,用橡子喂猴子。他对猴子们说,早上喂它们三个橡子,晚上给它们四个橡子。猴子们听了之后比较生气,他赶忙说,那就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们才高兴地同意了。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喜欢朝令夕改、反复无常的人,嘲笑他们是像猴子那样的蠢人。
看上去这好像就是一个笑话,但实际上这种被实际情况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黄河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历朝历代开发黄河、治理黄河的举措,也成为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明朝对于黄河的治理,正是没有合理变通规则,错误地进行目标转移的教训。
明王朝的统治前后共计二百七十余年,其中,明太祖朱元璋和建文帝朱允坟都以南京作为首都,这个时期对黄河的治理,只不过是对国家境内一条大河的治理。自从明成祖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之后,大部分时间都是以北京为政治、军事中心的。为了维持首都北京数量巨大的粮食和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在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年),明成祖下令修复了元代在北京附近开凿的会通河,又沟通了从江南到北京的水道,使北京和江南建立了水运上的直线联系。从此以后,北京的物品需求,就主要依靠南北运河运输,这样一来,维持南北大运河的漕运畅通无阻,就成为明政府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问题。
运河漕运既然成为明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与运河有关的方方面面也就越发重要起来。因而,穿越运河而人海的黄河就与漕运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明成祖永乐年间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对黄河的治理,基本目标就是保证漕运不受影响。
当时,黄河的决溢泛滥大多在河南境内发生,尤其是开封上下,决溢次数非常频繁,黄河由中游所挟带的泥沙也经常淤积运河的河道,而使漕运受阻。当时,治理黄河、运河,与黄河夺淮人海后产生的治理淮河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治理的困难程度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河道的紊乱也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面对黄河、运河治理过程中问题相互交叉的形势,明代的治河者既害怕黄河决堤冲毁或者淤塞运河河道,又希望借用黄河之水,以补充运河的水流量,增加运河的深度,以保证运河的畅通。这种治理黄河的思路,就是既想遏制黄河的水患,保障漕运的顺利畅通,又想引导黄河之水,趋利避害,以黄河水支持漕运。明代人也正是出于这种极力避免黄河水患破坏社会生活,又要利用黄河水流支持运河漕运的双重愿望,一方面竭力防止黄河妨害运河畅通的情况,特别是防止黄河向北摆头侵犯会通河,避免黄河冲毁运河河道;另一方面又要不使黄河干流脱离徐州以南的运河河道,力图引黄河之水充实运河,保证运河水量充足,来保证漕运的顺利进行。
为了避免运河经常被黄河所侵扰、破坏,明代开始了开凿新运河河道避开黄河泛滥区域的方法。应该说,这个方法是通过变通规则。使黄河与运河河道相分离,这样治理黄河就可以不必考虑到漕运的问题了。到了明神宗万历年间,新运河全线基本竣工,避开了黄河容易决口、泛滥的险段三百三十里。不过,明人避开黄河以保证漕运畅通的目的,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完全实现,仍然有将近二百里的路程需要以黄河河道作为漕运干线的一部分来维持。
对规则进行调整和修改,需要一个相对固定的出发点,这就是在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前提下,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如果既定的目标都被抛开,那么,由此带来的所谓“变通”或者“灵活”,就不是进行博弈的规则调整,而是朝令夕改、政策混乱。
作为一个政权,要保证首都的安定与繁荣,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如何保证向首都畅通无阻地运送物资,并考虑到让沿途的百姓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下不至于造反起义呢?这就要采取合理的方法才能实现了。明代前期治理黄河的经验证明,要实现国家中枢与地方社会安定的“双赢”。就应该在两者的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然后再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管理。黄河的泛滥已经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大灾难,同时也是阻碍向首都运输物资的拦路虎,所以,二者都希望将黄河治理好,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是出于“趋利避害”的基本原则是没有不同的。到了明代后期,在黄河的治理问题上,和“保漕”的经济目的相背离,出现了在南部的“护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