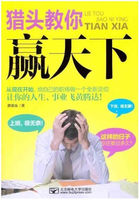曾国藩深得“阴阳盛衰”之道,强调在得意之时,需“势不使尽”、“弓不拉满”。自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但他却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会办。在他弟弟曾国荃孜孜以求功名利禄的时候,曾国藩谆谆教导他,凡事切不可太过。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曾国藩一生同受儒家入世和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学会“盈虚”之道呢?荷道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译文】
写作文章的道理,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雄俊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就像是连日淫雨绵绵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的感觉。再如登上高楼俯临浩淼的大江,独自一人坐在明亮的窗台下,在洁净的茶几旁悠然远眺,可以看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丝毫没有卑下龌龊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文章中如果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了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的贾谊、唐代的陆贽、宋代的苏轼,他们的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相对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宏伟雄俊的气象,虽然文辞意旨不够渊博高雅,但他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浑然一体,通畅明快,就好像和知书达理的人谈话,文章言辞和内容都很华美,中心和铺陈相得益彰,这确实不是能够轻易达到的。
【原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文】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诸葛亮凭借区区蜀国汉中的一小块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面讨伐势力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少有的。但是《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谈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该恢宏、赏罚应该公允,为君者应当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当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自己的职责。由此可以推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胸襟远大、思虑精密周到的结果呀。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
夏、商、周三代的鼎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候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村夫或者是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自己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当不用多言。等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败枯竭,道义本身就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看到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示称王百代所需要的法制,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遍布天下,不断传授、演进他的学说。后世聪明杰出的人才或者是有知识见解擅长著书立说的,大多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醇厚或者驳杂,因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人,他的文章就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在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作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点评】
自古至今,“文”、“道”的说法一直在文人脑海中萦绕。“文以明道”、“文道合一”、“作文害道”等说法层出不穷,不管怎样,在历朝历代,大多文人都认为,“道”是文的核心,一篇文章,如果没有“道”,就失去了写作的意义。曾国藩熟读前代文章,自然也不能避开“文”、“道”的说法。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这里的“道”自然是圣人之道,特别是孔孟儒学之道。
曾国藩,主张为文时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他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他认为,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了,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就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假若平常酝酿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但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于雕饰,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
藏锋
【原文】
《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伤,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译文】
《扬雄传》中说道:“君子遇到政治清明、君王有为的时候,就要努力实施自己的理想抱负;遇到政治紊乱、君主无道的时候,就要像龙和蛇那样,能屈能伸。”龙蛇,就是指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高洁的操守,就属于伸的一方面。言语谦逊,就属于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诚恳的心意表现在人的外貌上,生根于心里,显示于颜色神气上。古往今来有道的人,他们的淡雅谦和无不通过外貌表现出来。我的气色没有丝毫变化,难道是我内心强烈的欲望没有淡化?机心没有消弭?我应该在心中深刻反省,让我的修为涵养通过外貌表现出来。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译文】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想超过他人。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向往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些都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君子,大都终生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明白了大的道理,知道一般人所争夺追逐的名利是不值得计较的。从秦汉至今,所谓的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尽呢?当时他们占据权势要地,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才智超过别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就那样熙熙攘攘活着、又潦潦草草死去的人,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当然其中也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但等到他们死去之后再看,他们和当日的杂役贱卒、低贱贩夫,熙熙攘攘的活着、又草草地死去的人,也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深义而地位显贵,因而泰然自若地自奉为高明,竟然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熙熙攘攘、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做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同归于死亡,而没有丝毫的差异,难道不叫人悲哀吗?
【原文】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译文】
古代的英雄,志向和胸怀都很广阔,事业规模宏大、声名远播,但是,他们教训告诫子孙,做人应该虚心、谨慎、藏锋,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势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于别人,别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犬马、嬉游聚会之类的活动,不应该做得太度。像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样的事情,一概都不要做;吃穿用度等各种花费都要有节制。对于奇异服装、稀有玩物,都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应该适当地与辅佐自己的官吏见面交流,相见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感情思想,不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又如何去了解民众的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治理国家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弟,都是意旨简约,往卑微处着想,非常收敛抑制。
【点评】
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韬光养晦了。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个人锋芒太露,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并最终为自己带来祸患。孔子谆谆告诫要“温、良、恭、俭、让”,实际上也就有藏锋的意思在内。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看来好像他们都是庸才,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当然,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所以藏是为了露,时机成熟时,要毫不含乎地露。
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也正在于能韬光养晦,懂得藏锋。他一生时时标榜自己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做人低调不张扬。但他对其弟曾国荃的复出及帮助李鸿章稳定两江总督一职,又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正是因为善于藏锋,他才于乱世之中得以最佳地发挥自己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