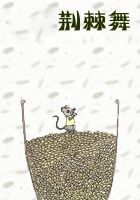“好一个奸诈的计谋,”福尔摩斯说着,用鼻子嗅了嗅那只死犬。“没有什么气味能干扰它的嗅觉。使您受如此惊吓,我们深感抱歉,亨利爵士。
我本来想象的是一只普通猎犬,而非这种猎犬。大雾重重,我们没来得及及时抓住它。”
“您终于救了我一命。”
“您受了如此的惊吓,还能挺得住吗?”
“给我再来一口白兰地,我就什么也不在乎了。啊!行了,劳驾把我扶起来吧,依你之见,该如何行动呢?”
“您就留在这里。今晚您不宜冒风险了。如果您愿意等一下,我们之中就会有一个随您回庄园去。”
他吃力地摇晃着站起身,但脸色仍然惨白,四肢抖个不停。我们搀着他到一块石头边,他坐下来,直打哆嗦,把脸埋在手里。
“我们现在得离开您了,”福尔摩斯说道,“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非干不可了,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我们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现在就只需捉拿那家伙了。”
“要想在房子里找到他,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往回走,顺着原来的小路飞速赶程的当儿,他又接着说。“那些枪声已经通知他,他那圈套已彻底完蛋。”
“当时,我们离他的距离还有些远,这场大雾可能已使枪声的传播大大减弱。”
“可以肯定他一直尾随那只猎犬,便于使唤——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不,不,此时他已经离去!不过我们还是把房子搜查一番,证实一下为好。”
前门敞开,我们冲了进去,匆忙地挨屋搜查,在过道里碰到了战战兢兢、步履蹒跚而年迈的男仆。除了在饭厅有灯光之外,别处漆黑一片。福尔摩斯急忙抓住一盏油灯,不让房子里面任何一个角落漏过,但是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所追寻的那人的踪迹,可是在二楼,我们发现有一间卧室的门是紧锁着的。
“里面有人!”雷斯垂德叫喊了起来,“我听到里面有动静。把门打开!”
从屋里传出微弱的呻吟和沙沙的声音。福尔摩斯用脚板朝门上使劲一蹬,一下子就把门蹬开了。我们三个人提着手枪,一齐冲进屋去。
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想要找的那个孤注一掷、胡作非为的凶犯就在里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非常奇怪而我们又没料想到的情景,我们呆立在那里打量着,惊愕不已。
这间屋子被布置成了个小博物馆的样式,墙上的一排盒子上安装着玻璃盖,里面装的全是蝴蝶和飞蛾,那个心怀鬼胎而凶狠的家伙居然把采集这些东西当作娱乐和消遣。屋子的中央竖立着一根木桩,这木桩是过去某个时候竖起来,为了支撑那根横贯屋顶、被虫蛀了的旧木梁的。柱子上捆着一个人,那人被布单捆得严严实实,不能出声,无法在瞬间辨出来是男还是女。一条毛巾绕着脖子系在背后的柱子上,另一条毛巾蒙住了脸的下半部分,只露出两只眼睛——眼里满是痛苦与羞耻的神情,还夹杂着令人害怕的疑虑——死死地盯着我们。一眨眼工夫,我们就把堵在那人嘴上的东西及捆在身上的东西都解了下来,斯台普吞太太就倒在我们面前的地上。她那美丽动人的头低垂在胸前,在她的脖子上我看到了鞭子抽打出的红色鞭印。
“这都是那畜生所为?”福尔摩斯叫喊道,“哎,雷斯垂德,把你的白兰地拿过来。将她放置在椅子上!她因受虐待而衰竭,现在昏厥过去了。”
她又睁开了眼睛。
“他现在平安无事吧?”她问道,“他跑掉了吗?”
“他是逃不过我们的手掌的,太太。”
“不对,不对,不是指我丈夫。亨利爵士呢?他现在脱险了吗?”
“他平安无事。”
“那只猎犬呢?”
“已经上西天了。”
她满意地长叹了一声。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啊,这个该死的家伙!你们看看他是怎样对待我的呀!”她猛然拉起衣袖伸出胳膊来,我们看见她臂上的斑斑伤痕,心里禁不住感到恐惧不已。“可这些还算不上什么——还不算什么了不起!更可恶的是他折磨了、玷污了我的心灵。原来我还心存希望,心想只要他依然爱我,无论是虐待、寂寞、受骗上当的生活等等,我都可以忍受,但现在我看透了,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成了他的欺骗对象和役使的工具。”她说着说着便突然伤心地抽泣起来。
“您对他已绝情了,太太,”福尔摩斯说道,“那么,请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的踪影。您要是曾帮过他干过坏事的话,现在就请协助我们以便将功补过吧。”
“他只有一个地方可逃。”她回答道,“在沼泽地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废弃的锡矿,他把猎犬藏在那儿的,并且还在那儿做了防备,以备逃避之用。他肯定逃到那里去了。”
雾堤像雪白的羊毛,紧紧围在窗口外面。福尔摩斯提着灯走到窗前。
“瞧,”他说道,“今晚恐怕没人能找到走进格林盆沼泽的道路。”
她大笑起来,拍着手,眼里和牙齿都闪耀着极度狂喜的光芒。
“也许他会找到进去的路,可是做梦也别想再出来了。”她嚷了起来,“今晚他怎么看得清那些木棒路标呢?是他和我两人一起插下的,用来标明穿过沼泽地的小路的。啊,我今天要是都给他拔掉该多好啊,那样他真的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很明显,在雾散去之前,任何追捕都是徒劳的。我们留下了雷斯垂德,让他照看房子,福尔摩斯和我以及男爵一起动身回到了巴斯克维尔庄园。有关斯台普吞家里发生的实情再也瞒不住他了,当他了解到他所钟爱的女人的真实情况时,竟然还能勇敢地承受住这种打击。然而夜间的那次惊险的恐骇已使他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天还没亮,他便发起了高烧,迷迷糊糊躺在床上,不过摩迪默医生被请来照料他。他们两人已商定,在亨利爵士身体康复之前便去周游世界,他在掌管这份不吉利的财产之前,是多么精神抖擞,健壮有力啊。
好了,这个离奇的故事讲到这里就快要收尾了。我试图使读者体会体会故事中那些隐匿的恐惧与模糊不定的猜测。它们曾长期使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结局却悲惨不堪。在猎犬丧命后的第二天上午,雾气散除,在斯台普吞太太的带领下我们到了一条贯通沼泽地的小路的地方。这地方是他们发现的。看她领着我们去追捕她丈夫时表现出的急切和喜悦的神情,我们便能意识到这个女人昔日生活的可怕程度。我们让她站在一个荒疏的小岛上,小岛地面坚实,土硬似泥煤。这块小岛越往沼泽地延伸,面积逐渐变得窄小。从这小岛的起点开始就在四处插立着一根又一根的小木棒,标明着这蜿蜒曲折,从一堆乱树丛转到另一堆乱树丛的小路。其间有漂着绿沫的浅水坑和污浊的泥坑,陌生人无法穿行。丛生的芦苇和茂盛细长的水草散发出腐烂的臭味,浓重的瘴气直扑面孔。同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失足,陷入深没漆盖的,暗黑的泥沼里。这样摇摇晃晃走了数码远,粘糊糊的泥还是沾在脚上。我们往前走着,烂泥一直紧紧拖着我们的脚跟。我们一陷入泥窝,就好像有一只邪恶的手使劲往下拽,要把我们拽到污泥的深处,而且拽得毫不含糊,似乎蓄谋已久。偶尔我们也看到一处踪迹表明有人曾在我们之前越过了那条危险重重的路。在泥沼的一堆杂乱的棉草中有一件黑色的东西显露了出来。福尔摩斯越出那条小路,想去抓那东西,一下子陷入齐腰深的泥沼中,要不是我们眼疾手快赶过去把他拉出来,他再也不会踏上这块坚实的陆地了。他挥动着一只黑色的皮靴,里层的皮上印着“梅尔斯·多伦多。”
“这个泥水浴没白洗,”他说道,“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亨利爵士丢失的那只皮靴。”
“是斯台普吞逃窜时扔在那里的。”
“没错。他用这只靴子引导猎犬追踪之后,还把它留在手中,他知道圈套会被戳穿因而出逃的时候,仍把这靴子紧紧抓在手里,奔逃途中就丢弃在这里。这说明,到这里为止他还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无法知悉更为详细的情况,虽然我们可以作出种种臆测。在沼泽地里根本不可能找出脚印,因为涌出的泥泞已迅速将脚印盖住了。可是一走出沼泽地,踏上硬实的土面,我们便急切地寻找脚印。可偏偏找不出半点踪迹。如果地上所见没有欺骗我们的话,那么斯台普吞昨晚并没有到达他挣扎着穿过浓雾所要去的那个避难的小岛。在格林盆大沼泽地中央某个地方,沼地里污秽的泥浆早已将他吞噬了。这个冷酷无情,狼心狗肺的家伙永远被埋葬在这里了。
在他藏匿他那只凶猛的伙伴、周围被泥沼所围绕的小岛上,我们发现了很多与他有关的痕迹。一只大传动轮,一个填了一半垃圾的竖坑,表明这矿坑已废弃不用。旁边是零星散落的矿工居住后丢下的遗留物件。那些矿工无疑是被周围泥沼的浓烈臭味给熏跑了。在其中的一间屋里,我们发现一只U形钉,一条链子和一些啃过的骨头,可以看出这里就是禁闭那只畜生的地方。
一具骨骼上面粘着一团乱糟糟的棕色毛发,散置于残留碎物之中。
“原来是一只狗!”福尔摩斯说道,“啊,是一只卷毛长耳獚。可怜的摩迪默再也见不到他宠爱的狗了。哼,我不清楚这里还有什么我们没有彻底弄清的秘密。他可以藏起他的猎犬,但他没法使猎犬闭住嘴,所以,传出来的犬吠声,即使在白天也是难听极了。在紧急情形下,他还可以把那只猎犬关在梅利琵的库房里,但这是要冒风险的,而且只有在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并且他认为是万无一失的时候,他才敢采取行动。那只铁桶里粘糊糊的东西不用问就是涂抹在那畜生身上的发光的混合剂。自然,这方法是由于家族中流传下来关于地狱之犬的故事而得到启发的。其用意是要吓死查尔兹老爵士。怪不得那穷途末路的恶魔似的凶犯看见这样的一只怪兽穿过黑暗的沼泽地,尾随其后时,一边跑,一边尖叫,就像我们的那位朋友那样。不过,轮到我们说不定也会那样的。这是一桩奸诈的计谋。因为除了将蓄意谋害的人置于死地之外,许多在沼泽地见过这只猎犬的人们当中又有谁敢于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呢?华生,我在伦敦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从没有一起追捕过比葬身此地的人更为危险的凶犯。”——他挥动着长手臂,指向那片茫茫的、斑驳陆离、其间布满点点绿色的沼泽地,它伸向远方,直至与那片赤褐色的沼泽地斜山坡浑然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