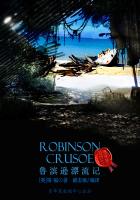“好极了,华生。你今晚总算开窍了。我也确实有过这个念头。你大概已经注意到了,这家旅店的隔壁有个自行车店。我赶紧跑进这家商店,租了辆自行车,趁着马车还没有离开视野就追了上去。我很快就赶上了马车,然后和它保持一百码左右的距离,跟着车灯一路出了城。我们已经在乡村大路上走了很长一段路,可这时发生了一件让我尴尬的事情。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大夫下了车,迅速地往后走到我停车的地方,用讥讽的口气对我说,他怕道路太窄,希望他的马车没有挡住我的自行车。他的话讲得很巧妙。我立刻从马车旁骑了过去,沿着大路往前又骑了几英里,然后在一个方便的地方停下来,看看马车是否已经过去。但是马车已经不见了,显然拐进了我在前面看到过的几条岔道中的一条。我把车骑回去,但是仍然没有看到马车,而现在你也看到了,马车是在我回来之后才到的。当然,我起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戈弗雷的失踪和阿姆斯特朗的外出联系起来,而只是认为阿姆斯特朗大夫目前的一举一动都值得我们注意,所以才跟踪他的。可现在既然发现他在竭力提防有人跟踪他,那么他外出这件事也就比较重要了。我不弄清楚是不会甘休的。”
“明天我们可以继续跟踪他。”
“可以吗?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熟不熟悉剑桥郡的地理情况?
这里不容易躲藏。我今晚经过的乡村平坦整洁得像你的手掌,而我们跟踪的这个人又不是傻子,他今晚的表现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已经给奥维顿打了电报,要他往这里回电,告诉我们伦敦有没有新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能把注意力放在阿姆斯特朗大夫身上,而这位大夫的名字还是那位帮了大忙的电报局姑娘,让我查看了斯通顿的加急电报的存根后才得知的。我可以发誓,他知道那位年轻人在哪里。既然他知道,我们要是找不出来就是我们的错了。我们现在必须承认,决定胜负的王牌在他手里,不过,华生,你也知道,我没有半途而废的习惯。”
然而我们第二天仍然没有进展。早饭后有人送来一封信。福尔摩斯看后微笑着把它递给我。
先生:
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跟踪我是白白浪费时间。你昨天已经发现,我马车后面有个窗子。你们要是愿意来回二十英里地折腾,那就请便吧。我还要告诉你们,跟踪我一点也帮不了戈弗雷·斯通顿先生。我相信你们如果真心想帮助他,最好还是回到伦敦去,告诉请你们调查的人,就说没有找到他。你们再呆在剑桥只会浪费时间。
你忠诚的,福尔摩斯说:“这位大夫真是个坦率的、直言不讳的对手。他倒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定要弄清楚再走。”
我说:“他的马车现在就停在他的门口。他正在上车。我看到他上车时朝我们的窗子望了一眼。要不要让我骑自行车去试试运气?”
“不用了,我的好华生。你尽管聪明机智,恐怕还不是这个大夫的对手。
我想我单独去试试也许能够成功。恐怕我要暂时离开你一下,因为如果在寂静的乡村出现两个问东问西的陌生人,一定会引起对我们不利的谣言。你一定能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找到一些名胜去散散心。我希望能在傍晚时给你带来好消息。”
然而我朋友又一次失望了。他到晚上才回来,疲惫不堪,而且没有收获。
“华生,我今天一事无成。我弄清了大夫的大致方向后,就到剑桥郡那一带所有的村子里去看了看,并且向酒店老板以及卖报纸的人问了一些情况。我去了不少地方,把切斯特顿、希斯顿、瓦特比契和欧金顿都跑了一遍,可是大失所望。在这种寂静的地方,每天出现一辆由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是不会不引起人们注意的。这位大夫又赢了一分。有我的电报吗?”
“有,我已经拆开了。电报是这样写的:
“向三一学院的杰瑞米·狄克斯顿要庞培。”
我看不懂这份电报。”
“哦,这很清楚。这是我们的朋友奥维顿打来的。他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我只需给杰瑞米·狄克斯顿先生写封信,情况一定会好转的。顺便问你一下,比赛有消息吗?”
“有。本地的晚报今天有详细的报道。牛津队赢了,一次攻门,两次带球触地。报上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穿蓝色球衣的剑桥队之所以失利,完全是因为他们第一流的国家级运动员戈弗雷·斯通顿不幸缺阵而造成的。比赛的每时每刻都能让人感到他缺阵所造成的后果。中卫线上缺乏组织,攻防不得力,这支实力雄厚、训练刻苦的球队显得软弱无能。”
福尔摩斯说:“那么我们的朋友奥维顿的预言是有道理的。我个人赞同阿姆斯特朗大夫的话,橄榄球不是我份内的事。华生,今晚早点睡,因为我预感到明天事情一定很多。”
我第二天早晨看到福尔摩斯时大吃一惊,因为他坐在火炉旁,手里拿着小皮下注射器。看到注射器在他手里一闪一闪的,我立刻联想到他体质很弱,真担心他会出什么可怕的事。他看到我惊愕的样子,笑着把注射器放到了桌子上。
“不,不,我的好朋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这一次用它决不是干坏事,因为这是解开这个谜的关键。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注射器上。
我刚刚去侦察了一番,一切都对我们有利。华生,好好吃顿早饭。我们今天要去跟踪阿姆斯特朗大夫,而且不查到他的老窝,我是不想吃饭休息的。”
我说:“如果是那样,我们最好把早饭带着在路上吃,因为他今天出门很早。他的马车已经等在门口了。”
“不用担心。由他去吧。他要是能走得让我追不上才算聪明呢。你要是吃完饭,就跟我下楼吧,我把你介绍给一个侦探,是干我们眼前这种活的最出色的专家。”
我跟着福尔摩斯下楼到了马厩的院子里,他打开马房门,放出一条狗来。
这条狗又矮又肥,耳朵下垂,黄白相间,既像猎兔犬又像猎狐犬。
他说:“我来把你介绍给庞培。庞培是当地最出色的追踪猎犬,跑得不是太快,但跟踪气味坚持不懈。庞培,你也许跑得不算太快,但对两个伦敦中年绅士来说,你仍然跑得很快,所以我只好冒昧给你戴上皮圈。好了,伙计,来吧,今天就看你的了。”他把狗带到大夫家的门口。狗到处嗅了嗅,然后兴奋地尖叫一声沿着大街跑去,而且还使劲地拉着皮带想跑得更快一些。半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出了城,正沿着一条乡村大道向前奔去。
我说:“福尔摩斯,你都做了些什么?”
“哦,是老掉牙的一套,但有时还是很有用。我今天早晨进了大夫的院子,在马车后轮上洒了满满一注射器的茴香油。一头猎犬闻到茴香油会从这儿一直追到天涯海角,而我们的这位朋友阿姆斯特朗只有到地狱才能摆脱掉庞培。这个狡猾的混蛋!那天晚上他就是在这里把我甩掉的。”
狗突然从大路拐进了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往前走了半英里,小道又拐进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从这儿向右转弯就通向了我们刚刚离开的城镇。大路转向城南,与我们出发的方向刚好相反。
福尔摩斯说:“那么这样拐来拐去完全是为了我们喽?难怪我在那些村子里打听不出什么东西来。大夫这个把戏玩得真不错呀,不能不让人想知道他精心设计这样的骗局目的何在。我们右边一定是川平顿村了。天哪!马车从拐弯处过来了。华生,快,快,不然我们就会被发现了!”
福尔摩斯拉着极不情愿的庞培穿过一个大门,躲进了田里。我们刚刚在篱笆下躲好,马车就咕隆咕隆地驶了过去。我看到车内坐着阿姆斯特朗大夫。
只见他拱着双肩,两手托着头,一副沮丧的样子。我从我同伴那严肃的神情上看出他也注意到了。
他说:“恐怕我们的调查会以悲剧结束。我们马上就会知道的。来吧,庞培。啊,是那边田里的农舍!”
毫无疑问我们的旅程已经到了终点。庞培在大门外跑来跑去,兴奋地叫着,大门外还可以看到马车的车轮印。一条小道通向这座孤零零的农舍。福尔摩斯把狗拴在篱笆上,我们急忙走到屋门前。他敲了敲简陋的小门,但没有回音。可是屋里显然有人,因为我们听到里面有低低的声音,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与绝望的呜咽声。福尔摩斯迟疑了一下,回头看看刚刚走过的大路。
一辆四轮马车正在驶过来,那对灰色的马儿毫无疑问地说明是大夫的马车。
福尔摩斯叫道:“唉呀,大夫又回来了!这回问题可以解决了。我们一定要在他到来之前看看是怎么回事。”
他推开门,我们走进门道。呜咽的声音显得大了一些,后来变成了长长的悲嚎声。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福尔摩斯飞快地跑上楼,我也紧跟了上去。
他推开一扇半掩的门,眼前出现的情景让我们站在那里目瞪口呆。
床上躺着一个已经去世的年轻而又美丽的姑娘。金色的头发环绕着她宁静而苍白的脸庞,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无神地向上瞪着。一个年轻人半坐半跪在床上,脸埋在床单里,哭得浑身颤抖。他完全沉浸在悲伤中,直到福尔摩斯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才抬起头来。
“你是戈弗雷·斯通顿先生吗?”
“是的,我就是。可你来得太晚了。她已经死了。”
这个年轻人悲伤得都搞糊涂了,没有看出我们根本不是来看病的医生。
福尔摩斯正准备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并且告诉他,他这样突然失踪把他的朋友们都吓坏了,这时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门口出现了阿姆斯特朗大夫那张严峻、沉痛和责问的脸庞。
他说:“先生们,你们终于达到目的了,而且选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闯了进来。我是不会当着死者的面大吵大嚷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我年轻一点,我绝不会饶恕你们这种恶劣的行为。”
我的朋友十分庄重地说:“对不起,阿姆斯特朗大夫,我想我们之间有些误会。要是您跟我们下楼,也许我们彼此可以解释一下这件不幸的事情。”
一会儿,这位脸色阴沉的大夫和我们到了楼下的起居室里。
“说吧,先生,”他说。
“我首先希望您能理解,我并不是受蒙特·詹姆士爵士之托,而且我在这件事情中是完全反对这位贵族的。一个人失踪了,我的责任是弄清他的下落。在我看来,只要事情能了结,只要里面不涉及到任何犯罪的问题,我也急于让流言平息下去,而不是把它四处传播。既然这起事情中没有犯法的地方,您完全可以相信我会守口如瓶,而且决不会让报界知道。”
阿姆斯特朗大夫赶紧往前走了一步,紧紧握住福尔摩斯的手。
他说:“您是个好人。我错怪了您。我真得感谢上帝让我掉转马车回来认识了您,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把可怜的斯通顿留在这里不合适。既然您已经知道了那么多,问题也就好解释了。戈弗雷·斯通顿一年前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疯狂地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并且娶了她。她美丽、善良、聪明,不会让任何娶她的人丢脸。但是戈弗雷是这位脾气怪戾的老贵族的继承人,如果结婚的消息传到他那里,戈弗雷一定会失去继承权。我非常了解这个年轻人,而且因为他有许多优点而喜欢他。我尽我最大的力量帮助他。我们尽量不让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只要有一点点风言风语,很快就会弄得人人皆知。幸亏有这么一座偏僻的农舍,也幸亏他自己小心谨慎,戈弗雷到现在一直没有让人知道他的秘密。知道他们秘密的只有我和一个忠实的仆人。这个仆人现在到川平顿请人去了。后来,沉重的打击落到了他们头上。他妻子得了重病,是最可怕的肺病。可怜的戈弗雷悲痛得都要发疯了,但是他还要去伦敦参加这次比赛,因为不去就要做出解释,这样就会暴露他的秘密。我给他发了封电报安慰他,他回电求我竭尽全力。这就是您想法看到的那封电报。我没有告诉他病情有多么危险,因为我知道他在这儿也起不了作用,但我把实情告诉了姑娘的父亲,谁知这位父亲考虑不周,把情况告诉了戈弗雷。结果,他像发疯似的立刻赶了回来,一直就这样跪在她的床前,直到今天早晨死亡结束了她的痛苦。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全部情况。我相信您和您朋友都是靠得住的人,都会守口如瓶的。”
福尔摩斯紧紧握住大夫的手。然后他说:“走吧,华生。”
我们离开那座充满忧伤的房子,走进了冬日惨淡的阳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