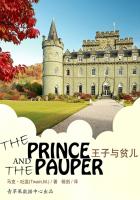可他也像她一样迅速,不顾一切地逃走了。不一会,她又顺着大路骑了回来,傲然地昂着头,不屑再去注意那不声不响的尾随者。他也转过身来,依然保持着那段距离,直到转过弯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我呆在藏身的地方没有动;幸好我没有动,因为那个男人不一会儿又出现了。这次他不慌不忙地骑了回来,拐进庄园的大门,下了车。我看见他在树丛中站了几分钟,抬起双手,好像在整理他的领带。然后,他又上车从我身边骑过,沿着马车道朝庄园驶去。我跑过石南灌木地带,透过树丛望了过去。我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远处古老的灰色建筑和高耸的都铎式烟囱,只是那条马车道穿过一片浓密的灌木林,因此我没有能再看到那个人。
不过,我倒是觉得自己这一上午已经干得很不错了,便兴致勃勃地走回法罕姆。当地的房产经纪人没能告诉我任何有关查林顿庄园的情况,而是把我介绍给了帕尔马尔的一家着名的公司。我在回家的途中在那里停留了一下,受到经纪人的殷勤接待。不行,我不能租用查林顿庄园来避暑了。我来得太晚了,庄园一个月前就租出去了。租它的是威廉逊先生,一位体面的老先生。那位彬彬有礼的经纪人客气地说他别的无法奉告,因为他不能议论他主顾的事。
当天晚上,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全神贯注地听了我向他作的冗长的汇报,却没像我期待的那样说上一句会让我高兴的称赞的话。恰恰相反,当他评论我做过的事和没有做到的事的时候,他那严峻的脸甚至比平时更加严肃。
“我亲爱的华生,你藏身的地方选得很不得当。你应该躲在树篱后,这样就能仔细看看那位有趣的人。结果呢,你却躲在几百码远的地方,告诉我的情况比史密斯小姐还要少。她说她不认识那个人,我确信她认识。要不然,那个人为什么刻意不让她靠近,不让她看清他的面容呢?你说他弯腰伏在自行车把上,你看,这不又是为了不让人认出他吗?你确实没把事情办好。他进了那栋房子,你想查明他是谁,却跑到一个伦敦房产经纪人那里!”
“那我该怎么做呢?”我气鼓鼓地嚷了起来。
“你应该去离那里最近的酒店。那是乡下人说东道西的中心。他们会告诉你每个人的名字,从主人到帮厨的女仆。威廉逊?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如果他上了年纪,那么他决不是在那姑娘飞速追赶下能够潇洒地逃走的那个人。你这次远行的收获是什么呢?弄清楚了那位姑娘讲的是真话,这我从来就不怀疑。弄清楚了那位骑车人和那庄园之间有联系,这我也不怀疑。弄清楚了庄园被威廉逊租用了,这谁查不出来呢?好了,好了,我亲爱的华生,不要显得那样灰心丧气。星期六前我们反正也行动不了,我还可以亲自去做一两次调查。”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到了史密斯小姐的一封来信,简要而准确地重述了我所看到的那些事,可是信的要点却是在附言中: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会尊重我的隐私的。我在这儿的处境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因为我的雇主向我求了婚。我相信他的感情是非常深厚、非常高尚的。我当然把我已经订婚的事告诉了他。他十分认真、十分和气地接受了我的拒绝,可是你看得出来,我的处境有点尴尬。
“我们年轻的朋友好像陷入了困境,”福尔摩斯看完信后,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案子的确比我原来想象的要更有趣,发展的可能性也多得多。我早就想到乡下去过一天安静太平的日子,现在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去,试一下我的一两个推论。”
福尔摩斯在乡下安静度过的这一天是以奇特的结局结束的。他晚上很晚才回到贝克街,嘴唇破了,额头上青肿了一块,还带着一副狼狈的神情,完全可以成为苏格兰场调查的目标。他对自己的历险感到非常有趣,一边讲一边开心地哈哈大笑。
“我一向很少锻炼,所以锻炼一下真是件乐事,”他说。“你知道,我精通拳击这门英国优秀的传统体育运动,偶尔还能把它派上点用场,比如说今天,要是没有这一手,我肯定会一败涂地。”
我请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找到了我提请你注意的那个乡村酒店,并在那里悄悄地进行了调查。在酒吧间里,饶舌的酒店老板把我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威廉逊是个白胡子老头,和几个佣人一起住在庄园里。有谣传说他曾当过牧师,好像现在也还是,可在他住进庄园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有一两件事情让我觉得他不像牧师。我查询过一个牧师机构,那里的人告诉我,曾经有一个叫这名字的牧师,可他过去的行为极不光彩。酒店老板还告诉我,庄园每到周末总有一些来客——“是一伙下流痞,先生”——特别是一个长着红胡子的伍德利先生,更是每次必到。我们正谈到这里,那位伍德利先生竟然走了进来。他一直在酒吧间喝啤酒,把我们的话全部听了进去。他问我是谁?想干什么?
问那些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口若悬河,什么样的话都说了。他骂到最后,凶恶地朝我反手就是一拳,我没来得及完全躲开。后来几分钟里就有好戏看了。
我对那凶恶的暴徒一顿拳打脚踢,结果就成了你看到的这副样子。伍德利先生坐车回去了,我的乡间之行也就这么结束了。我得承认,不管多么有趣,我这次萨里边界之行的收获并不比你上次的收获大。”
星期四我们又收到了那位委托人的一封信。她写道:
福尔摩斯先生,听到我要辞去卡如瑟斯先生的聘用,你不会感到吃惊吧。尽管报酬丰厚,我还是无法忍受这尴尬的处境。我星期六就回城,不打算再回去了。卡如瑟斯先生已经准备了一辆马车,即使那条偏僻的路上曾经发生过危险,那么这种危险现在也过去了。
至于我离开的具体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我和卡如瑟斯先生之间的这种尴尬处境,而且是因为那个讨厌的伍德利先生又来了。他本来长得就丑,现在好像更丑了,因为他似乎出了车祸,全身都挂了彩。我是从窗户里面看到他的,而且可以高兴地告诉你,我没有碰上他。他和卡如瑟斯先生谈了很久,卡如瑟斯先生后来好像很激动。伍德利肯定就住在附近,因为他没有住在卡如瑟斯家,而我今天早晨又看到他在灌木丛中鬼鬼祟祟地活动。我不久就会在这地方碰到这头凶猛的吃人野兽了。你简直不知道我是多么憎恨他、害怕他。卡如瑟斯先生怎么能容忍这样一个家伙呢?不过,我的一切麻烦到星期六就都结束了。
“我相信是这样的,华生,我相信是这样的,”福尔摩斯神色严峻地说。
“有个极大的阴谋正围绕着这个姑娘,我们有责任确保她在这最后一趟旅行中不受任何伤害。华生,我想我们星期六早晨必须挤出时间一起去,以保证这次奇怪而广泛的调查不至于出现不幸的结局。”
我得承认,直到那时我一直都没有把这个案子当回事,因为我并没有看出里面有危险,只是感到它荒诞、古怪而已。一个男人埋伏着等待并尾随一个漂亮的女人,这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如果他只有那么一点点放肆,都不敢向她表白,甚至在她迎上来时反而逃跑,那他就不是十分可怕的暴徒。
那个恶棍伍德利是与众不同,可除了那一次外,他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们的委托人。他现在到卡如瑟斯家去不是就没有硬闯到她面前去吗?那个骑自行车的家伙无疑是酒店老板所说的在庄园周末聚会的一员,可他是什么人,他要干什么,这仍然是个谜。真正使我感到这一连串怪事后面可能隐藏着悲剧的是福尔摩斯严肃的表情,以及他在出门时把手枪放进口袋这一事实。
下了一夜的雨后,早晨阳光灿烂;长满了石南灌木的乡村盛开着一丛丛耀眼的金雀花,在看厌了伦敦那阴郁灰暗色调的眼睛里,这些花显得格外美丽。我和福尔摩斯走在宽阔而多沙的道路上,大口大口地吸着早晨清新的空气,聆听着鸟儿的歌声,体验着春天的气息。我们从克鲁克斯伯里山顶的路上,可以看见那座灰色的庄园耸立在古老的橡树林里。这些橡树虽然古老,但比起它们所环抱的建筑来说仍显得年轻。福尔摩斯指着长长的一段路,这段路像一条红黄色的带子一样蜿蜒在棕黑色的石南灌木丛和嫩绿的树林之间。远处出现了一个黑点,可以看得出是一辆单马马车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移动。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惊叫了一声。
“我留了半小时的余地,”他说。“假如那是她的马车,那她一定是在赶早一趟的火车。华生,恐怕没等我们见到她,她就经过查林顿了。”
我们一走下山顶就看不到那辆马车了,但我们快步往前走去,速度很快,弄得我落到了后面,开始显露出平日安坐为生的坏处。然而,福尔摩斯一直锻炼有素,因为他总有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他那轻快的步子一直没有放慢,突然,他在我前面一百码的地方停住脚步。我看见他举起一只手来,做出痛苦而绝望的手势。与此同时,弯路上出现了一辆空马车,吱吱嘎嘎朝我们急驶而来。拉车的马一路小跑着,缰绳拖在地上。
“太晚了,华生,太晚了!”当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福尔摩斯身旁时,他叫道。“我真笨,居然没有想到她会坐早一点的火车!一定是劫持,华生,是劫持!是谋杀!天知道是什么!挡住路!把马拦下!就是这样。好了,跳上来,看看是否能补救一下我犯的大错所造成的后果。”
我们跳上马车。福尔摩斯把马调过头来,朝它狠狠抽了一鞭子,我们便顺着大道往回疾驰。马车转过弯之后,介于庄园和石南灌木林之间的整个路段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一把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
“就是那个人!”我喘着气说。
一个孤身骑车人正朝我们冲过来。他低着头,拢着肩,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脚蹬子上,像赛车手一样骑得飞快。他突然抬起那张胡子拉碴的脸,看到我们正朝他驶来,便停住车,从车上跳了下来。他那漆黑的胡子与惨白的脸庞形成鲜明的对比,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好像他正处在极度兴奋之中。
他紧盯着我们和那辆马车,然后脸上露出诧异的神情。
“喂!你们停下!”他大声叫到,用自行车拦住我们的路。“你们这马车从哪儿弄来的?把车停下!”他喊叫着从侧面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我说停车,否则我就要让那匹马尝一颗子弹了。”
福尔摩斯把缰绳扔给我,自己从马车上跳了下来。
“我们正要找你呢。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在哪儿?”他快而清晰地说。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你们坐在她的马车上,当然应该知道她在哪儿。”
“我们是在路上见到这马车的,上面没人。我们把车赶回来是去救那姑娘的。”
“上帝呀!上帝呀!我该怎么办呢?”这位陌生人绝望地叫着。“他们把她抓去了,那个该下地狱的伍德利和那个恶棍牧师。快点,伙计,快点。
你们要真是她的朋友,就跟我一起去救她。我就是横尸查林顿森林也在所不惜。”
他手里拿着手枪,脚步凌乱地朝树篱的一个豁口奔去。福尔摩斯紧跟着他,我把马放到路边吃草,也跟在福尔摩斯后面跑过去。
“他们是从这儿穿过去的,”他指着泥泞小路上的几个脚印说。“喂!
等一下!灌木丛里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