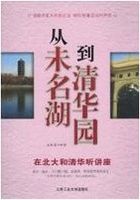父亲四十来岁,一米七的个子,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印象中的他总是一副心事重重,沉默寡言的模样。一身朴素的深色休闲着装,中年微微发福的脸上有一头微微卷曲,若隐若现着头皮的短发。矫健的却已日渐失去硬朗的身姿,宽厚结实的却渐渐被岁月重担压迫得已显疲态的双肩。
有时因工作出差或加班劳累,父亲的上唇,下巴似乎又悄无声息地冒出一圈浓密的胡须,他却总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直到什么时候儿子提醒起:爸,你的胡须几天没刮了,该去整理一下……他这才去到镜前,拿起那把久未动过的剃须刀,刀片由于久置未用,已显锈迹,父亲更换了刀片后,对着镜面,一只手托起下巴,另一只手抓着剃须刀,沿着胡须的纹路,艰难地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刮得一干二净。直到凝望到父亲光溜溜的下巴时,我的心才稍显欣慰。
大约儿子不愿看到父亲冒着浓密胡须的脸于不经意间显出苍茫衰老的表情,尽管岁月流逝,那些往昔稚嫩的年轻都将被打磨得只剩可怜的回忆,父亲的年轻也只是海市蜃楼。于我似乎未曾窥视到他矫健结实的背影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颗被苍穹岁月打磨过的心。它隐藏在万丈深渊,纵横交错的根苗以及被琐碎生活页面堆积的岁月书本中。在我十岁之前的那段日子,那是一个清晰却又模糊的幸福光景所处的年代。已不记得父亲母亲于何时结识,度过了怎样一段甜蜜的恋爱时光,从未听他们向我仔细讲述过,孩童时的自己似懂非懂,曾试探性地问父亲,关于他们的爱情故事,父亲只是微笑地抚摸着我的额头说:“孩子,我和你母亲只是很平凡的由相恋到结婚的过程……”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亦是相同的答案。
大约他们那代人的情感是我永远也无法去验证的,却知道于此有了我的诞生,那是父亲最值得骄傲的事,因为他有了儿子。那时,父亲总会在闲暇时抱起小小的我,用他初冒的尖尖胡须来回不断地摩擦着我光滑的脖颈。接连不断的欢笑声久久回荡在小小的客厅里。一种幸福洋溢其中。
于我总爱在任何场合之下站在父亲身后,紧紧地抓住他厚实的手臂,我的手掌与父亲的手臂间没有任何缝隙,然后怯弱地望着周边陌生的,时刻充满危机感的世界。此时父亲的身影无疑是我最温馨的避难所,孩童时的我对父亲有着与对母亲同样的依赖。
父亲在市区一所图书馆工作,虽然平时工资不高,在我心里,他却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但凡遇到不顺心之事时我总爱找父亲倾诉。那时自己还是家中的独苗,每天傍晚他下班回来,总爱与我打闹嬉戏一番才去忙乎自己的公务。他总是不时地关心着我的学业,每次在我完成家庭作业后,他总要亲自过目,指出优缺点并让我改正,这才算完事。
望着父亲那双圆睁明亮,炯炯有神的眼,感到一股力量如同血液般流淌在我孩童的小小身躯里。父亲在我心中仿佛一道暖阳,而我亦有个幸福美满的家。
岁月在悄无声息中继续前行。
在我二十岁之前的那段日子,家中又添了一位新成员——妹妹。也许是父亲看到我在家中那终日孤零的身影,于心不忍,便和母亲商量为我增添了妹妹。便是从那时起,我有了作为哥哥的骄傲。从此以后,家中有四个成员,于我上有父亲母亲,下有乖巧可爱的妹妹。父亲总是笑容满面地看着他两个至亲至爱的孩子,虽然我那时未曾真正懂得他的心,却想没有任何时刻会比现在更让他感到幸福了。
从那时起,上苍也许已在暗暗算计着什么,不敢说它是否会嫉妒这样幸福的一家子,却已印证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07年的夏天,日子如行云流水般流淌着,一场人间悲剧却悄无声息地降临到父亲以及我的一家之中。就在春节刚过不久,年旬七十的爷爷便患胃病住院了,因不能确定病情性质发展时间的早晚,须进行手术才能查出结果。
在动手术的前晚,父亲和母亲似乎在躲避着我和年幼的妹妹在商量着什么。于我虽度过了童年,却仍处在懵懂的少年时期,对于他们商量爷爷病情的话语并未放于心上,更不懂得那病魔是如何地残忍。伴着他们在客厅中若隐若现的细声谈话,我沉沉地入睡了。
梦境中似乎看到父亲的胡须又长得浓密了些。第二天清晨,父亲送了妹妹回校后,便带上母亲匆匆忙忙地出了家门,我知道一定是去医院了。看着他们的身影,我的心微感苦涩。在父亲走出家门前,不经意间,我看到他的脸,宽厚的下巴已泛出一圈浅浅的胡须,环绕着他的整个下巴在生长着。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不是梦境。只是不明白父亲与母亲在出门前为何不带上我一同前往医院。
爷爷怀着众多亲人忐忑不安与祈祷的心被推进了手术室,术中几小时却似度过了半世纪般漫长,结果出来了:晚期胃癌!这样的结果无论对父亲还是整个家庭而言都是晴天霹雳。中午回到家,父亲拿着医疗报告单一脸平静地点燃了一支烟,并狠狠地吸了一口,随着腮帮深深凹陷又鼓起,一股缭绕的烟雾弥漫在他的胡须里,久久地未曾散去,一张黯淡的没有一丝光泽的脸在自言自语着:“早也料到这结果。只是没想到……”他欲言又止。此刻却有谁知道此时父亲的心如同掉入万根寒光闪闪的针尖中,那种早已被跌得血肉模糊的痛楚。
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淡淡说道:“过几天去医院看望下爷爷吧。”我点点头。并看着父亲有些疲惫的脸:“爸,你的胡须又长了,去整理一下吧。”父亲只是象征性地应了一声,便去忙别的事了。
五一假期,父亲带着我到医院看望了爷爷。当我问到为何不带上妹妹时,他只说妹妹还小,就不去了。沿着医院干净的花岗岩楼梯向着爷爷的病房走去,一路上我的心在咯噔着。终来到病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爷爷。他那有些臃肿的身躯上穿着一身病服,半躺在床头,布满皱纹的松弛皮肤的手背上贴着用于打点滴的医用胶带,几近光秃的脑袋上只零散地分布着几根风残白发,一双与涅槃岁月周旋了半个多世界的眼透着一丝因病痛的折磨而显出疲惫像。
在我进入病房前,于门口看到爷爷的目光在虚无的空间中游离着,虽只有短短几秒,却让我感到一股不安。看到孙子的到来,老人显然很高兴,病容一下子挂满期待的微笑,游离的目光仿佛转变成翘首的欣慰。父亲在来到病房后只对爷爷说了句:“爸,你们聊吧,我到外面走走。”说完便安静地走出去了。看着父亲的背影,我想起《平遥》:浑浑噩噩如一梦,传来慈母唤儿声。声声似有千均重,声声铭刻在心中。三九天,好大风,风中有个白头翁。七旬老父虽年迈,依旧为儿去担惊。父亲担忧着父亲,我亦担忧着他,似乎有种说不出的困惑。在他转身离去之际,我看到了那双同样泛着游离失所的目光。但此时,却还是强打笑脸与爷爷说着有关学习生活的琐碎事,奶奶便坐在病房一处椅子上边聆听着爷孙俩谈话,边微笑地削着手中的苹果。看着奶奶手中那只被一点点削掉皮的,逐渐显出本质的果子,我的脑海始终反复出现着那双游离的眼,顷刻,心神不宁。
几天之后,爷爷选择出院回到老家进行保守治疗,这意味着什么,父亲也许已心知肚明。在爷爷回到家的那段日子,他还会不时地对我说:“没课时多抽空回去看望下爷爷。”语气同样淡淡的,不同的是,这次言语间隙里似乎带着某种波澜汹涌的情绪,我默默地感受到了,只是远远未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此时父亲下巴的胡须似乎又浓密了一些,就在我刚想起要提醒他什么时,随着一阵外门锁的转动,他默然地走出去了。我明显看到父亲那双无奈地游离之眼。母亲在下厨,妹妹则在卧室里做着习题。仿佛一切没发生过,我亦在自我安慰着,但愿爷爷能好起来,不再看到他们那样的让我感到疼痛的眼神。
爷爷在老家那段日子,由他的两个儿子轮流照顾,父亲作为大儿子,忙里忙外,似照料在孕期前后的母亲般照顾着爷爷。由于奶奶年事已高,只能帮上一些轻杂活,父亲则几乎包揽了所有大忙。后来他的单位正逢上评职称时期,怕两兄弟实在忙不过来,父亲还特地花钱雇来一位与爷爷仿佛年龄的东北老汉帮忙照顾爷爷。
那位东北老汉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帮父亲减轻了不少负担。自回家后,爷爷的身体状况突然急剧下降,短短一个多月便瘦得只剩皮包骨了,原本我还想再多回去看望爷爷几次,却又不忍心目睹被病魔折磨摧残得已不成人形的爷爷。
父亲却仍在默默为照料老人而忙碌着,那些吐在痰盂上的痰,不时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恶臭,一口痰中不知隐藏着多少病菌,父亲却从无掩鼻避开之意,帮着处在人生最后阶段的爷爷擦背,倒痰,喂饭,洗澡……一天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每次他回到家时,我总会看到他的眼袋又加深了,胡须又变长了。父亲只是进行简单的洗漱后便又重新强打起精神投入到工作中,我注意到他的胡须一直未刮,下巴那一圈若隐若现的黑乎之影让我有种被钻心般的疼痛。
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我躺在床上,母亲与妹妹早已入眠,这晚轮到小儿子舅舅回来照顾爷爷,父亲才得以在家休息。静谧的夜色中仿佛只听到他平伏却又深长的鼾声。通过一方小小的卧室里散发着微弱的灯光中,我看到他微微起伏的胸膛与颤动着的下巴上那圈不知隐藏着多少苦累的胡须,心想:父亲已太累了,只盼那寂静的夜能再漫长些。
就在我伴着夏夜闷热的季风就要进入沉沉的梦境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划破这宁静的夜,亦惊醒了睡梦中父亲。挂断电话后,顿时,他睡意全无,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起床之后随即从卧室传来衣物与皮肤阵阵“咝咝——”的摩擦声,未曾入眠的我隐约有一种不详预感,而且愈发强烈。
之后父亲悄悄走到另一间卧室叫醒母亲,两个身影随着外门一阵轻微的开启声,便匆匆消失在门外的茫茫夜色中。依稀记得母亲在临行前的穿衣间隙,向着半梦半醒的我扔下一句:“爷爷走了……”听罢,那晚我彻夜未眠,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带着妹妹怀着一种沉底的悲痛之心回到老家,奔丧。
此时,爷爷被一张白布轻轻地盖着,看不到他的任何表情,更看不到他昔日矫健硬朗的躯体,怎么亦无法接受躺在那张床上的便是我那曾经笑眯眯的爷爷,但我相信老人是安详地离开了。所有的儿女都已赶回老家,只为送父亲最后一程。前来的还有爷爷生前的部分老干部同事。原本狭窄的老家客厅一下子被前来的悼念者挤满,令人窒息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茴香伴着清脆如初开的莲的悼铃声,与微泛潮湿的各种汗味混合在一起,让夏日的屋内空气突变压抑,以及带着肃穆的沉重。
父亲与其他亲人静静地坐在房间的一处地板上,跟着前来诵经超度的和尚一同为爷爷祷告着。我这才看清楚父亲的胡须由于几个月未刮,其浓密程度已完全覆盖了他整个下巴,上唇,脸上油光油光的,卷曲的短发无精打彩地垂在光滑的脑袋上,看上去似乎苍老了十岁,更像一个拾荒的糟老头。
那浓密的,乌黑的胡须里究竟隐藏着父亲多少爱与遗憾,也许我未曾知道,却从他那双布满血丝的混浊而又清澈的眼里看到一个高大的身影。送走了爷爷后,父亲才把那浓密的胡须刮掉,胡须随同丰富的白色泡沫,连同悲痛的思化作三千东逝水似流水般融入人间的滚滚长河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似乎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平静生活状态,我却始终未曾懂得他那浓密的,如同铁树般尖锐生在表皮的胡须在背后的辛酸是怎样浸染着一个中年人的灵魂。
在我二十出头的那段日子,没想到之前的只是悲痛的开端,原本我以为这因风雨的洗礼已微微有些摇曳飘摇的家就此能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却没想到一个更大不幸悄然无息地降临,让我的一家措手不及,甚至面临精神的崩溃瓦解。
就在爷爷离世后两年多之后,我那年幼的妹妹在一个繁忙的五月天猝不及防地远离人世。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这次由于身处千里之外的大学未能前往送她。这一别便是一辈子。
恍然间,时光回溯,一年前在车站,父亲母亲与妹妹一同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着我踏上新的求学征程。
随着长途大巴的缓缓开动,一个新的寻梦征程开始了。隔着车厢厚厚的玻璃,我看到父亲的身影,他站在月台上,牵着年幼妹妹的小手,下巴的胡须已全无踪迹,原来苍老的父亲竟也有如此年轻的光景,于我总期盼这光景能就此延续下去,不再有伤悲,不再有离合。而上苍却从不将风平浪静赋予我一家,大约这已是冥冥之中一种注定。
父亲母亲与妹妹,他们目光中充满翘首的期盼,无论如何亦想不到昔年的寒假会是我与妹妹在人世的最后相见。
当电话中传来母亲泣不成声的言语时,我惊呆了,天地仿佛在顷刻间凝固倒塌。由于受雨天影响,第二天下午我才赶到家,只见母亲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父亲则刚从外面回来,他一言未发地走到椅子前叹了口气便轻轻坐下。点燃一根杂牌烟,两个指头紧紧地夹着烟尾,父亲的眼角布满深红深红的血丝,似纵横交错的红带,这里面的混浊或清澈的记忆,如一潭停滞的死水,让我心疼担忧。
父亲下巴的胡须不知什么时候再次变得茂密,似麦田里被荒芜了几世纪的丛草。一个中年男人在失去最心疼的灵魂支柱时会是怎样的彻心彻肺,我明显感到他的身影带着一股沉重的伤悲。父亲边吞吐着烟雾,脸上的肌肉在缭绕的烟雾中微微抽搐,带动着他那渗透了整个下巴的胡须。
妹妹的葬礼我终因迟到未能赶上,却没想到这一别却是永远。我更不知道倘若赶上又该如何去面对那幼小冰冷的躯体。两年前爷爷离世是因人生已走到终点,父亲也许还可自我安慰。如今妹妹的猝然离去让他如何接受,也许唯一让父亲感到欣慰的便是还有我这个儿子,父亲母亲唯一的儿子。于是我总以为要成为他们的骄傲,为仙逝的妹妹,亦为父亲母亲。
这次回家我没有再次提醒父亲剃须,却终于知道那是他的默悼,他的不修边幅只因那茂密的胡须中承载了太多沉重的深爱。他的沉默是一种沉心的爱,这种爱能穿越任何时空。当我再次踏上返校的征程时,同样的车,同样的人,同样的景,却是不同的时光,原先不知时光竟可以残忍到将一个人的身躯彻底湮灭在岁月长河里。
父亲母亲站在车站月台上目送着我,往昔他那双厚实的曾牵过妹妹的手竟不知往哪放,却牵着母亲的手臂。这一刻,我的泪已在心间悄然流淌。
迷茫的夜色中,我透过厚厚的,布满长途模糊记忆的车窗,看到站在长途车站出口的父亲,他流离的目光似乎在极力眺望寻找着车厢中的我,当大巴驶出站口,缓缓地经过他身边的公路时,隔着车窗,我看到他那张流露着沧桑却没有了胡须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