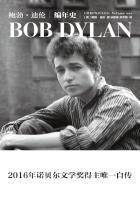贾士芳刚一落座便道:
“贫道看万岁爷的气色想必圣躬已安。看来贫道虚此一行。”
雍正忙道:
“不,朕正有事烦劳仙长。请仙长不吝赐教。”
“万岁爷有话请讲,且莫折了贫道的寿。”
雍正笑道:
“仙长位列仙班,也有寿数吗?”
贾士芳郑重地道:
“贫道祖上是医学世家,自然对医术也略通一二。偶尔救人危难也是依着医理,断无妖魔邪术。所以贫道只是一俗人,无缘位列仙班。”
“请问道长高寿几何?”
“贫道虚度九十一载。”
雍正、弘历、弘昼都惊讶不已。看他那长长的银须银发,想来不虚。雍正感叹地问道:
“仙长如此高寿,莫非服了长生不老仙丹。”
贾士芳微微一笑道:
“贫道只相信人能长寿,不相信长生不老。当然也不相信世间有长生不老仙丹。”
弘昼惊奇地问道:
“照你这么说,世间那些炼丹的道士全是骗人的。”
“那倒未必。”贾士芳解释道,“道家炼丹,也是依着医理,由药石、草药提炼而成。虽不是长生不老的丹药,但如果配制合乎医理,为人增寿倒也不假。贫道苟活至今,多半是服了自制的丹药的缘故。”
雍正心中一动,觉得贾士芳说得有根有据,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道士胡乱吹嘘。便故意问道:
“想不到仙长还有如此本领。仙长炼的长寿丹药可否让朕一见。”
贾士芳摇摇道:
“真是不巧,贫道观中还有一粒,只是不曾带在身上。贫道今晚是专程给皇上看病的,只带来治病的药。”说完,他从道袍里取出一个纸包,放在御书案上。
允昼伸手拿过来,打开纸包一看,是两粒白色的药丸,便笑道:
“皇阿玛的病已经好了。吃了你这药,也说不准是你的药管用,还是皇阿玛根本就没有病。”
雍正把眼一瞪,斥道:
“弘昼,不得对道长无理。还不代朕谢过道长赠药之恩。”弘昼嘻嘻一笑,向贾士芳略一躬身道:
“仙长,小王刚才跟您闹着玩呢,千万别放在心上。”
贾士芳无所谓地一笑,道: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贫道的药效如何,待万岁服用之后。自然会有公论。”
雍正感叹道:
“仙长妙手回春,朕早已见识过。只是刚才仙长所说自炼的长寿丹药,朕还没有见识过,岂非一件憾事。”
“这个容易。”贾士芳道,“待贫道回到观中采集药石,提炼出丹药,送进宫中就是。万岁爷,您也该安歇了。贫道告辞。”
雍正也不留他,吩咐弘昼派几个亲兵护送到白云观。
贾士芳走后,雍正便命朱儿拿过贾士芳送来的药。弘历一见,伸手阻拦道:
“皇阿玛,儿臣不明白您为什么这么相信贾士芳,如果他和邬思道串通一气,图谋不轨岂不是害了您。”
雍正没有搭理,反而向朱儿命道:
“朱儿,把贾士芳的那两粒药服下去。”
朱儿莫名其妙,手拿着小纸包,呆了半天才道:
“万岁爷,这药可是贾士芳给您服用的,奴才吃下去有什么用?”
“少废话,朕要你吃下去你就吃下去。”
“好,奴才遵旨!”
朱儿不敢多说,把那纸包里的两粒药丸全部倒进嘴里,也不用水冲服,他一仰脖儿便吞了下去。完了,还故意张开嘴巴给雍正和弘历看。
弘历眼睛不眨地盯着朱儿,一声不响。雍正才道:
“贾士芳和邬思道交往甚厚,朕不是不知道,可是他医术高超,名满京城。如果朕能把他留在身边,充作太医,岂不是好事一件。而且此人精通炼丹术,如果真能使朕长寿,岂不是我大清之福。当然,朕也有防他施奸的办法。凡他要朕服用药,必先由御前太监服用,确信无碍,朕才服用。”
弘历这才明白雍正是一心要求长寿,才宠信起贾士芳。想想弘时已死,虽然将来承继大统的非他莫属,但雍正一心想长寿,就注定自己这个储君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变为人君。
弘历极聪明,他知道自己不宜在长寿这个问题上跟皇阿玛多说。因为那样做极易引起生性多疑的父亲的猜疑。于是他岔开话题道:
“皇阿玛刚才说贾士芳跟邬思道交往甚厚,儿臣突然想到邬思道会不会就藏身在白云观,明日儿臣就派人去搜。”
“不必了,”雍正摇摇左手道,“邬思道知道朕很清楚他和贾士芳的交情,当然不敢去白云观。何况,朕已派人暗中搜过两次。”
弘历一听,皇阿玛果然虑事周到,处处想到自己前边,他由衷地感叹道:
“皇阿玛,您不愧为一代圣明之主。”
贾士芳由弘昼的两个亲兵护送出了紫禁城往南走不到二里地,贾士芳便道:
“两位军爷请回吧?”
两个亲兵知道他是神医,又是皇上看重的人,不敢怠慢,忙道:
“这黑灯瞎火的,仙长一个人走道儿我们哪能放心,再说,王爷的命令我们也不敢不从。”
贾士芳一摆手道:
“不妨,贫道不告诉你们王爷就是。二位放心地回去吧。”
两个亲兵求之不得,忙把一个灯笼送到贾士芳手里,说声,“道长走好!”已是往回走出多远。
贾士芳是走惯了夜道的人,便把灯笼一扔径直往白云观走去。他虽然是九十多的老人,但脚步却比年青人还快。不过半个时辰,便到了山门前。此时已是更深夜静,白云观内除了一两声钟声,一片寂静。贾士芳轻轻一敲山门,里面传出一个道童的声音:
“谁呀?”
“我!”
“是师父!”
山门打开,贾士芳走进去,责怪道:
“妙空,为师不是让你早些睡觉吗?明日还要做早课呢!”
“师父,”妙空声音低低地道:“邬先生来了,在三清阁呢!”
贾士芳吓了一跳。忙道:
“快,带师父去见他。”
三清阁在邱祖殿的后头。贾士芳刚穿过邱祖殿,便看见三清阁里亮着灯,灯光下,一个人影正在不慌不慢地舞着剑,贾士芳一步跨到门前,轻轻地敲门。
“谁?”“邬先生!”
黑影立刻收势,走到门前,把门打开,惊喜地叫道:
“贾道长,你总算来了。”
两人手牵手在蒲团上坐下。妙空过去,献上茶。贾士芳一手端着茶杯,来不及品茶忙问道:
“邬先生,这几天巡防营搜捕得正紧,我这道观也被粘杆处暗中搜查过。你怎么还敢到处乱跑。”
邬思道脸色忧郁,低着头抚摸他那把久违了的宝剑,轻轻叹息一声道:
无限伤心夕照中。
故国凄凉,剩粉余红。
金沟御水日西东,
昨岁陈宫,今岁隋宫。
往事思量一饷空。
飞絮无情,依旧烟笼。
长条短叶翠蒙蒙,
才过西风,又过东风。
贾士芳哂然一笑道:
“小老弟,复国壮志难酬吧!”
邬思道赫然大怒,对着贾士芳吼道:
“贾老道,你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贾士芳见他戚然动容,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忙解释道:
“小老弟,我是前朝人,祖上受满清所害,至今大仇未报,我怎么会忘了亡国之恨呢?只是这大清王朝正值鼎盛之时,万民受其物化,不思前朝,你我虽有报国之志,又能奈其何。小老弟,你处心积虑,在雍正跟前混了这么多年,又能如何?”
邬思道被他说得更加心灰意冷,但他不甘心,愤恨地道:
“弘时是个废物,他如果有弘历一半的才能,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我的大计也不至于落空。”
贾士芳一捋胡须道:
“小老弟,过去的事就别想了。还是想想跟前怎么办?”
邬思道咬牙道:
“不是鱼死,就是髓破。我现在只有下下之策,杀雍正。”
贾士芳一怔,一捋雪白的胡子道:
“要杀雍正你何必等到这个时候。在雍府时,要杀他何等简单。”
“此一时,彼一时嘛,我现在是朝廷通缉要犯。唯一能做的就是杀雍正。”
贾士芳不以为然地摇摇头道:
“杀了雍正,还有弘历当皇帝,天下还是满人的天下,只是改了个年号而已。”
“不,”邬思道愤然道,“雍正矫诏篡位戮杀手足,逼死亲娘,这种丧尽人伦的畜牲位列九五之尊,岂不是对天理的亵渎。”
“邬先生,你何时变成‘皇子党’了?”
“假老道,我是有真凭实据的。”
邬思道说着从贴身衣内取出一只金匣子,放到两人面前,然后把金匣子打开,从匣子里取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金质御纸,慢慢地展开。贾士芳仔细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那金纸竟是一份皇帝诏书,上面写道:
朕十四子胤穗即缵承大统
下面是满文,贾士芳不认识,邬思道便解释给他听。诏书的正中偏左下角盖着康熙皇帝的印信。
这分明是康熙皇帝传位给十四皇子允禵的遗诏,想不到竟会落入邬思道之手。
贾士芳这才相信世人传言雍正矫诏篡位果然是事实,不由气得他银须乍立,以手击地骂道:
“雍正果然丧尽天理人伦。这样的畜牲岂可再为人君。”
邬思道见他动了真气,更进一步挑起他的反清情绪,慨然道:
“岂止一个雍正不该做我汉人人君,满人乃夷狄,都不能做我中原之君。东海夫子说得好,满人入主中原,是元朝蒙古人以来的第二次陆沉,汉人蒙受羞辱。这江山原本是我朱家的天下,可恨逆贼李自成聚众叛反,毁我朱氏江山于一旦。叛贼吴三桂不守人臣大义,卖主求荣,引满清八旗铁骑入关,践踏中原之地。满人得以入主中原,非仅八旗劲旅之力,亦倚仗汉人相佐之故。”
邬思道的这一番宏论,贾士芳只是洗耳静听,不置一词。他是明朝过来的人,明朝皇帝一个个荒淫放纵,不理朝政,致使宦官当道,奸臣逞凶,把大好河山搅得乌烟瘴气,千疮百孔,老百姓苦不堪言,倒是满人人关之后,尤其是康熙年以来,天下大治,百业兴盛,老百姓安居乐业。雍正改元以来,更是致力于刷新吏治、力挽颓风,生生造就一个太平盛世。贾士芳出身于医学世家,冷眼看世界,比较客观,明清两朝一衰一盛,他都亲历过,渐渐感觉到清朝的天下也不是那么暗无天日。自己何苦追思那个死去的明朝亡魂昵。但想想祖上之仇,仍耿耿不能释怀。
邬思道见他半天没说话,便一拉他的道袍道:
“老道,你剐才还说雍正当杀,怎么又没有下文了。”
贾士芳恍然大悟,道:
“无天理人伦,当然该杀,邬先生施出手段吧!”
“我?”邬思道为难地道,“我还要仰仗仙长相助。你是名医,可借进宫看病之便,伺机下手。”
贾士芳原本复仇之心有些淡了,被他说得心中一动。不错,眼下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真能置雍正于死地,一则可报祖上之仇;二则也伸张了天地正义。但一想雍正、弘历并不信任自己,便道:
“邬老道说得有理。只是雍正、弘历防范甚严,如何有机可乘。”
邬思道轻松地一笑,道:
“你是名医世家,在用药上做些手脚,岂是难事?既可安然脱身,又足以置畜君于死地。”
“不妥,不妥!”贾士芳连连摇头,“雍正用药,必先由御前太监试服,确信无碍,才自已服下。如果在药中下毒。岂不露了马脚。”
“老道,难道不能配制出只毒雍正,不毒太监的毒药吗?”
贾士芳被他说得笑了起来道:
“毒药岂能分出谁是主子、奴才?谁吃了它,它就取谁性命。”刚说完,他忽然一动惊喜地叫道:
“有了!”
邬思道心中一喜,忙道:
“快说,有什么妙计?”……
贾士芳双手合十道:
“先祖李时珍遗书中曾记载一种毒药,人服下后,只要不行房事,不纵欲,肝脾不张,则无碍,一经纵欲,肝脾大张,则毒性发作,半日可致人死命,无药可医。”
邬思道一拍手,连声道:
“好极了,仙长若能置雍正于死地,我便可以乘乱逃出京城,将康熙遗诏告知天下,则满清朝廷人心必失,我汉人便有机可乘了。”
贾士芳看不惯他那种朱氏后裔的作派,抑郁道:
“小老弟,别高兴得太早,这药还没配好呢。”
二、迟到的忏悔
雍正气息全无,双瞳渐渐散开。这时允禵赶到床前大叫:“四哥,等一步。”他忽然睁开眼睛,极清晰地说道:“十四弟,我对不住你。”说完,头一歪,再没有醒过来。
弘历毕竟年轻,守在雍正床前一宿没睡,依然精神饱满。天亮之后,他见父亲睡得正香便悄悄退出房去,到了门外,见惠儿、菊儿在门旁的长凳上打盹,便把她俩叫醒,仔细叮嘱几句,才走出养心殿。
军机处张廷玉、方苞和果亲王都已来到,见弘历走过来,三人一齐迎上前,张廷玉、方苞施礼,向安后道:
“四爷,今天就由您总理朝政,有什么要交待奴才的。”
弘历谦恭地道:
“几位都是老军机了,办起差来比我有经验。我要说的话就是,但凡有差事,只管放心大胆地去办,实在争议难决的事,再来问我,我不能决的,还有皇阿玛呢。”
允礼点头赞许道:
“宝亲王说得有理,虽说由他总理朝政,也不能大事小事都来烦他。下面能办的差事尽量在下面办。”
张廷玉、方苞二人听完弘历训谕。正要进房中办公。弘历却又叫道:
“皇阿玛特别叮嘱,今天一定要派人去易县请怡亲王回京,一则皇阿玛想见见他;二则盛郡王的丧事也要请他来。回去你们军机处派人走一糟,就说是皇上的口谕。”
“四爷放心,奴才记下了。”
张廷玉、方苞答应着,转身进房。
弘历想想再没有要交待的差事,便慢慢走进军机处旁边的松竹轩中。早有八个小苏拉太监站在两边侍候着。一见宝亲王进来,一个太监慌忙将泡好的浓茶放到书案上,另一个太监则赶紧将当天的折子放在弘历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