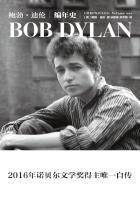“八阿哥说佟中堂怀有私心,排定的名次时没有与我们两人商定,现在去找他,佟国维也不会同意改动,一旦发榜更改就来不及了。八阿哥要求先斩后奏,出了问题他负全部责任。我一听八阿哥这样说了,也不再强求他去找佟中堂,他毕竟是皇子,皇上派他任南闱副主考也是有深意的,一是锻炼,同时也是对我们的监督。万一真的存在问题,我也要担当责任,便同意更改名次。至于如何更改,由八阿哥和几位阅卷师傅定夺。”
施世纶稍稍犹豫片刻又说道:“说心里话,我之所以没有参与八阿哥的更改名次也是存有私心。凭多年的为官经验,我已经感觉到要出事。当时只估计八阿哥与佟中堂之间会有一番激烈争吵,而我资历如此浅,哪有资格搅在其中呢?”
“后来,发生争执了吗?”
施世纶叹口气:“事情万万没有想到会一发不可收拾。发榜之后佟中堂才晓得他排定的名次给更改得面目全非,除了第,一名没有改变之外,其余九名全改动了,其中有四名被排除在前十名之外。”
“那位叫邬思道的考生呢?”曹寅问道。
“他最惨,由第二名降为副榜倒数第二名。”
“佟国维身为主考官怎能容许八阿哥这样做呢?”
“不容许也没有办法,榜已经发了。佟中堂去找八阿哥论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据属下报告,两人并没争吵,佟中堂铁青着脸回到住处躺了一天。”
“考生砸贡院的牌子,冲击贡院,殴打考官是怎么回事?”曹寅又问道。
“佟中堂与八阿哥没有争执,我估计这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过去了,佟中堂消消气也就算了,至于其他事回京之后由皇上论理。谁知发榜三天之后,我正在贡院处理一些琐事,猛然听到院外人声鼎沸,正准备出去观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一名随从慌慌张张跑进来拉起我就向后跑,说有数千名考生前来闹事,贡院的牌子都给砸了,正向后院冲来。后来才知道领头之人就是邬思道。他得知更动了名次,便煽动滞留在金陵的一千多名考生前来闹事。幸亏江苏巡抚张自德及时带兵赶到驱散考生,才没有酿成大的暴动,但贡院已被糟踏得满院狼藉,为首之人邬思道及十几名闹得最凶的人全部被抓。”
曹寅沉思片刻问道:“阅卷评定名次是在贡院中进行的,对外保密,没发榜之前考生是无法知道名次的,邬思道从哪里得知更动名次的消息?”
“曹大人,即使无人外泄消息,也没有不透风的墙,发榜之日自然是有人哭来有人笑。对于落榜之人当然不从自身找原因,不是埋怨出题太偏,就是猜测有人从中舞弊,如果有人从中吹风点火,这些饱受经书熏染、承蒙诗礼训教的书生也会做出非常事来。发生考生罢考与闹事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了,只是没有这次规模大、影响广而已。”
“那么你认为佟国维有没有收受贿赂从中营私舞弊呢?”
这话令施世纶十分为难,他想了想说:
“在下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不敢妄加猜测。”
曹寅又紧逼一句:“在八阿哥要求更改名次时,你有没有询问他是如何得知佟国维有受贿行为的?是否证据确凿?”
“我问了,但八阿哥不愿意讲。他说回京之后向皇上奏报,我也没有执意询问。”
曹寅沉默一会儿,呷口茶,又问道:
“施大人了解邬思道这人的底细吗?”
“原先并不知道,事发后才从江南学政张长庚那里得知邬思道是浙江人,家境十分富有,此人博学多才,在地方也小有名气。别的则一概不知。”
“那么此人现在关押何处!”
“据说在江南学政张长庚那里待押,一旦事有定论再作处理。”
曹寅又询问了一些细节,便告辞离去。
多日来佟国维一直坐卧不宁,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皇上一定会追查南闱考生大闹贡院的事,万万没有想到,这钦差会来得如此之快。更令他坐卧不安的是钦差竟是曹寅,这可是一个不好说话的人,他平日里只忠于皇上一人,与外臣也极少交往,像佟国维这样的一品官,又是皇亲国戚,曹寅都不主动结交。因此,两人关系十分平常。
佟国维恼怒儿子给他出了这么一个大难题,也恨自己一时手软心软接受别人的贿赂才做出这些蠢事。事上没有后悔药,现在必须想办法应付曹寅的访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如何搪塞曹寅呢?
佟国维正一筹莫展,忽然下人来报,说门外有两个和尚求见。
两个和尚?佟国维一愣,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挥手:
“不见,让他们快滚!”
传事的随从刚转身走开,佟国维又喊住了他:
“慢,让他们进来吧。”
文觉和性音进入客厅,见佟国维的神情沮丧,态度也不友好,并不放在心上,径自坐了下来。
文觉率先说道:“佟大人,皇上派曹寅来金陵的用意你已经明白了,不可再耽搁下去了,让张长庚放人吧,否则对大家都不利。”
佟国维背着手,来回踱几步,忧心忡忡地说:
“万一曹寅追问下来怎么办?他向我要人,我给不出人如何向皇上交代?”
文觉答道:“佟大人,钱我们花得不少,该赔的也都赔了,该送的也都送了,事情闹到这个后果再不放人,让我如何向朋友交待?再说事情办得如此糟糕,只能怨佟大人身为主考却当不了胤祀的家,也不是我们的错呀?”
佟国维气得哼了一声:“别说那点东西,宫中的御用品我见得多了,我府也不缺,不是看在四阿哥和我儿子的面子上,说什么也不会收你们的东西。”
“可你毕竟收了。”性音淡淡地顶了一句。
“我也不是没有为你们出力,若不是胤祀从中作梗——唉,如今说这些也没有用了。”
佟国维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性音看一眼文觉说道:“让考生到贡院闹事的主意也是佟大人出的,万一审讯起来邬思道经受不住拷打和盘托出,倒霉的只会是佟大人,请佟大人三思。”
佟国维忽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只是让你们煽动一下考生在贡院门前围坐争吵要求重新考试,给胤祀施加压力,然后把邬思道的名次给提进前十名,谁知——”
佟国维没有说下去,又缓缓坐了下来。
文觉叹息道:“我们并没有把给他疏通关系的事告诉他,他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只想凭个人真才实学挤入龙门。”
“既然他个人那么自信自负,你们何必多此一举呢?”
文觉看着性音,性音忙解释说:
“他父亲虽有些家产,但祖上几代人从来没有读书做官的,希望在儿子身上实现当官的梦想。虽然邬思道对今科十分自信,但他父亲却不这样看,认为儿子是不知天高地厚,对科考无望,这才肯花大钱四处拉关系为儿子疏通疏通的,他父亲只是暗中为儿子找门路,并没有向邬思道透露半点信息。发榜之日见自己名次那样低,很不服气。我们也不相信,来向佟大人询问情况,你授意我们让考生闹事,我们便把这个意思向邬思道透露一点,谁知这小子一呼百应,把事情闹大了。我等也没有想到会有此后果,早知如此,何必——”
文觉见性音说得太多,便打断他的话:
“佟大人还是把邬思道给放了跑,曹寅问起来你把责任全部推给八阿哥。只要你不说我们不说,曹寅纵有天大的本领也查无对证。佟大人在官场上已经几十年了。怎会被这点小事难倒呢?”
佟国维冷静地考虑一会儿,对文觉说道:
“我马上派人去找张长庚,令他放人,但你们也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佟大人尽管说——”性音急忙说道。
“你们立即把邬思道带走,最好不要回到他的家乡,找一个偏僻的寺院让他住下来安心读书,等过了风头再出来参加科考。凭他的才华,不求任何人也会榜上有名。”
“可如今的科场上实在是——”
佟国维打断了性音的话:“今年的例子你们还不明白,官场也不像你们认为的那样腐败,皇上也还着力整顿吏治,清理腐败。话又说回来,人情也是难免的,如果有可能,邬公子下次科考,我仍会尽力帮助,不过,文觉大师最好直接找四阿哥帮忙。倘若邬公子今科到北京应试,四阿哥为主考官,也许不会有这样尴尬的事。”
文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他还是忍住了。
佟国维送走二人,再三告诫他们要带邬思道到偏远的地方躲避起来,并告诉他们不得向任何人提及走门子的事,否则,倒霉的不仅是他佟国维,还有四阿哥。
等到文觉与性音走后,佟国维踌躇片刻,便喊来心腹吴文山,悄悄告诉他:
“你立即去找张长庚,传我的口信,先把姓邬的那小予两腿废了,然后派人送到夫子庙,那里有人接应。”
吴文山刚刚离去,就有人来报,说曹寅来访。佟国维吃了一惊,稍稍镇定片刻这才出门相迎。二人来到室内,佟国维便以攻为守地问道:
“曹侍卫是奉皇上之命来查问南闱举子闹事的吧?即使曹侍卫不来,我佟某也会查明真相将此事上奏皇上的。既然曹侍卫来了,那再好不过,省得我佟某人有口难言,有苦无处诉了。”
曹寅只好应付说:“佟大人也有难言之隐?好好,尽管说来,我老曹代你传给皇上。”
佟国维立即诉起苦来。
“曹大人,你我跟随皇上多年,皇上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今年用我们这些老臣负责科考,这是对我等的信任,但南北二闱又各委派一位皇子,明着说是锻炼一下皇子,实际是让皇子们监视我们这些老臣,说到底,是皇上对我们的猜忌与不相信。北闱的情况我不太清楚,这南闱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让我老佟心寒。我虽然是主考官,实质上是分文家也不当,否则,怎会惹出今天的祸端来。如今事发了,又想把屎盆子往我老佟头上扣,真是有口难言呀!”
曹寅哈哈一笑,“有哪些难言之隐,慢慢说来,我会如实奏与皇上,圣上也是明白事理的人,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放过一个坏人的。哪怕是皇子,皇上也会秉公而论的。”
“好,曹侍卫是奉命调查南闱科场一案的,我就把事情经过说与你听,请曹大人评定一下,究竟是谁的错?我自奉命任主考以来就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坐卧不安,吃睡不宁,这是为国家挑才,岂能有丝毫差错?否则,上愧于君,下愧于民。可以说每做一件事都反复思忖,并与施世纶和八阿哥等人商量,不敢有丝毫懈怠。特别是来金陵之后,谢绝一切亲友往来,唯恐为了老关系而徇情枉法辜负了皇上的龙恩。就这样,从开考到批阅试卷排定名次,每一步都慎之又慎,始终以‘公平无私,选拔真才’八字作为行事准则,自认为对得起天地良心,无愧于皇上宠信和百姓所望。”
说到这里,佟国维长叹一声,老泪纵横:
“哪里知道老臣的一片苦心全部泡汤了!就在发榜那一天,老臣才从属下报告中得知施世纶与八阿哥瞒着佟某把我等事先排定的名次全部打乱了,他二人重新排定了名次。不错,那前十名是佟某亲手排定的,但也是反复审阅试卷并和他们两人一同商量后才定下来的。是我代笔,但代表我们三人的意见啊,如果他们二人有何不同见解应该当面向我说明不能这样做呀,我心中该是何滋味?为官多年马上都要进棺材了,还从来没受过如此窝囊气呢!曹大人可以去复查一下,我所排定的前十名试卷都在那里,如果其中有一份徇私情不够格的,我老佟愿搭上全家性命。相反,施世纶与八阿哥私自改动的名次则是名不副实,自从放榜之日就遭到举子非议责难,最终闹到考生不服,群起而上砸了贡院的牌子,把整个贡院闹腾得乌七八糟,几位考官差点被打,我老佟不是有两名随从抬走,如今只怕葬身黄泉了。可气可叹呀!”
曹寅见佟国维说得天花乱坠,丝毫也找不到一点破绽,心里遭:想从这样的老滑头那里找出他的不是那是比登天还难。只好假惺惺地说道:
“如此说来,真让佟大人受委屈了,我一定把佟中堂的委屈奏与皇上,但曹某想了解一下肇事的经过,请佟中堂详细讲一讲。”
佟国维立即委屈地说:“嗨,整个闹事经过我哪里知道!逃命还来不及呢,还有功夫管那么多?只是后来听说有一千多人,乱轰轰的,也不清谁是主谋者。”
“曹某听说抓住一个姓邬的书生及十几个领头的,有没有这回事呢?”
“抓住十几个人倒是真的,听说押在江南学政张长庚那里,有没有一个姓邬的我不清楚,我一直没来得及问起呢。至于这十几个人是不是主谋就难说了,这样的事是违反大清律例的,主谋者自然明白,怎会再直接参与闹事呢?我以为抓住的这些考生不过是科考落榜者,受人怂恿蛊惑罢了。”
曹寅知道在佟国维这里耽搁下去毫无意义,什么也得不到,便直接说道:
“佟大人,曹某想去见一见被抓的十几个考生,你愿不愿意与我一同去张长庚那里?”
佟国维哈哈一笑:“既然是曹侍卫相约,岂有不愿意之理?我也正想去见识一下这落榜者有哪些怨愤呢。”
张长庚接到吴文山的密报后,立即派人行动起来,先废去邬思道的双腿,然后派人送往夫子庙交给性音与文觉带走。
张长庚为了不引起怀疑,又从被抓的十几个人中挑选几个罪责轻微的释放几个,如今关押处仅剩下七八个人。
张长庚刚刚派人做好这几件事,就接到属下报告,说佟大人与曹大人前来拜访,张长庚立即把两人迎到府内。
三人分宾主坐定后,佟国维先开口说道:
“张大人,曹侍卫奉命来查访南闱科场案,他想见一见被抓的几个肇事者。”
张长庚会意,急忙说道:
“回曹大人,所抓的十几个肇事者经过审理都是被怂恿者,没有一个是主谋,虽然他们闹得较凶,但也没有犯下什么大的过错,我已经将几个罪责轻微的人给释放了,如今仅剩下几人,如果曹大人想见一见,那就请吧?”
“听说有个姓邬的举子是今科闹事的主谋,我想见他一人就可以,他如今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