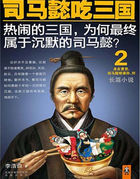1
那个大堡实在太奇怪了,像是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但并不生硬,因为有水,还有一个船坞,便有了抑扬顿挫的意味。天气晴朗时站在大堡脚下看船坞,看不见船坞,只看见半天云里长着一棵大树。是一棵柳树。长了千百年了,长得偌大的一座岩土堡子一片寂静。那树偶尔一阵摇动,四面八方都会起风。入夜,从那沧桑的树叶里吐出几星灯火,人们才知道那大树里边还藏着东西,仿佛从烟火人间中脱离出来,高深得像座庙。多少年了,那里边只住着一个孤老,姓方,方秋爹。
等我们这些小把戏能够爬到那个大堡上面去时,方秋爹的背已驼了。他驼着背时,比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高不了多少。他的那个船坞,格局不大,一间工棚,两间厢房,圈在一个土墙院子里。湖光山色,却数这里最好。除了那棵长了千百年的柳树,船坞后面还有一片桃花捧着。桃花杨柳,是江南水乡的魂。每年桃树着花的时候,就像一片紫色的祥云。桃花一开,柳絮便开始飞舞,白的红的,被风送过来,一朵一朵地绽开,落到方秋爹头上,美美地吸了他一头。方秋爹有点不知所措,不知所措地就老了,一半的头发都白了。又好像,是在他长久地凝望之后,猛一回头,这头发就白了。
他是在看那些船。他这样长久地看着时,那个驼背让人生出许多感动。这个大堡三面环水,是八渡溪、陆水河和黄盖湖的交汇处。大堡脚下,水极深,正好可以湾船。没有足够的深度,水不会这样冷。即便到了炎热的夏天,一滴水溅到你身上,你也会心里一凛。在一片水泽中凭空多了这个大堡,大约也是天地中的一种造化吧。每年的桃花汛一到,河里、溪里、湖里的水就噌噌往上涨。别的地方都沉在水里了,这个堡就成了唯一露出水面的陆地,也可以说是个岛了。那些船,无论你从哪一条水路上过来,想要走得多远,在进入长江,进入洞庭湖之前都要经过这里,又无论你从多远的地方来,赶到这里就一定是太阳落水的时刻。多少往来江湖的船只,从没有在另外的时刻到过这里。这让人感到神奇,感到冥冥中有一种东西在控制你。你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种力量。你没法不按这儿的规矩来行事。
太阳落水时,方秋爹便会把手上的活儿放下,驼着背走下大堡,濒水是一个小小的麻石码头,他就在这里候着那些船。这码头也是老方家的先人修的,也由老方家一辈辈地管着。所谓船坞,既是修船、造船的地方,也供往来船只停泊。大堡柳船坞是老方家的祖业,先有这个船坞,才有我们现在住着的这个大堡柳镇。老方家在此地算得一个奇怪的家族,虽代代都有传人,却是世代单传,一根血脉晃晃悠悠命若琴弦,似要断了却又终于未断。然而到方秋爹手上,是真的要断了,方秋爹是第八代传人,八,发啊,可不但没发,反而要绝代了。
这会儿,水里已经撒满了船,渡人的,打鱼的,拉货的,或直里行,或横里走,那些船的种类和名字千奇百怪,什么新墙小驳,洞庭风网,麻阳箱壳,还有倒把子,摇戟古,黄雀嘴儿,小迷腊子等,多得让人数不过来。方秋爹不用看,一听那船行时的划水声,就知道是什么船。我眼睛好使,方秋爹看不见的地方我也看得见,我看见一条船远远地划来了,却叫不出那条船的名字。我只能把这许多船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帆船,一种是机轮船。这江湖上跑着的,机轮船是一天天地多起来,它们来了,先听见一阵机器突突的转动声,再看见一团团烟雾似的东西,待到烟雾散尽,猛然发现,那船已经驶到眼皮底下了。
嗨,拿稳了!那机轮船上的水手牛皮哄哄的,从一丈开外凌空抛过来一只铁锚,四只锋利的铁角,拉得铁链子叮咣叮咣一阵响。方秋爹伸长身子把那铁锚在半空中抓住,那一刻他是一点也不显老,一点也不驼,他那跃向空中的样子敏捷而矫健,一跃,又劈开两条腿站住,稳稳的。那像野马一样的船刚才还翘蹄子撅屁股的,嘶嘶地喷着响鼻,眨眼间就被方秋爹勒住笼头了,乖乖的驯服地游到岸边来,又伸出一只跳板,像一只古怪的触角,探了探,就把岸抓紧了。从船上走下的,有挑担的,有背筐的,花眼柳条筐里装着从岳州捉来的小猪崽子,神魂颠倒一般地叫唤。还有些人,一只手牵着小娃儿,另一只手牵着三两只小白山羊,娃和羊都在叫,不知是羊在叫还是娃在叫,叫声难以分辨。这是大堡柳一天最热闹的时候,充满了世俗吵闹的快乐,大呼小叫的,脸都被飞溅的浪花沫子溅湿了,于是都兴奋地不停地擦。
很快,一条条船都空了,码头也空了。方秋爹还没走,拎着马灯在数那些船,一条一条地数,一直数到所有的船都睡了,他也打了个哈欠,突然看见了我。他空空地呵了一声,你这个野崽怎么还没走啊,你姓啥?
2
我也姓方。我爹突然动了心思,他搔了搔那葫芦瓢似的秃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儿子,咱们也姓方啊。
本地姓方的人家不少,可和世代单传的方秋爹八辈子也扯不到一块儿去。我爹是看上方秋爹的那个船坞了。我爹看到了,这镇上别的姓方的人家也早就看到了,也早就有人领着自家娃儿上堡子去认方秋爹做爹,做爷,可又全都被那个倔老头儿从大堡上撵下来了。我爹却不死心,在家里先喝下几杯酒壮了壮胆,又拎了一壶刚出锅的烧酒,领着我爬到堡子上来,见了方秋爹,爹拿一只手摁在我长满疖子的脑壳上,要我跪下,给方秋爹磕头。我不肯跪,爹就暗暗使劲,连疖子里的脓血都给我摁出来了。
我还没死呢,你们就给我下什么跪,磕什么头呢?
老头子朝我们瞪了瞪眼,又哼哼地踱进工棚,开始鼓捣那条船了,把个屁股对着我们,屁股瘦得像刀把似的往外突,把两块补丁顶得老高。我爹站在门外,醉眼蒙眬地盯着那老汉的屁股,喘着粗气儿。秋爹啊!我爹喊,一笔难写两个方字呢,五百年前咱也是一……一家呢。他一着急,语气带着结巴,给人一种分外悲凉的感觉。但方秋爹始终却把个屁股对着他。
后来我就跑了。我一跑,才给我万分尴尬的爹找了个台阶下。我跑到堡子脚下,回过头去看了一眼,看见我爹一边跌跌撞撞地往下走,一边对着壶嘴喝酒,那壶酒方秋爹不肯收,又被他拎回来了。他的脸喝得通红,走到我身边,喷出一股酒气,呛得我也咳嗽流泪。我爹骂骂咧咧,那个老绝户,他死了谁来埋他呢?孤老相啊。我爹咕嘟又喝下一口酒,用力睁开眼,不知看着一个什么东西。
但方秋爹还是把我收下了。那时已是冬天,落了一场大雪。我还是喜欢爬到堡子上去玩,那上面的雪比任何地方都白。这个季节船少了,几乎看不见船了,水已落到坝脚下很深的地方。方秋爹提着一桶水,从那里往上爬,看上去不是个人了,像是件被风刮得瑟瑟发抖的老棉袄。我想去帮他一把,突然又想到了些别的东西,心硬了硬,就假装没看见。风把那棵柳树吹得吱嘎吱嘎作响,除了这声音,整个大堡上没一点儿响动。这树的确是很老了。
老天啊!方秋爹忽然干号了一声,我知道出了乱子,想也没想就奔过去了,方秋爹从那道又陡又窄的石阶上滑了下去,一桶水全泼了,那只木水桶一路上发出沉闷空洞的声响,滚进了水里。方秋爹的一只手本能地朝上面伸着,拼命挣扎着想要抓住什么。他把我的手抓住了。慢慢地,我觉得他松了口气。
他又问我,你姓啥?他好像有点神志不清了。
姓方!我大声说。
方秋爹摸了摸我的脑袋,莫名其妙地笑了笑说,知道自己姓啥就好。
我听说,这个世界上最难相处的一是老姑娘,二是孤老。老姑娘性情怎样我不知道,方秋爹这个孤老可是让我吃尽了苦头。我十五岁跟他学徒,学了五年也没出师,后来是我自己跑掉的。
刚开始学徒,家里养成的坏习惯我还没有改掉,擤了泡鼻涕,随手捺在了刚裁出来的船板上,方秋天愣是逼着我给舔了。我不肯舔,他就强按住我的头,顶着我的下腭让我伸出舌尖,把那鼻涕舔得干干净净了,老家伙又拍着我的脑袋哈哈大笑,那模样丑陋极了。他说,你一定会记我的仇吧,要记你就记一辈子,一辈子别把脏东西弄到船上来了,船是啥啊,船是神器啊。
渐渐的,我也发现这造船不是简单的木匠活。一个木匠打张桌子放在地上不平,打个柜子门关不拢,人家骂你活儿糙,但毕竟不大碍事。造船那就不得了了,针鼻子大的缝儿都是天大的事,人命关天啊,稍微马虎一点就要背一身人命。一条船跟另一条船,外表上一看差不多,里边的东西却不一样,这造船,特别讲究里边的东西。方家世代造船,自然掌握了许多造船的秘密,一整条船造出来,不用一颗钉子。那船下水时,无论大小,都像是一整块木头雕成,头发丝大的缝儿也没有,被桐油刷得黄灿灿的,这样的一条船,父亲驾过一辈子了,儿子、孙子还可以接着驾。
那才是真正的船啊。方秋爹叹息一声,又把目光投向了那一片大泽。又是春天了,水天一色,空旷而清晰。方秋爹不知不觉就有些走神,一时神色悠远。
3
最后一条船,下水已整整二十年了。
那会儿方秋爹的背还没有驼。那会儿他还有个女人,给他煮饭,给他洗衣服。方秋爹和汉子们正在弄那条船时,女人就在给他洗衣服,不时有肥皂泡沫被她撩拨起来,搞得他心神有些迷乱。女人体态丰盈,一洗白乎乎的奶子一滚,那可真是个漂亮娘们儿。
方秋爹吃力地定了定神,和那船对视了片刻。船头两侧各雕着两只鲭鱼的眼睛,看上去有股狠劲儿。鲭鱼是这大泽里最凶猛的鱼,这双凶猛的鱼眼是老方家的徽记。只要是老方家造出的船就少不了这双大睁的眼,放浪于江湖上的人,见了这双眼,就知道,老方家的手艺还没瞎呢。
船就要下水了。每次放船下水,方秋爹总要和那双眼对视片刻。可这次,他一触着这双眼就浑身一颤,蓦地感到一种强烈不安。他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大声提醒那些伙计们小心,小心啊。果然,还没等伙计们把系船的缆绳完全解开,那船就猛地一挣,像挣断了缰绳的一匹烈马,按住了前头,尾巴又撅起,按住了后头,船首又昂起。十几个伙计,全都是血气方刚的汉子,一双双粗壮的汗毛浓密的手臂,都黑黝黝地发亮,使劲地抓住两边的船舷往回拖。方秋爹那时也年轻啊,他勒着半截缆绳喊着号子,不是不肯放它下水,是让它慢慢下水。可最终还是没把船拽回来,船往水里一扑,折腾起一个巨浪,把十几汉子全抛进水里了。
你……方秋爹冲那条船破口大喊。
只有他没被掀进水里,还劈开两条腿站在岸上,两只大脚丫子像长了吸盘,牢牢地吸住了船坞边的麻石。他还瞅着那条船,瞅着那片大泽。风把天空高高掀起,趁水而起的风,掠过浪尖,浪却平静。水一大就看不见浪了,满河满湖的水,莫名其妙地汹涌,苍穹下,那一望无际三水交汇的大泽,都漫到他的脚丫子边上来了,浪花咬着他的脚趾头,咬得他心里痒痒的,牙痒痒的。那船走得好快啊,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
他不知望了多久,回过头来时,就发现少了一样东西。女人呢?女人刚洗过衣服的那只脚盆还在,浮了一盆泡沫。女人给他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都晾在晒衣的竹篙上,却比平日少了一些鲜亮的颜色。那女人的衣服全不见了。那女人也不见了。他把那只大脚盆一掀,没看见泡沫里藏着个女人,就知道女人藏在哪里了。女人是什么时候上船的他不知道。但他明白那条船为什么走得那么快了,那船舱里藏着一个女人啊。
冬去春来,日子如风吹水流。他也慢慢想通了。女人拴不住,就像船。船一拴住,那就不是一条船了。船天生就野,就浪。不野,不浪,那船就像一只抛在滩上的旧鞋了。女人走了他不怪她,他和这女人一床被窝里滚了十年,女人是块好地啊。他却愣是啥也没种出来过。他还老揍她,揍她是为了自己那点儿男人的尊严,让别人都觉得,是那女人不行哩。他也很快就把那女人忘了,可他却忘不了那条船。那是条柏木的双桅船,镶着青枫木的舷。这辈子他不知造了多少船,记都记不清了。可他把这条船记得很牢。尽管他现在还在造,不停地造,他却固执地认为那是他这辈子造的最后一条船,甚至觉得,他这辈子其实就造了这样唯的一一条船。这之后他造的那些东西,哪是船啊,只是一些像船的东西。
我跟方秋爹学徒时,连这种像船的东西也很少造了,别的船坞,船越造越大,造铁驳船,机轮船,大堡柳船坞的船却越造越小,只造些小舢板和黄雀嘴儿了。辱没先人啊,方秋爹哀叹。他觉得这是辱没了老方家的手艺。造铁驳船机轮船他又没那技术,没那设备。他好像也从来没想过要造那些铁家伙。铁和水是相克之物,遇水即沉,又极容易生锈,一条铁驳划不了几年,就烂得跟筛子似的了,修都没法修。最好的船,还是上等木材打出来的船,这是由木头的本性使然,凡是树木皆由水土滋养而成,天生就能浮在水里,水养船,船养水。他还让我长久地看那棵大柳树,说是让我养眼。我就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那棵树看。那树丝毫没有察觉有一个傻小子这样长久地盯着它,只管用心地苍绿着,阳光从一片树叶移到另一片树叶。看树看久了,看太阳也是绿的,看天空也是绿的,看方秋爹也是绿的。我眼里已经有一种发绿的东西。
方秋爹说,好。你眼里有了这片绿意,就可以造船了,你造出来的船才是活的。他弄了些边角余料来,让我造一条船,尺把长的一条船。这么小的一条船,我用了半年时间才造出来。方秋爹问,造好了?我说好了。方秋爹眯着眼瞅了一会儿,没看见缝儿。他又把船拿起来,对着阳光看,也没看见缝儿。我正暗自得意,方秋爹用手指在船上弹了一下,发出一阵轻微的铮铮之声。他支棱起耳朵贴着船舷听,一听就知道哪里还有缝儿,很快就奇迹般地找到哪里还有缝儿。他毫无表情地说,不行,这船到处都是缝儿,你再造一条。
我又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造了一条尺五长的双桅船。从半年到一年,慢了,造船不嫌慢,越慢就越说明你的手艺有长进。你得把所有的念头都压抑下去了,才会体味到那种缓慢而坚实的质感,就像树木本身的生长过程。这一条船,方秋爹摸了又看,看了又听,然后他轻轻地笑了起来。找是找不出一点缝儿了,他说,可还得让别的眼睛看看呢。
谁?我疑惑地问。我想,还会有谁比方秋爹的眼睛毒呢。
方秋爹慢吞吞地吐出一个字,天。
他诡谲地眨了眨眼,立刻就让我觉得,那个神秘的天,比人类掌握的秘密更深一层。他让我把船搬到外面的太阳底下去,让天看看。老天爷也长着眼睛呢!他又得意洋洋地喊了声,就蹲在那里,一边悠闲地抽烟,一边幸灾乐祸地等着我的船露出破绽。没过多久,我那船就到处都是缝隙了,惨不忍睹,我都不敢去看了。他嘿嘿地干笑了几声,又把笑容收敛了,说,你现在知道造一条船有多难了吧?你脑子不笨,可这造船啊,心比脑子重要,心里要有血!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心,它在我的手心里怦怦直跳。
我知道方秋爹为什么总是放不下那条船了,那条真正的船,倾注了他一身的全部心血。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打听那条船的下落。他问别的船,看没看见那条船。一问,别的船里就会有人像虫子一样伸出脑袋来,然后使劲地摇着他们的头。他喝醉了酒,也会问我,问我那条船走到哪里去了。十六岁的我,这时候就会傻乎乎地想,二十多年了,一条船能够走多远?怕是早就划到世界外面去了吧。
方秋爹最担心的还是那条船会沉,那是条好船,可性子太急了。一条船就算真的没有一丝缝儿了,还不能下水,还得经受日晒夜露风吹雨打,让日头晒透了,风吹透了,水浸透了,用桐油反反复复地刷过了,这船才能下水。可那条船太性急,偏偏就少喝了一些水。船和人一样,在岸上干久了也会渴,得在岸上慢慢地让它饮饱了,再慢慢地把它放了。它那么突然往水里一扑,浑身就像着了火似的,再好的船板也会炸啊。老头儿每次想到这里就抡着那船挣断了的小半截缆绳拼命抽打自己。要等血流出来,血一流出来他就清醒了。
我就是这样打她的!他笑着说。
我已经十八岁了,人世间的事多少懂了一点。老家伙放不下的还是那个女人啊。他羞于提及那个女人,是因为毕竟那是件丢人的事。他那点可怜的尊严不允许他打听那个女人。每次他都只打听那条船的音讯,找到了那条船,自然就找到那个女人了。
4
一天傍晚,我竟然奇迹般地看到了一条白帆船。那一页白帆,洗得极干净,白云似的,闻起来都是白的气味。哪怕只有一叶白帆升起,这一片大泽顿时得到了和谐升华。看见它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明亮了。我赶紧拉了拉站在身边的老头儿,我说,你看!
我连眼睛也不敢眨,怕眨眼就看不见它了。
老头儿努力地伸直他的驼背,仰起脸很信任地看着我,问,什么?
我知道那一叶白帆离得还太远了,他现在还看不见。我告诉他,是一条双桅的白帆船。老头儿很激动,但又很害怕,犹犹豫豫地问,你看见那双鲭鱼的眼睛么?我摇头。我真的没有看见船头两侧那双鲭鱼的眼睛。噢?老头儿竟然奇怪地松了一口气。
那条船走得格外慢,就像在遥远的天尽头轻轻移动,又像是根本没动,幽深而神秘,像是影子,极梦幻的神情。这时别的船已陆续靠岸了。码头上热闹了一阵,热闹完了,方秋爹也上了堡子。我还站在那里看。那船终于划过来了,我已经看得见那个驾船人清晰的身影了。划一下,桨便亮一下,静悄悄的,像在静静地挑明一些东西。我一直看到桨叶子上拨起了夜雾,水与岸都难以分辨了,那船还没靠岸。离码头近了,那船反倒有点畏缩。
吃完夜饭,我又出来看了一次。夜黑得更加深刻了,不见星月。我摸黑在通向码头的石阶上走了许久,前边有了隐约的亮光。那是水。这微弱的光芒在如此漆黑的夜里更让人心里发虚。不知怎么的,我没提马灯下来。那个夜晚我的心情有点复杂,我突然很怕看见某样东西。借着水面微弱的光芒,我把所有的船挨着数了一遍,还是没有看见那条白帆船。我又茫然地向夜幕深处搜寻了一遍,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竟对自己的眼睛发生了深刻的怀疑,或许根本就没有那条什么白帆船。
那晚的天气热得要命,我回来时方秋爹还打着赤膊在喝酒。那根弯弯曲曲的脊梁骨,尖锐地赤裸着,令人心尖儿发颤。他没问起那条船,他问我外面下雨没有。我说没下,怕是要下了。他说怎么听见雨在响?我走到门外一看,果然是在下雨,很大很稀疏的雨点。
你以为我耳朵聋了啊?老头儿撅起山羊胡子来看我,那样子得意得不得了。他要我过去,把脑壳低下,低得他能够着了,一把揪住了我的耳朵,我哎呀哎呀地叫唤起来。
我就是这样揪她的!老头儿那手简直像猛兽的爪子,揪着我的耳朵来回拖。蠢婆娘。他骂了一声,泪水便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一颗眼泪溅在了我的手臂上。我用鼻子嗅了嗅手臂,深深地吸了一口它的气味。不知是什么气味。
半夜里风雨大作,还在打雷,电扯得忽闪忽闪。但我并不是被这些东西惊醒的。我听见有人在拍门。睡觉之前,我像平时一样用木杠把门顶住了,从外面是很难推开的,但外面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费劲地推着,勉强被推开了一条缝隙,又啪的一声弹了回去。也就在门咧开的一刹那间,我看到了一张被狂风吹得奇形怪状的脸,显得狰狞可怖。我吓坏了,喊睡在另一张床上的方秋爹,他像是真的聋了,没一点儿反应。我下了床,趿着鞋子扑过去,想要把他推醒,一摸,那床却是空的,枕头被子乱作一团,像是狗窝。
师父,师父!我更加惊恐万状地叫起来。
门角落的阴影里传来一声低沉的吼叫,住嘴,莫乱喊。我赶紧把嘴闭了。短暂的寂静中,又听见一个女人微弱的哀求声,船快沉了,你去救救他吧……
方秋爹深吸一口气,把那木杠猛地抽开了,一道闪电照亮了他佝偻着的身体,他仍打着赤膊,酷似一尊深暗的乌木雕像。我牙齿打着战,迎面扑来的风雨使我看不清在前面带路的那个女人,闪电消失之后,我看见方秋爹手里拎着的斧头在黑暗中静静地发着光。
我又看见那条白帆船了,那帆早已降下。它没停在码头上,停在离码头一里多远的龙王庙。洪水陡涨,龙王庙已经被水淹了一半了。连我都知道,一船建龙王庙的地方,都是江湖险滩,最容易出事的地方,这才想要龙王镇一镇。可现在,就连龙王本人也无奈地站在齐脖深的水中了。那船已经翻了一半,一个老汉在狂风暴雨中使劲地抓着船,水浪像恶狗一样狂吠着,不断朝他扑来……
方秋爹一斧头下去,把老汉紧拽着的锚链劈断了,那船不顾一切地撞开一个大浪,径自冲了出去。那船跑了。老汉像是疯了,老汉往水里一扑嗷嗷地嘶吼着去追他的船。
你把老子的船眼都给剜了!
方秋爹又骂了一句,一锚链甩出去,像套马一样,把那老汉手拖到岸边上来了。
老汉像死狗一样趴着不动了,恐怖地睁大了眼,看着方秋爹手里的斧头。——我一斧!方秋爹在老汉的头上比划了一下,我心里蓦地一寒,可斧头并未落下。方秋爹收了斧头,冲那老汉吼了一声,你还趴在这里干啥?你要不想死,先去我那里喝口酒,暖暖身子骨吧。那老汉翻了翻眼白,仍趴着不动。方秋爹便不再理他,转身对我说,让他死在这里吧,走,咱们回去。
我担心地问,那船……
那船自己会回来的!方秋爹十分肯定地说。
真是神啦!第二天早晨,那船还真的自己回来了。雨过天晴,白茫茫的水面上现出一条船影,一路向码头这边奔来。方秋爹也早已奔下码头,去迎接那条船。他抱住船头,使劲地搂啊,亲啊,船头那一对被剜掉了的鲭鱼眼,又像是活了,对着他直眨呢。老头儿爬到船上去,往那高昂的船头上一站,连脊梁骨也挺起来了。
人其实还不如一条船啊。船回来了,那个和他一床被窝里滚了十年来的女人,却愣是不肯回到这家里来。她和那老汉,就住在水退下去后的龙王庙里。方秋爹让我给他们送饭去。那老汉背靠着龙王的一双大脚,浑身上下邋遢死了,活像个流浪汉,从他阴郁的目光里,看不出对人的任何友善,更不说感激了。方秋爹还特意吩咐我去镇上买来了卤猪蹄,打了酒,他却把这一大堆吃的喝的推到了一边。那个女人也头发花白了,像哄孩子一样地哄着他,哄他吃点东西。老汉依旧紧闭着嘴,后来干脆连眼睛也闭上了。
我在鼻孔里哼一声,扭头走了,走到门口又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那老汉满嘴塞得鼓鼓的,那丐婆似的女人手里抓着一个猪蹄,正在张牙猛咬。他们都没发现我在偷窥他们,两个人互相打量着,像两头分享猎物的野兽满含深情地相互凝望着。
我没把这一幕告诉方秋爹,我感到我的心事更复杂了。
方秋爹差不多花了半个月时间,把那条船修好了。那船放浪于江湖二十多年,浑身充满了历尽奇险的气息。但大的毛病没有,龙骨、船舷都还结实,就像方秋爹早就预料的那样,它下水太急了,炸开了一丝丝小小的裂缝,时间长了,就有些渗水。方秋爹把那缝儿一条条摸拢了,刨去船上的死皮,新刷了一层桐油,又把那双鲭鱼眼睛刻画分明。那船昂着头,又是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了。
在龙王庙里住了半个来月的老汉,屁股上已长出了一层青苔,像只熊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步地走过来了。多少钱?他看看船,又看看方秋爹。方秋爹说,算了吧,穷家富路,你们也不容易。老汉木头木脑地上了船,那女人还在方秋爹跟前站了站,她指着我问,这是你儿子?
方秋爹不动声色地说,是啊,你儿子也有这样大了吧?
那女人哆嗦了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
船上的老汉又把白帆扯起来了,又是那样一副傲慢的神态了。他喊了一声,走!女人就赶紧爬到了船上,船头朝方秋爹点了点,就慢慢地朝着另一个方向了。那老汉,那女人,那船,此时都背对着方秋爹了。
你可别再把那双眼剜了,这船也不能没长眼睛哪!方秋爹喊了一嗓,咬着牙,鼓着腮帮子,似强忍着什么。
5
那船走后不久,我也走了,跟一个陌生人进了城。
我跟方秋爹学了五年造船,最后也没造出一条可以下水的船。我造的那些小玩意儿,一共有几十条,什么新墙小驳,洞庭风网,麻阳箱壳,还有倒把子,摇戟古,黄雀嘴儿,小迷腊子,这些家伙,只要是我见过的我都已一一会造,只不过,我造的都是一个个缩小了的船的化身,小得像童稚未脱的玩具,又小出一脸的奸诈。这些船一溜儿排开,就像一个小小的船队,最后那条就是我照着那条双桅的白帆船刚造出来的,白帆是一样的白,船板是一样的被桐油浸得油光光的。方秋爹看了也挺高兴,方秋爹说,一个人打出了第一条船,那后边的船,就像这条船陆续生下来的儿子,你看像不像,儿子?
他叫我儿子。自从他跟那个女人撒谎,说我是他儿子后,他就一口一声地叫我儿子了。但我却不肯叫他爹。
老头儿的意思我明白,只等我打出一条真正意义上的船,我就可以出师了。我和他都在苦苦等待,等待一条即将由我来制造的船,但却苦等不至。没一个人上大堡来找我们造船了,连摇戟古、黄雀嘴儿、小迷腊子那样的船也没人找我们造了。老头儿一天到晚喝酒,我不分白天黑夜地睡觉。闲得最无聊的时候,我竟然用墨线在手腕上画了一只手表。时间仿佛凝固了。
挨到秋天,岳州城里一家宾馆来了一个人。他带来了一张图纸,那上面画着一条奇形怪状的外国船。他问方秋爹,这船会造吗?方秋爹把那些图纸翻过去一次,翻过来一次,差不多都翻烂了,才一脸疑惑地问,这是船吗?下得水?跑得江湖?来人笑道,不一定要下水的,我们要把这船停在宾馆门口,只要好看就成,惹眼就成。方秋爹也笑了,你这不是造船呢,你是要我给你打个幌子呢。来人说,就是。方秋爹说,不造。来人说钱的事好商量。方秋爹说,不造!声调里含着怒意。
那人悻悻地要走时,忽然看见我造的那些玩意儿了。他一条一条地挨着看过来,看得很仔细,我看不见他的表情,只看见他带点笑意的半边脸。他转过身来时,嘴唇动了动,吐出一个字,好!
我兴奋得满脸是汗。
我就是跟在这人屁股后面走进城市的,凭着我师父方秋爹瞧不上眼的那点手艺,我居然在城里打出了一片天地。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一代人,现在我已在城里娶妻生子,还被人封了个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城里那些工艺品商店、大小宾馆、旅游公司以及许许多多的体面人家里,都摆放着我制造出来的那些船,谁也没说它不是船。但我从不敢在这样的船头上刻上一双鲭鱼的眼睛,也不敢妄称我是老方家的传人。
不久前我回了一趟大堡柳。
黄盖湖,那片天生地长的水泽,现在已被人们把水拦起来了,变成了一个人工水库。溪水,河水,湖水被隔开了,而且越隔越开,水小了,地大了,连片的水域变成了连片的土地。那个古老的大堡,一大半身子已被撂在陆地上,只剩下一个脑袋,还挣扎一般地向水里伸着,像一条快干死的鱼,想找口水喝。这里已经不能湾船了。水死了。水里一没有了船,就死了。原来湾船的地方漂浮一些翻着肚皮的死鱼。那股气味死死地停留在我的鼻腔里。开始我还感到惊慌,当死亡的气息开始从每一个角落里弥漫出来时,我反而嗅不到了。
那棵柳树还很古老地长在那里,痛苦地支着身子,一根根多杈的树枝刺向天空。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声地震,那个老船坞已被半埋在疯长的野草里,几扇破旧的窗户用旧木板钉了起来,门开着,被风吱呀吱呀地推来推去。我喊了几声师父,没听见方秋爹答应。走到方秋爹常常站着凝望过往船只的地方,那里也是荒芜一片了。一阵风吹来,在拂开的草丛中,忽然升起了一叶小小的白帆。我急忙飞奔过去,原来是一块雕琢成帆形的白色墓碑,没有铭文,只有水的波纹,在一片神秘的光泽下粼粼地闪烁着,恍然真的是一片跳动的水泽。我慢慢地跪下了,把脸伏在那冰凉的墓碑上。
一只手从后面伸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我回过头去一看,眼睛惊得都快裂开了。我想我是看见鬼了。方秋爹站在我身后,像个孩子似的顽皮地做了个鬼脸,我还没死呢,你就给我下什么跪,磕什么头呢?我哆哆嗦嗦的,叫了一声师父。
你姓啥?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
这老头儿,这老头儿,他竟然没死,他怕自己死了没个人埋,或是要把他埋到别处去,就先给自己造了一座墓,立了一座碑。看样子老头儿一年两年是不会死的,还挺健壮。水边上的人很容易老,但老到一定的程度就特别难老了,像一块顽石,抗磨,抗折腾。老头儿已经活了九十多岁了,牙掉光了,又长出了满口新牙,吃得豌豆,啃得骨头。人也变得像个小孩样了,我跟他说话时,他竟然把两条腿端到了自己的肩膀上,那么天真可爱的晃呀,悠呀,还伸手去摸自己通红的脚丫子,几乎就是一个刚出娘胎的婴孩呀。一个人活到老年,又能活转来,又能像一个孩子那样天真烂漫地生活,那该多幸福啊。只是那背驼得更厉害了。
我看着他的驼背时,老头儿出了个谜语给我猜:远看寻东寻西,近看打躬作揖,仰倒龙船下水,扑倒乌龟晒背。他像三五岁的孩子那样天真地考我,你猜是个啥玩意儿?我知道他是在顽皮,就故意说,这还不容易,是船啊。老头儿笑得向后一仰,身子弯得像个只剩了一半的圆球似的前后翻滚了一阵,又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个笨熊,连这都猜不出,就是我啊,驼背啊!他摸着自己的驼背哈哈大笑,我也笑,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好笑,又很悲惨。真的是这样,只要你想一下。
老头儿又开始打船。没人请他打,是他自己要打。打着玩儿呢。他拆了自己的床铺,却没砍那棵柳树。他其实一点也不糊涂。我走了,走得很远了,到了大堡脚下,还听见那叮当叮当的声音。日子便显得格外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