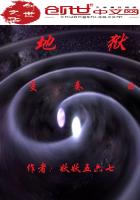蜿蜒着的羊山路,在山崖和竹林深处便到了尽头,于是便有一间人字小屋倾斜在那里。不知有多少年了,那屋顶上的茅草一层层地灰去,又一层层地加厚,终于,那最后一层屋草也早就发出灰褐的泥土色,与那崖壁浑然一体。哑舅也终于老了。
谁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村里人无论老少无论男女都一律叫他“哑舅”;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是谁家的舅,大家都只这样叫他,叫了半个多世纪了,哑舅,成了村里人最熟悉的称呼。
只知道他原来是给东家放牛,最早,他是一个野孩子。村里烧窑,一遍又一遍地塌窑,后来他被选作童男子去祭那窑神。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一神圣的当选。当人们将他穿戴一新,高高地举起迎向那炽烈的窑火的时候,他忽然大叫一声:“妈妈——”那撕肝裂胆的叫喊首先惊动了在一旁看热闹的东家,东家说,野孩子也是有娘的,饶了他吧。就这样,他到了东家。
东家对他不错,他也感激东家。1951年当人们将东家押赴刑场时,半路上他突然抢把快锹劫了法场。直到人们将他五花大绑捆了半个多月,伟大的土地革命才得以完成。那一年秋收时节,他照样在东家的地里收割,将一担担金黄的谷子挑到东家的院里,东家的老太太被他这一行动吓得半死。人家告诉他,这地现在不是东家的了,这土地现在是“集体”的,其中也有你的一份你明白了没有?他不明白!他不知道为什么东家的地会变成集体的,再说,“集体”又是怎么一回事?
哑舅在昏懵的岁月中不知过了多少个轮回,那一年,村里人开始丈量土地,他知道,那“集体”没有了,这土地又将归于个人。他搓了根长长的绳子。连夜将原先东家的地一块不拉地圈了起来,他说,这原先都是东家的,有一百年了吧,你们不记得,可我记得。
他在那山崖和竹林深处的人字小屋里记不清日月,记不清世事的变迁,他只记着东家的好处,记着东家将他从窑火中救了出来,他没有报东家的恩,他的心,得向着东家。
人家又告诉他,这土地将有你的一份,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明白了吧?他不明白!他只知道自己原先是个野孩子,他原先并没有地。他终于放弃了他对这复杂世事的苦思冥想,放弃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土地,再回到他的人字小屋,过他的山野独居的生活。
哑舅的手很巧,他砍下竹子,编出一只只斗笠、一只只竹篮、一只只小巧而结实的背篓,他将他的这些东西送给村里人,于是人家给他一碗米,给他一碗饭,也有人会按价给他差不多的钱物。他永远也无法估算出他的产品与应得的价钱之间的关系。人家给什么他要什么,人家给多少他要多少。他将钱随便地塞在屋檐下,床席里竹筒里,他不知道那些钱的大小和用处,于是,那些钱最终又落到放牛孩子的口袋或是被进山打柴的人随手拿走。拿走就拿走吧,反正这些钱在他也派不上多少用处。
在他的人字小屋里,任何一个孩子都能成为他欢乐的伴侣。他让孩子坐在牛背上,他牵着牛,在山坡上慢慢地散步,春天的阳光真暖和啊,如果哑舅有听觉,他该听到牛啃着青草的“嚓、嚓”的声音,那声音清脆而细密,与那周围的鸟鸣雀语组成一曲美妙的音乐,于是他不时回过头来,给孩子诉说着什么。他说得很动情,时而发出一两声短促的笑声。他确信孩子懂得他的絮语,当他快乐而冲动的时候,他将孩子从牛背上抱下,用自己满脸的胡髭去扎孩子的小脸,直扎得孩子“嗷嗷”叫唤,并且用小拳头揍他的脑袋时,他才将孩子放开,爬上崖去,给孩子采一把金银花,为孩子编一个秀巧的花篮。
一般说来,村里人通常想不到他,而当春耕或者秋收,当谁家劳力缺乏的时候,人们会唤自家的孩子:“去,叫哑舅来帮一天忙!”孩子就去了,也只有孩子能请得动他。哑舅不惜力,就像他使唤的那条蛮牛一样。做完活,哑舅再回到他的人字小屋歇息。当好多年过后,哑舅将一串串长短不一的草棍扔到谁家门口时,人们这才发觉,哑舅并不糊涂,这些草棍,记录着他帮工的天数,长的是一整天,短的是半天。人就笑着说:“你这个死哑巴,你也不真哑嘛!你记着有什么用?你要工钱吗?”于是人将那一串草棍在笑声中扔进了灶门,哑舅的脸上便露出短暂的怒色,然后他继续给你蛮牛样干活,直干到落日归去。
忽然有一阵哑舅没出那林子了,村里人说,该不是哑舅出什么意外了?人又说,哑舅也够老的了,再不能让他苦做了,我们该养着他才对。终于都想,哑舅够老了,于是商议出“五保”的措施。等到那孩子将这条喜讯报到人字小屋时,人字小屋内却只有一条黑疙瘩样的棉被和一眼冷却的土灶。孩子四处去寻,终不见哑舅的身影。
以后的好多天里,好多的人在好多处寻找,仍不见哑舅身影,人们才知道,羊山缺少点什么。孩子哭起来,唤:“哑舅,你在哪里?”女人也哭,说:“哑舅,我们该早就请你到村里去的……”
不久,人们就忘了羊山顶上那条蜿蜒的山路,以及那路的尽处曾有一个人字小屋,又过了很久,孩子也忘了那扎人的胡髭,大家都过自己的日月去了。
198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