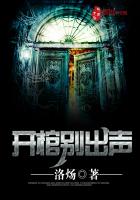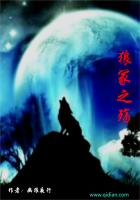那是一个春天即将来临的夜晚,我乘坐着一辆充满汗臭与膻臊的长途客车,从格尔木开始了我的高原之旅。车窗外的风雪淹没了所有的风景,窗外世界混沌一片,想像中的奇峰与荒漠都是一望无际的风雪。
车上的乘客除了到高原某个地方淘金的砂娃们之外便是要去守卫某个山口的军人们。这是两种境界的人生,两种境界的人生同一辆车同走一条道。当然还有一些浪迹高原的其他人等。在这个寂寞漫漫的夜晚开始的时候,他们怡然自得谈笑风生。他们以高原人自居,显然他们已经溶入高原了。车上有一个女人,一个不知是北方平原或南方水国生长的女人,也是从格尔木开始了她的高原之旅。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方才知道,她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就在高原上的某个地方。她领着的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她必须翻越唐古拉山口方能见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她没有犹豫,即使听说要翻越唐古拉山她也没有犹豫。或许是她压根就没有想到唐古拉山的高度的意义,她只是一遍遍地念叨着路途的遥远。
终于要过唐古拉山口了,一过唐古拉山她就可以看见她的丈夫,那两个孩子就要见到父亲。她听说快到唐古拉山口了,她就有些激动,不停地向窗外张望,尽管窗外是混沌一片。
窗外的混沌让她有短暂的失望,短暂的失望让她逐渐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她突然发现:那个5岁的孩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休克了。
女人惊慌失措,大喊,大叫,大哭。同车的人随着女人的大喊、大叫、大哭而紧张、无助,继而因无能为力而麻木。
女人的大喊大叫大哭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也没有能唤醒自己5岁的孩子。失望的女人能做的只有紧紧地怀抱着已经休克的小孩。唐古拉山之路漫长地在升高。那个休克的孩子身体开始发凉。几个常走青藏线的男人开始劝她,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孩子是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她,这里死个人是瞬间的事,死的人也太多了。有人已经让司机停下车,说就把孩子埋葬在唐古拉山上,免得她见了丈夫又是一场大悲大痛。
那个女人不再喊叫,只是紧紧地怀抱着冰凉的孩子不动。她没有了眼泪,她对车上好心的人们说,孩子是无论如何要见爸爸一面的,这孩子打生下来也没见过爸爸一面。车上的男人们全哭了,那个女人依然没有哭。
汽车翻过唐古拉山口很远的时候,这个女人感到怀中一般温热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她突然感到恐惧起来。她张望一下周围的人,个个昏昏欲睡。她怀疑自己是在梦中,她对那温热越发感到惧怕,她猛然站起身来,两手不由自主松开了,从怀中掉下来的孩子却“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孩子的哭泣使她彻底从梦中惊醒,她真真切切地听见那是自己非常熟悉的哭声。“我的孩子回来了1她突然大喊一声,发疯般地抱住孩子,泪水哗哗地流下来。
车上的人们被眼前发生的景象惊呆了,只有疑虑的目光在车厢中穿梭着,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汽车疲惫地在高原上继续爬行着,车上鼾声渐起……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位置,即有些人所说的人生坐标。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谁就取得了获得成功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