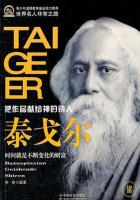王守仁刚到梧州,便立即开府治事。不久,他将田州之乱的真相和自己的平乱措施疏奏朝廷,皇帝下诏,褒扬“守仁才略素优,所议必自己见”,准许他便宜行事。嘉精7年(1528年)二月,王守仁采用招抚方式平息了思恩、田州首长卢苏、王受之乱,安抚其众7万余人。然后,他兴建了思田学校、南宁学校,推行社会教化,加强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七月,王守仁本可班师回朝,但他被效忠朝廷的“良知”驱动,认为八寨、断藤峡两地长期未能镇压下去的僮囗族起义军是一大祸患,于是不待诏命,自动移师广西一举剿灭,残酷屠杀了无辜百姓15000余人,再次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十月,王守仁因咳痢之疾(肺痨)日益加剧,过了片刻工夫,他便瞑目而逝。嘉靖八年(1529年)正月,丧发南昌。门人钱德洪、王畿西渡钱塘,迎丧至严滩。随即讣告同门,阳明弟子相继前往奔丧。二月四日至越,“子弟门人莫枢中堂,遂饰丧纪,妇人哭门内,孝子正宪携弟正忆与亲族子弟哭门外,门人哭幕外,朝夕设奠如仪。每日门人来吊者百余人,有自初丧至卒葬不归者”。其后,王守仁遗体被安葬在山阴兰亭山(见《余姚县志》卷15)。会葬之日,门人至者1000有余,人人麻衣衰履,扶枢而哭。四方前来观葬的人不计其数,一个个亦无不涕泪交流。
王守仁去世之后,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桂萼奏其擅离职守,处理思、田、八寨之乱恩威倒置,又低其擒濠军功冒滥,谤其“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明世宗偏听偏信,乃下诏停止守仁世袭,不行赠谥诸典,并严禁阳明“伪学”。38年之后,即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明穆宗诏赠王守仁新建侯,谥文成。再至万历十二年(1584年),明神宗又下诏以王守仁从祀孔庙。由此,王守仁就成为明代官方推崇的“内圣外王”的典型,阳明心学也就成为明朝后期思想统治的工具。
“心即理”说
王守仁的学说世称“心学”,并与陆九洲的学说合称为“陆王心学”,这是同程朱理学分营对垒的一种新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把抽象的“理”(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即物穷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陆王心学则将主观的“心”(人的意志和道德观念)视作宇宙万物的本原,主张“发明本心”、“致良知”,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范畴。王守仁集来明心学之大成,他在全面继承和批判儒家人性论的基础上,着重对孟子“尽心”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创建了以注重内心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色的新儒学--阳明心学,从而达到理学发展的高峰。在阳明心学体系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是三个最为重要的论题,由此也形成了王守仁独到的教育思想,下面予以分述。
心即理“心即理”是王守仁心学的逻辑起点,是其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是他的宇宙观。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产生了很大分歧。程颐认为“须是遍求”事物,方可“达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朱熹继承程氏学说,提出了“即物穷理”的主张。而陆九渊则认为“理”不寓于外物,而存在于人的心里,“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象山全集》卷11《与李宰书》)。不过,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主观唯心主义方面还不够彻底,对“心”与“理”的关系问题还存在并列倾向和把“心”客观化的痕迹。而王守仁则克服这个缺陷,发展了陆氏“心即理”这一命题,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于“格物”,而在于“致知”,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答顾东桥书》)。王守仁公开宣称:“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象山文集序》)。他以“心即理”作为“立言宗旨”,否定了朱熹分裂“心”与“理”为二的理论;以“求理于吾心”作为“致知”途径,否定了朱熹“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的观点;又以“心之本体”说扩充了“心”的内涵,修正了陆九渊的“本心”说。这样,便形成较为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王守仁认定:吾心便是天理,便是世界的本体,它既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又是事物变化的归宿。因此,天地间诸事万物,举凡纲常伦理、言行举止,成败荣辱等等,无一不是根于吾心而森然毕具。所以,他反复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与王纯甫(二)》),“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答顾东桥书》),提倡求“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王守仁“心即理”之说,是其“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它充分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相信自我的道德力量和自我成圣潜在能力,反对迷信外在权威,否定用现成规范和书本教条来禁锢人的身心,而主张依靠自我的“心之本体”(良知)来主宰和支配一切行为,在道德实践中努力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然而,王守仁的“心即理”之说,把人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等同起来,断然否定了有离开心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王守仁所谓“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把人类认识的能动作用片面夸大和过分神化,以致用吾心之主观精神吞并了客观存在之物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批判的。
知行合一
“知行”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曾为历代哲学家所关注和探讨。从先秦《左传·昭公十年》的“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道家的“不行而知”,到宋代程、朱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乃是“知行”范畴发展的重要阶段。
“知行合一”论是阳明学说的核心,是其理论体系的主体结构,所以王守仁自始至终以此作为“立教宗旨”。这种“知行观”只是把认识问题局限在伦理道德的范畴上,主要是揭橥道德修养层面的认识与实践问题,其价值取向则是道德实践的实际作用。因此,它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实学精神,具有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倾向和人本主义意义。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以“心即理”之说作为理论基础的。他在《答顾东桥书》中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王守仁认为,“知行”问题与“心理”关系紧相联结,朱熹学说之失就在于分“心”与“理”为二,因而导致分“知”、“行”为二。他一反朱熹“外心以求理”之说,主张“求理于吾心”,大力倡导“知行合一”。
王守仁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论,主要是因时而发。明代中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贪官污吏肆意横行,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严重威胁着封建政权的稳固,有力冲击了封建王朝的伦理纲常,大大加深了明代潜伏已久的社会危机。由此,王守仁痛感:“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而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答储柴墟(二)》)于是,他以治天下之病的“医国手”自诩,几经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一个自以为救治此病的“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在王守仁看来,人们想的与其做的基本上是相合的,如果彻底去掉人们对于封建伦理经常的违戾意识,就不会发生违反和破坏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如果分“知”、“行”为二,其危害甚大。所以他曾明确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着重从“知行”的同一性方面较为深入地进行了探讨,认识到“知行并进”,“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自信这种“知行合一”论,既可纠正程、朱“知先行后”之偏,又可补救世人“知而不行”之弊。平心而论,王守仁关于“知行合一”的主张,确实比前人有所进步。首先,他将“吾心之良知”作为“知”,将“致吾心良知干事事物物”作为“行”,而以“心即理”为前提,以“知行合一”为指归,从而达到体认良知的目的。这种认识论,就其解剖自身(吾心固有的“良知”)以推求万事万物之理的认识方法来看,内中蕴含有“一般(事事物物)存在于个别(吾心良知)之中”的辩证因素。由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便以其发展了主观能动的一面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高度,为宋明理学增进了一个新的范畴,为认识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对于后世唯物论知行观的建立,显然起到了触媒的作用。其次,王守仁反对朱熹以“知先行后”说割裂了“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开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极力强调认识过程中“知”、“行”两个阶段之间的统一与联系,这是王氏高于朱氏之处,是他对于认识论的新贡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它片面夸大了“知”和“行”之间的统一性,而抹煞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并将其歪曲成绝对的同一,从而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等同于纯粹主观先验的“知”,由此否定了“行”的客观性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致良知”论,是王守仁关于认识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他对于“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心学命题的理论概括与升华。王守仁称此为“孔门正法眼藏”,是“千古圣圣相传的一点真骨血”。他曾自我标榜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他从37岁龙场“大悟”到50岁始揭“致良知”之教,其间经过了十几年学术研究和事功磨炼的艰难历程。“致良知”命题的提出,代表了阳明心学的终结,标志着阳明心学的发展达到了它的顶峰。
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是将《大学》的“致知”与孟子的“良知”说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发明而产生的。《大学》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圣”,强调“格物”是身心修养的首要环节。王守仁对此进行了改造,认定“格物”就是“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答罗整庵少宰书》),因而“致知”也就在于“格心”。《孟子》所谓“良知”,主要是指先天固有而不经后天习得的善性,即天赋的道德意识。王守仁就此作了很大的发挥,认定“良知”为心之本体,能生天地、万物和人类;它“动静一源”,是封建伦理的升华和至善的道德;它是“辨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样,被改造过的《大学》“致知”和被发挥了的《孟子》“良知”两个观点便溶合为王守仁的“致良知”说。在王守仁看来,“良知”也就是“道”、“天理”、“本心”;“致”就是使良知“明觉”和“发用流行”。“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扩充、推及到万事万物之中,予以发扬光大,从而将人的潜在道德意识转化成现实的人生价值。
王守仁之所以要倡导“致良知”,自然是为了达到“为善会恶”、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这个现实目的。所以,他后来把自己的心学宗旨归结为“王门四句教”,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是王守仁的晚年定论,与其“致良知”说相吻合。由于“致良知”说甚为“明白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党”(《寄邹谦之(三)》),加之王守仁宣扬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传习录下》),使“致良知”得以普及和推广,因而其影响十分深远。
教育论
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京师任职时正式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嘉靖七年(1529年)去世,一共渡过了20余年的讲学生涯。他注意继承古代教育传统,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