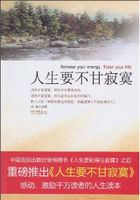一、留在我心底的眼睛
今天的少年,不会知道那时候……那时候,是1966年的8月。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卷起了“横扫一切”
的风暴;谁也不知道这风暴将要刮到什么时候。许多人睡下的时候还是个革命者,醒来却成了“反革命”。亲人不再相认,同志间不再有真诚。疯狂、颠倒,整个社会混乱了,人的心也倒悬起来。
那时候,我是个27岁的青年,在大学里教书。可我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反革命分子”。在这风暴刚刚腾起的时候,我就被列为“横扫”的对象,挨了无数次“批斗”。我不知道为什么,别人也不知道,连同那些批斗我的人。他们说我是“漏网右派”,但是,我怎样“右”法,又是怎样“漏网”的,谁也说不清。
我的心充满了迷惘和痛苦。但我却因此而出了“名”。当我的名字被大大地写在纸上倒挂而又划上红“×”的时候,当我被拽到台上被人扭起手臂弯腰低头的时候,我在学校和宿舍区是个妇孺皆知的“名人”。人人远离我,仿佛我是个传染病患者。当批斗者也玩腻了的时候,我被打发去拔草,从晨至昏,蹲在热地里拔草,是难受的,尤其是心里难受的时候。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我蹲在校园的铁栏墙边拔草,铁栏外,是一条通往近郊农村的小道。小道上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骑车的,步行的,凡看到我们这些拔草者,都会停下来,或者默默地看一阵,或者高声地讽刺,低声地议论一番。我以为这是种污辱,我的心淌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铁栏外站了一群小学生。他们是去参加义务劳动,还是劳动归来,我说不清。也许,他们是列席参加了一次“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归来。他们站在铁栏外,指手画脚地议论我们,用最纯洁的心诅咒我们,还有几个男孩子用土块、小石头砸我们。
我不能违犯“纪律”离开铁栏杆。我只有忍受那咒骂、那石块,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坍了,四周是一片黑暗。假如连纯洁的孩子都疯狂了,生活还有什么希望?就在这时候,一声轻轻的、甜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叔叔!”
我抬起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站在铁栏外面对着我。她乌黑的短发下有一双明澈的眼睛,清秀的脸颊上滴着汗水,手里捏着两根冰棍儿。
“叔叔,给!”她把一根冰棍儿从铁栏外伸过来,两只眼里全是真诚和期待。周围的孩子们哄地发出一片嘲笑和指责。她连头也不回,只是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期待地望着我。
在我从睡梦中被人拉起推到学校的时候,在我被草绳捆住,头上被罩上厕所里的便纸篓的时候,我没有一滴泪,这时候,我却止不住泪水了。我的泪泉被一个小姑娘的心捅开了。
我不敢吃,也实在不愿吃那根冰棍儿,这将会给那个小姑娘带来灾祸。我抬起泪眼凝望着她。她却固执地伸着那只拿冰棍儿的手。周围一片寂静,那些哄笑的孩子们也噤了声,所有的人都看着她,连同那些过路的人。
小姑娘也凝视着我,给我以鼓励和安慰。我终于忍不住,伸过头去,咬了一口那冰凉、甘甜的冰棍儿,然后,伸出脏手,捏住那冰棍儿,把它递给一位现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的历史学老教授。那老教授也泪眼模糊,抖颤着手接过这孩子最珍贵的赠予。
当我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那小姑娘已经走了,只有她洗得褪色的蓝布上衣在小路上飘摆……啊,你这清秀的小姑娘,你的姓名我不曾知道,但是你的爱心,你的正直,你的清敞的眼睛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力量,使我度过了那疯狂、颠倒的岁月。我永远感谢你。
也许你今天已经步入中年,成了国家的栋梁;也许,你早已经把这件小事遗忘。可是,你的那双眼睛永远留在我心底,它将伴随我走完生命的路程。
二、糕点的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糕点的故事。
糕点,故乡人一向称之为“子”。在我的记忆中,子绝不是随便充饥的大路货,而是出门入户的礼品。在我儿时,子的品种十分单一,只有那种用模具脱成的、有凹凸花纹的“八大块”。八大块即为一斤,要连包装纸算在内。包装纸是内外迥异的两层,里面是厚墩墩的糙纸,外层是普通包货纸,双层叠得四棱见线,顶上要压封一张彩印的“子票”。体面的人出门要带上两包子,上下系成一对,手头拮据的人往往只带一包,看望过人家之后大都有“自知之明”,不在那儿用饭。
那时候是难以捞到子吃的。因为家境贫寒,即使有亲戚带来,也必定留着出门时带给别家。故乡有句俗话,“过年子比人忙”。如果偶尔能有子分吃,那一定是已过了往来拜望的时节,子包早已磨损了边棱,甚至那八大块中的某一块已被谁家的母亲让孩子啃去了一些边缘。分到一块子,还要抢到那张同样已磨损了的子票,叠起来,藏在自己认为最稳妥的地方,不让任何人也不让老鼠偷走。它的用项是逢到中秋节或下一个年节时剪窗花。子绝对不会狼吞虎咽吃下去的,要嗅个够,才开吃,吃得细致而久长,有时候要留下一点儿,馋着看看。子里边的核桃仁要挑出来,看明白才舍得嚼呢。啊,那时候的子多么珍贵。
在我十多岁的一天,我去赶集。我的任务是卖掉一些玉米,把钱拿回来到矿上买煤。在那大集的街口,我看见一位老头,蹲着,面前一只破旧的柳编小浅篮放着一包子,子上插了一支小小的谷草十字架。老头默默无语,但是目光不停地追寻过往的赶集人。我明白,他要卖掉那包子。那也是一包包装破损的子。
时令已是古历的三月,那年头热得早,别人已穿了夹衣,老人还穿着棉袄棉裤。我想:他为什么要卖掉这包子呢?凭他的年纪,还没有吃一包子的资格吗?
在粮市卖完玉米,天已过晌午了,我非常饿。我的肠胃告诉我什么都想吃,尤其想吃插有谷草十字架的那包子。我固然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吃子,但是我知道这样出卖的子肯定便宜。为什么不买下来,自己吃一块、两块,再拿回家去孝敬妈妈呢?
赶回街口,我蹲到老人面前,问:“这包子多少钱呢?”
老头伸出四根指头:“四角。”
我把谷草十字架从纸绳中轻轻拔下来,说:“我要了。”递给他四角钱。
老人样子是高兴的。他撩起棉裤脚,我见到的是一条疮疡连片的枯腿。他指着,对我说:“我就去抓药了,改日说话!”
我饿得东倒西晃地回到家,才打开了子包。我没有背着妈妈吃好东西的习惯。
是八大块。八大块一点儿也不缺,但是全都生满了绿斑,霉了。妈妈用菜刀把绿斑刮掉,里边依然是墨绿的颜色。掰开来,没有可吃的了。
我多么难过,我白白地花去了四角钱。“妈,他骗了我们,真可恶!”我的眼泪下来了。
“不,不会的。”妈妈说,“他不知道子搁坏了,你不是说他治腿要钱花吗?
”妈妈擦去我的泪,安慰我,“咱们的四角钱,也不准能治好他的腿,他可怜啊。”
我细细想:老人也的确可怜。
“我们常常觉得苦,世上还有比我们苦的人。他一定没有玉米可卖呢。苦日子要挺住,苦尽甜来,咱们盼着。”
三、良心如枕
午后,倚于床头闲翻杂志,看到一个句子:“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就随手记在纸上,体味。这个句子让我想起一些普通的人和事来。
一件事是发生在我母亲身上的。夏天晚上,我们在院中纳凉。一只半大白兔从门缝跑进我家,赶之不去。母亲说:“天这么晚了,让兔子往哪儿去呢?弄不好会让什么给吃了。先留它一夜吧,明早谁吆喝,再还给谁。”我就找出一个笼子把兔子安置下来。
到了第二天,并没有人吆喝少了兔子,又过了好多天,还是没人找。兔子在我家一天天过下来,母亲却日益感到不安。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古训,母亲不懂得也没听说过,但却凭着做人莫坏良心的本能而奉行着并教导我们一生也要这样严谨地做人。所以一只误闯我家的兔子成为母亲的心事也就不足为怪了。
她的不安在一天晚饭后再次流露出来。那晚她一边给兔子喂青草,一边说:“我怎么老觉得眼皮跳?耳根发热?兔子,你说是喂你还是放了你?”兔子只顾埋头津津有味地吃草。
母亲叹了口气,从父亲的皮夹里抽出两块钱走了出去。
过一会儿,她回来了,如释重负地说:“我把两块钱丢在两边大路口了。随便谁捡了去,就当赎这只兔子了,省得晚上睡觉也不塌实。”
这件小事在一些人看来也许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带着迂腐的天真,但我相信另有一些人会表示理解并有同感。生而为人,总与一些事相连。有些事情,也许不为人所知,似躲不过良心的审视,尤其当午夜梦回时,也是良心靠灵魂最近的时刻。
真的,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枕着这个温柔的枕头,我们得以安然入眠。
四、一杯白开水
读大学那年,我得了肺结核病。因我的家乡偏远,所以校方没有通知我的父母就安排我住进了学校附近的一所医院。
因为是传染病,昔日很要好的同学都怕被沾上身,像躲瘟疫一样逃避我。因此,去医院探望我的人很少。我每天沮丧地躺在床上,想起人生的无常,世态的炎凉,大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每每看到邻床的病友们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去探望他们,我总有一种无名的失落涌上心头,甚至想到了死。我不但不配合医生的治疗,还消极地用药,病情没有一点好转。
一天下午,我倒好一杯白开水,百无聊赖地趴在病床上给远方的父母写信。忽然,护士小姐进来告诉我,院门口有个女孩要来看我,我一听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住院以来第一个女孩来看我。我原以为是我心仪已久的英。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子女孩提着一兜橘子在护士小姐的陪同下来到了我的病房。原来是丝绸专业的一个不算熟悉的女孩子,叫翟宵。她是校女子篮球队队长,听人说是位个性极强的女孩。我跟她交往很少,平常见面只是打个招呼,所以她的到来使我非常吃惊。记得她当时满头大汗,将提兜中的橘子放到我的床头柜上便坐在我的床沿上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并安慰我说,这种病很平常,不要有心理负担,但我仍忧郁地摇了摇头。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小时,她忽然端起我床头柜上的那杯白开水说,她渴极了,便要喝。我惊呆了,急忙阻止她说:“不行的,我有传染病——你还是吃橘子吧!”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然后用手抹了抹嘴唇,笑着对我说:“没关系,健康的生命是不怕被传染的!”望着她那张健康纯真的笑脸和眼镜后面那秋水般明澈的眼睛,我的泪水差一点流了下来,她之所以喝下这杯水,是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来证明这种病的轻松,以减轻我沉重的心理负担呀!
流年似水,学生时代的记忆已越来越模糊了,不知怎的,惟有这位女同学当年喝下那杯白开水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
时至今日,我才明白:有时候,人生中一个偶然的细节,却让你用一辈子的时光去体验和感受。
五、一个日耳曼男人的眼泪
莱勒镇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北方小镇。小镇丁字路口北侧有间堪称小镇一景的修鞋店,这间修鞋店临街的正方形大窗户下,有一个用红白大理石修建的专为非洲捐鞋的“捐鞋台”。台子四周有一圈精美秀丽的白石栏杆,每个栏柱顶端都有一颗心形石雕,台上四个柱子擎起一个呈穹隆形的镀金石顶棚,看上去很像一个小巧玲珑的凉亭。
几乎每天捐鞋台上都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这些鞋从外表看非常干净,同新鞋没有什么两样。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大部分鞋是七八成新的,只是样式过时或是过了季节,还有些人将坏了一点儿的鞋先拿到修鞋店去修整,然后做些技术处理如打鞋油、喷香水、换条新鞋带等。我又好奇地问:“这么多漂亮的鞋为什么捐到这家修鞋店?能保证捐到非洲吗?”这位朋友似乎听出了我话中的弦外之音,他忙笑着说:“我可以向上帝保证,店主弗里茨先生不会把这些鞋挪作他用,他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好老头。”
一天我又到小街散步,转悠转悠终于抑制不住好奇之心便走进了修鞋店。店内正面墙上悬挂的一幅黑门大照片赫然映入眼帘:一个瘦骨嶙峋的黑人躺在杂草丛生的公路旁。两手抱着流血的双脚,痛苦万状的表情震撼人心。“请坐吧!”满头白发的弗里茨老人诧异地看着我,“不是修鞋吧?”他问道。我正为自己既不是来修鞋也不是来捐鞋而感到尴尬时,老人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请坐,来我这儿参观的人远比修鞋的人多。”我这才坐在一张洁净的沙发上,仔细打量这间十七八平方米的修鞋店。室内窗明几净,非常现代化,绝不是我印象中的那种修鞋店。
我先从这张照片谈起,慢慢地同老人聊起来。这张照片是弗里茨于60年代在汉诺威参观一个图片展览会时看到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流下了眼泪。“那是一个日耳曼男人的眼泪,绝不是轻易流淌的。”弗里茨反复强调。后来他设法从拍摄该照片的德国通讯社记者那里索取了这张照片,并从记者那里了解到许多背景情况。记者采访这个非洲国家时有70%以上的人没鞋穿,长年打赤脚,一次他们开车外出,途中遇到一位不慎刺破双脚的黑人,他抓拍了这张照片。
“这是一张获金奖的照片。我并不懂艺术,对我这个同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来说我想的是另外一方面的事。”说到这里,老人慈善的双眼噙着泪花。老人十几岁就在耶拿的一家鞋厂当学徒,几十年的制鞋生涯使他练就了一手绝活。60年代中期的这张照片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萌发了向非洲捐鞋的想法,于是他辞去了鞋厂主管的职务,办了修鞋店并修建了捐鞋台。弗里茨除修鞋外,还为畸形脚和特型脚定做鞋子,每天都要亲手缝制几双鞋捐给非洲。
弗里茨的行为感动了许多人,本镇和附近城镇的人们纷纷前来捐鞋,后来莱勒镇修鞋店名声大振,人们从德国四面八方专程到莱勒镇捐鞋,还有不少外国游客也闻讯前来捐鞋。当地市政厅专门指定民政署抽专人协助弗里茨处理捐鞋事务。
我告别老人,走出修鞋店,迎面碰见一对前来捐鞋的中年夫妇,只见他们打开一个大包将5双大小不等的鞋子整齐地摆在台上,原来他们还代表3个因上学不能前来的孩子捐鞋。
在即将离开莱勒镇的一天傍晚,我又一次来到镇南小街,夕阳把它绚丽多彩的余晖洒落在小小的修鞋店和捐鞋台上,远远望去竟显得那般金碧辉煌、华丽富足。一会儿,弗里茨老人怀抱一摞纸盒从店里出来,他躬身台前用颤抖的手将一双双鞋分别装入不同型号的盒里。望着老人的背影,我脑海中浮现山照片中那张非洲黑人痛苦的脸和弗里茨老人慈祥的面容,我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了……六、想及他人
时下的综艺节目中往往穿插一些要现场嘉宾回答问题的节目,时下的嘉宾往往非常机灵,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只要导游小姐一声“这是干什么用的呢”,他们都能凭着丰富的想像,争先恐后地说出种种答案来,而且,总能猜它个八九不离十。
却有一次例外的意外。
那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东西——电梯,问题是:电梯里总有一面大镜子,那大镜子是干什么用的呢?回答踊跃异常:
——用来对镜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