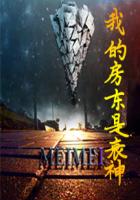宋人话本写妇女的生活,写她们对爱情婚姻幸福的追求,不是孤立的描写,而是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她们的命运和遭遇,让人看到当时社会的面貌。璩秀秀所追求的是起码的人身自由和个人幸福,她只想能摆脱不被当成人的被奴役地位,与自己心爱的人过自食其力的生活,但却被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郡王活活打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周大郎极力阻止女儿的婚事,周胜仙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反映出封建门第观念的深重影响。《王魁》反映出一个深刻的新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后来许多作品所反映的“痴心女子负心汉”主题。科举制度打破了豪门士族对官场的垄断,庶族寒士也可以通过参加科考跻身官场,这就是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这些科举的幸运儿“一阔脸就变”,“贵易妻”也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贫穷女子成了牺牲品。桂英就是其中一个,她的悲剧是有典型性的。作者对她充满了同情,最后写到“桂英死报”,既表现出宋人话本反映现实的敏锐性,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宋人话本小说的另一重要题材是公案,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随着封建社会向后期发展,封建专制统治日益稳固,社会也越来越腐败黑暗,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残害越来越严重。公案类作品的大量出现,正是封建统治阶级草菅人命、制造冤狱的黑暗现实的反映。
《错斩崔宁》通过一个冤案,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法制的腐败和封建官吏草菅人命的罪恶。小市民刘贵向岳父借得十五贯钱,回家后对小娘子陈二姐开玩笑说是她的卖身钱,于是陈二姐连夜逃开,想回娘家。当夜,刘贵被杀,银子被抢。陈二姐早起路遇小贩崔宁,结伴同行。人们赶来抓住,崔宁身上刚好带有卖丝得来的十五贯钱,银数的巧合成了罪证。虽然崔宁对银子来源交代得很清楚,但府尹咬定“世间不信有这等巧合事”,既不听申辩,也不去调查,只是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两个无辜的人被糊里糊涂地处斩了。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也不难调查清楚,但封建官吏视人命如儿戏、武断专横,随意制造冤案。作者气愤地说: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相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明确指明这个简单易断的案子成为冤案是因为“问官糊涂,只图了事”,只知“捶楚”。作品以简单冤案来揭露当时社会的阴暗,反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充分说明封建官吏昏聩到何等程度,封建官府黑暗到何等程度。作者不由得发出痛切的呼吁:
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在这些糊涂问官的身上,作者不仅揭露了他们不分青红皂白、武断专横、滥杀无辜的罪恶,而且更窥视到封建官吏视人命如草芥,对人、人性和人权的压制和漠视。因而作品不再局限于对昏官糊涂不明的批判,更发出了争取人权、重视人命的深沉呼声。
《陈可常端阳仙化》中的吴七郡王听了针对可常和尚的诬告,就随意“教人分付临安府”抓了,也不容分辩,将“被告”打得皮开肉绽,郡王想怎么判处就怎么判处,临安府也不敢做主。
在这些公案作品中,除了揭露社会黑暗、官府昏庸专横外,还突出反映了当时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错斩崔宁》中的陈二姐,听到刘贵的一句“戏言”之所以信以为真,就是因为当时确实存在典当与买卖妇女的野蛮制度。听说丈夫把她卖了十五贯,她的疑虑也主要在于“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并非不肯相信,更非要有所反抗。唯其如此,更显出这种事情的普遍性,才更反映出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居然像牲畜一样听任买卖。
社会黑暗、狱冤遍布,生活于苦难中的广大市民群众渴望着减轻苦难,得到拯救,于是在公案话本小说中出现了“清官”的形象。《三现身包龙图断狱》《合同文字记》中的包公,就是一个典型。他“能剖人间暧昧之情,断天下狐疑之狱”救民于水火。而且他还能“日间断人,夜间断鬼”,有超凡的智慧和权力。与以后小说戏曲中出现的“包青天”形象比起来,宋人话本小说中的包公形象还是较为单薄粗疏的,但却为后来流芳百世的包公形象打下了基础。《皂角林大王假形》中的赵知县,也是一个“清官”形象。在市民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起来的“清官”,是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是随时可能会遭到飞来横祸,蒙受不白之冤的市民们,为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无理迫害而制造的偶像。《错斩崔宁》中,小商贩崔宁只是与陈二姐同行即被冤,可见飞来横祸是如何地让人防不胜防。而如果有“清官”包公在,他也许就不会蒙冤被害,屈死刀下。话本小说中的“清官”,即使是历史上确有其人,也不再是历史人物的简单再现,而成为市民理想的寄托,体现出他们要把自己对社会和事件的看法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的愿望。市民的这种理想和愿望借《王魁》中的阴间判官的口表达了出来:
阳间势利套子,富贵人只顾把贫贱的欺凌摆布,不死不休……俺大王心如镜,耳似铁,只论人功过,那管人情面?只论人善恶,那顾人贵贱?
通过幻想表达的这些要求,实质上是要求在法律面前有平等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于是寄托于“清官”。但“清官”也只是一种幻想。
除幻想“清官”来解救自己外,市民们还希望有人能除暴惩凶,为自己出一口恶气,《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等作品就反映了这一点。这篇话本小说歌颂的是一批侠盗,他们机智大胆,以神出鬼没的本领、高超出奇的手段,窃富济贫、骚扰官府,“激恼京师”。他们为穷人伸张正义,惩罚贫吝刻薄、为富不仁的财主张富,使他坐牢破产而死。他们还偷走了钱王府的金银、玉带,剪掉了马观察的一半袖子,割去了滕大尹的腰带挞尾,在皇城脚下戏耍官吏,闹得满城风雨。在他们的挑战面前,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们专与富豪、权贵、官府作对,他们对权贵富豪的戏弄和惩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恨情绪,表现了对迫害者的反抗斗争。《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尹宗也是一个侠盗。他虽是偷儿,但能急人之难,救人之命,并为救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作品反映出市民群众反抗黑暗社会、反抗封建压迫的强烈情绪,与公案作品中的“清官”,一文一武,成为市民反抗精神的寄托。
宋代统治者由于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国力孱弱、外患不已、最后北宋覆灭,南宋半壁江山也朝不保夕,一个民族矛盾尖锐、民族灾难深重的朝代到来了。面向现实的宋人话本也有反映民族矛盾之作,《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就是一个代表。北宋沦亡时,入侵的金兵俘虏了徽、钦二帝,也掳掠去大批宫女和平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南宋时期,出现不少抒写亡国之痛和流落异邦之苦的作品,如《靖康孤臣泣血路》《窃愤录》等,但都是为最高统治者唱哀歌的,而这篇话本小说,却展现了民族大灾难中广大人民群众生离死别的悲惨图景。作品写“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对金统治者作了高度概括和深刻揭露,通过对流落敌国的杨思温在热闹节日里凄凉心境的表现,抒发了无可奈何的亡国之痛;以郑意娘的一灵不昧,刻画了国破家亡时殉身的鬼魂的难以瞑目;又以韩思厚的违弃盟誓、另求新欢,谴责了不能坚持节操的乱世男女,揭示了“人不如鬼”的严酷现实。压抑的气氛、沉痛的感情,真实地再现了民族大灾难中生活于“人鬼相杂”世道的人民的苦难和沦陷区人民的心理创伤,表现了反对民族压迫的情绪,在话本小说中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领域和感情世界。宋人话本中还有不少志怪之作,只是为迎合小市民的猎奇心理,并无什么意义。一些据历史和旧著编写的作品,一般说来,思想价值也较弱。只有那些面向社会现实、反映市民生活的作品,才是宋人话本小说的代表。
宋人话本小说是宋代市民生活和思想意识的真实记录,这些有幸流传下来的作品,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秩序的混乱。当时的官府贿赂公行,不断地制造冤狱,滥杀无辜。都城临安,夜有盗贼谋财害命,城外郊野更有恶贼拦路抢劫、杀人越货。宋代市民阶层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在沉重的封建势力压迫下,他们希望能得到“清官”的解救,也渴求有“侠盗”除暴惩恶,并以浪漫的幻想,让在现实生活中被迫害至死的有情人变成鬼——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得到幸福。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为人身解放和婚姻自主,进行了勇敢而顽强的斗争,表现了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执着追求。他们也艳羡发迹,幻想有神怪相助,如《董永遇仙记》中的贫苦农民董永,依靠仙女的帮助,不仅摆脱了佣工奴役,而且后来还当了兵部尚书,而他与七仙女生的儿子,竟然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这种想象何其大胆、活跃。但是,市民们的生活理想却主要是在世上过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生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仅璩秀秀、崔宁是这样,就是其中的历史人物(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是通过开酒肆来谋生,过着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
宋人话本小说是市民生活真实生动的历史画卷,充分表现了处于封建势力重压下的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是真正“为市井细民写心”的。
刚刚从封建社会母体中成长起来的市民阶层,其思想意识带有明显的不成熟特征,且具有复杂性、模糊性,还带有软弱性。他们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有冲破封建思想牢笼的强烈愿望,但却由于时代的限制,尚未找到与之对抗的思想武器。因而,即使他们斗争是勇敢的,但思想意识却并非很明确,还带有某种程度的盲目。如周胜仙,不可谓不勇敢坚定,但对那个见到她的鬼魂就惊慌失措以致误伤她的男人到底是否真值得她爱,却似乎从没有认清。也就是说,她只是在追逐爱情,舍生忘死地狂热追逐爱情,至于这爱情的内涵、思想意蕴是什么,她却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其中就包含了某种盲目。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理想,有过幸福生活的愿望,也曾为实现这种愿望奋斗过,但不少人却因惧怕封建压力而显得软弱,特别是那些男主人公。崔宁不及璩秀秀坚强,也可能有性格因素,而实质上是思想境界的差异。而张胜更不能与执著的小夫人相比,这个对小夫人未必没有一点爱慕之心的主管,由于畏惧封建势力,思想上受封建礼教束缚,在小夫人顽强执著的追求面前,显得那么怯懦、软弱。然而,话本小说虽对小夫人的不幸命运充满同情,却仍然要肯定张胜“立心至诚”,以至把小夫人当成祸水,而张胜“不受其祸”。所谓“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所以本篇又名《张主管至诚脱奇祸》。话本作者的这种矛盾的处理,充分反映了刚刚从封建社会母体中挣扎出来的早期市民阶层在思想意识上的复杂性、矛盾性、软弱性。即使像《碾玉观音》这样的优秀之作,虽然充分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下层劳动者的迫害,但其矛头却主要指向了挑拨是非的郭排军,这实际上为主犯郡王减轻了罪责,勇敢反抗的璩秀秀也只是以惩处郭排军来报冤仇罢了。《错斩崔宁》这种深刻揭露官府专横昏聩、草菅人命的作品,却又强调“只因戏言酿灾危”,削弱了作品思想的尖锐性。《陈可常端阳仙化》更是把陈可常被迫害致死说成是“前生欠宿债,今生转来还”。
由于他们受封建统治者的迫害,所以渴望有“侠盗”为之出气,但是当他们兴高采烈地赞赏宋四公、赵正戏弄官府、惩处恶人、大闹东京时,又不忘提及他们的破坏性,如写宋四公行窃时杀死无辜妇女,赵正捉弄侯兴杀死亲生儿子等令人切齿的罪行。这种矛盾正是早期市民意识的反映。这篇话本小说所包含的官逼民反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水浒传》的先声,但其思想价值却不可与《水浒传》同日而语。
至于宋人话本中所反映的因果报应、封建迷信思想等等,并非仅是早期市民意识,而且也不仅仅是市民阶层所具有的思想意识。不过,在这些落后意识中,也包含着在现实生活中遭受苦难和迫害的市民们的愿望:“若是世人能辨假,真人不用诉明神。”信奉神明保佑与幻想“清官庇护”,思想认识上具有相通之处。
(三)别具特色的叙文艺术
宋人话本小说是由入话、头回、正话、篇尾等部分组成的,成为话本小说的标志,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独特体制。
宋代话本小说一般在开头都有“入话”,中间有诗词韵语的穿插,结尾用诗句结束。“说话”人在正式开讲之前,为了使已到场的听众安静下来,并等候后来的听众陆续到场,往往要先串讲一些诗词或讲一个与主体故事(正话)有关的小故事,这就是“入话”,也叫做“头回”。如《错斩崔宁》开篇有诗: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
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
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这首诗讲出了为人的难处,说明举止言行需谨慎。接下来先串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叫魏鹏举的新科进士,因一句戏言被降职,丢了锦绣前程。恰恰也是因为戏言,《错斩崔宁》中的刘贵丢了性命。
在讲说过程中,特别是当故事发展到紧要去处,“说话”人又往往要插入一些诗词韵语,或写景、或状物,或发感慨、或作评赞,既可对讲说部分起到加强或烘托的作用,又可以通过吟唱或吟诵的形式调剂听众的情绪。话本结尾往往采用两句或一首散场诗,用以总括全篇,点明主题,一般具有惩恶劝善或总结教训的意味。如《错斩崔宁》的结尾,有诗为证: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灾危。劝君出语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所有这些结构形式,都是宋代话本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但为明清的拟话本小说所继承,而且对以后的中长篇小说也有很大影响。
体制毕竟只是形式,更为根本的是,宋人话本小说是由听觉文学向视觉文学的过渡,仍受“说话”的影响,具有诉诸听觉的艺术特点。这一总特点,规定了话本的叙述方式和方法。
1.情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