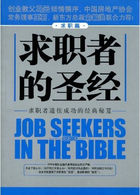《情人》是一本野蛮的书,它带来所有它遇见的东西,毫无区分,几乎无选择地迸出。所有的激情,语言上的、情感上的都一并宣泄而出。这是一本属于杜拉斯的书,只有个性如她才会对爱情有这样绝望而丰满的感触;这也是一本属于所有深深爱过的人的书,因为只有深深爱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深沉而无望的爱情过往。
她所展示给你的世界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现实在她眼中,没有任何的遮挡。她的瞳仁是一面光洁明亮的镜子,不,比镜子还要忠实。世界以什么样的面目展示给它,它便以同样的面目展示给我们,分毫不差。
黑暗中孤独盛开的双唇,冰冷颤动而青涩的指尖,擦肩而过中不经意却永远地凝视,那个夏天湄公河畔飘散湿润的水草香气,十五岁的白人女孩,穿着旧的丝质连身裙和金边高跟鞋,梳印第安人的麻花辫,涂着口红,贫穷、放肆的眼神,然后在渡轮上遇见来自中国北方的男人。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让人沉沦。他们被世俗阻挡,然后尝尽生死离别。所有爱、希望与死亡在整个过程中被无限地放大和体验。恰恰就是这样一场爱情,如同一瓶愈藏愈醇的美酒一样,在这样一个抛却年龄、地位、世俗的本身带有末期殖民色彩的西贡舞台上散发得这样芳醇郁香。
书中有大量优美而富有诗意的关于性爱的浪漫叙述。“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仿佛是它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流动之中爱抚他。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要死掉的。”“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变老了。”
无可否认,杜拉斯写出了绝大多数写作人所想表达出的共同主题,那便是人性——纯真、残酷、自私、坚强和怯弱、永恒与瞬间、绝望和孤独。
在小说的性描写中,杜拉斯始终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立场、女性特有的审美视角,对人类特别是女性的性意识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新的思考,赋予其真正的人的情感、人的生命活力和人的欲望要求,并且予以审美的提升——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却又不得不承受的情感欲壑。杜拉斯以百无禁忌的笔触展示了女性最隐秘的内心世界,把女性的个人经验推到极致而又独树一帜;她以精湛独到的精神分析,把女性多重心理剖析得丝丝入扣而自成一家,她对于女性生命真切的体验和大胆的描述,堪称当代女性神话。
杜拉斯的一生是追求极限写作的一生。一切以绝望开始的写法,就是典型的杜拉斯句式。她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对生命的思考,走的是一条极端化的道路,要么得到全部,要么一无所有。杜拉斯笔下的爱情是对灵魂的绝对欣赏、绝对讴歌;灵魂与肉体可以超越时空,使死亡在真爱面前俯首称臣。作为读者起码应该具备对激情的欣赏能力,能包容并深切理解她那异乎寻常的既晦涩又先锋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看懂她。
这是一部激情的史作,不管是有关性爱和激情的描述,还是内容上的错落有致,就连语言——同样具有短促有力的激情,都在这部小说中蕴藏了杜拉斯无限的生命激情。读者在她的引导下,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遥远的艺术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领略异国风情,承受生命的沉重。但《情人》绝不等同于自传,同样也不应仅仅归之为一个故事,因为这作品包含的内容大于情节。这本书的主体绝非一个法国少女和一个中国男人的故事,而是杜拉斯和作为她的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浸淫在其间的关于爱的理解,它成为杜拉斯之所以为杜拉斯的原因。
如果我们已经拥有了动人浪漫或是感性甜蜜的爱情,那不妨来看看杜拉斯的《情人》,体味一场激情缠绵、生动、鲜活而又如此绝望、无力的爱情。
14.美与爱是独立的——川端康成《雪国》
“虽然她自己并不自觉,但她总是以大自然的峡谷作为自己的听众,孤独地练习弹奏。久而久之,她的弹拨就有力量。这种孤独驱散了哀愁,蕴涵着一种豪放的意志……在岛村看来,驹子的这种生活可以说是徒劳无益的……”
被誉为日本“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的川端康成,“由于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也是这部《雪国》,让他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这部小说中几乎不存在戏剧式的起伏和冲突,所以如果不能体味到活跃着的浸透力,也许就会觉得再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世界了。那样的话,作品中就只剩下日本的美与情趣了。但就是这一缕缕氤氲首尾的凄凉,构成了本书含蓄的悲剧美。
岛村是个成年男人,一百九十九天以前在雪国这地方认识了一个叫驹子的艺妓姑娘,并与之发生了夹杂着肉与灵、颓伤与健康、哀与艳的关系。
驹子在年仅十六岁的时候被卖到东京去做用人,离开雪国的时候只有师傅家的儿子,名叫行男的人去送她。几年后师傅出钱赎回了她,回到了雪国。就在这时,十九岁的驹子遇到了来雪国旅游的岛村,并且爱上了他。她为他献出了一切,可是这个男人很快就回到东京。过了一百九十九天后,驹子终于盼到他回来。在情人的怀抱里,她把每个分别的日子一天一天地细数出来,一百九十九天啊!可是现在的驹子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艺妓,尽管她还是那样的清纯,那样的出淤泥而不染。
第二次相会很快也要结束了,岛村要回东京,驹子到火车站送他。这时候,爱上师兄的那个女子叶子慌张地跑来,告诉她师兄行男不行了,求她去见他最后一面。驹子拒绝了。驹子不愿意去为一个曾经为她送行的人去送终,而执意要送爱人回东京,哪怕眼前的这个男人根本就不会给予她什么,她也不在乎。小说就用这样的悲哀和冷艳来揭示驹子要告别往日生活的决心。用男主人公的话来说,这就是美的徒劳。
巧的是,这时候火车来了,岛村踏上了去东京的车,而驹子则要回到雪国继续当她的艺妓,去面对那个也许已经咽气的师兄行男和自己永远光明同时也永远黑暗的生活。光明是因为她心中有爱,有岛村,而且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同命运抗争,努力摆脱艺妓的处境,争取获得普通人起码的生活权利和爱的权利;而黑暗是因为谁也无法改变她的命运,谁也无法改变比雪国的雪更冰冷的现实,这是另一个意义上的宿命。
第三次见面又是一年之后了。岛村每次见到驹子都有变化,但是不变的是她的心,不变的是她那种永远属于自己的追求生活的方式:在悲哀与冷艳中看着时光的消逝,有所作为而最终却无力改变。她努力地学三弦,学舞蹈,学其他技艺,还天真地认为,到哪里做(艺妓)都一样。她依然还是那样深深地爱着岛村。
行男已经死了,可是驹子和叶子的生活还在继续。驹子周旋在来寻欢作乐的客人之间,而叶子每天都要到荞麦地里的坟墓前去看行男。
在岛村想要离开雪国从而彻底把驹子忘记时,叶子出现在他前面,恳求带她离开雪国,到东京去。其实这话应该是驹子说的才对。如果能带,岛村也许早就那么做了。他在拒绝叶子的同时也对驹子关上了她所盼望着的、从来没说出来的希望的大门。
正当岛村要离开之时,蚕房失火了,在上面的叶子掉了下来,死了。而驹子抱着叶子的尸体,疯了。
岛村抬头望去,“银河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上倾泻了下来”。
《雪国》无论是主题还是语言,都浸泡在一种悲哀与冷艳的氛围中,弥漫着强烈的东方色彩的宿命与轮回观念,但是透过这些深入到《雪国》主人公驹子的内心世界,我们会发现,川端康成致力要表现的是展示朦胧的、内在的、感觉性的、悲哀的美。他以极其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使用简洁而神秘的价值观来表现整个作品的技巧,整个作品是对日本绘画的怀旧;崇拜脆弱之美,崇拜用于写照自然界生命与人类尊严的忧郁语言。
对女主人公驹子来说,她的不幸遭遇扭曲了她的灵魂,自然形成了她复杂矛盾而畸形的性格:倔强、热情、纯真而又粗野、妖媚、邪俗。但她对命运的抗争是清晰的:即使是做了艺妓,也不自暴自弃,她抗争着,挣扎着,但是却从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尤其是岛村身上。唯一支撑她在那个寒冷、闭塞的雪国活下去的理由就是对生活不变的信念以及对人生权利和做人尊严的追求。相信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对爱的依赖是与生俱来的,但不要将爱人当成自己的救世主,因为在人的概念上,我们是独立的!这也是整部《雪国》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