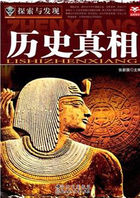我将记住我的过去,我厌恶链与绳——
我将记住一切森林之事以及我往日的威力。
我不会为一捆甘蔗把背出卖给人:
我将回到同类中间,回到林中同胞的兽穴那里。
我将出发一直走到早晨,走到白天——
去迎接纯净的风之亲吻,清洁的水之拥抱;
我将把桩子猛然拔断,忘记脚踝上的戒圈。
我将重获失去的爱及自由的伙伴——他们不少!
“卡拉·南格”是“黑蛇”的意思,47年来,凡大象能为印度政府做的事他都做过。他被捉住时已足足20岁,所以现在快70岁了——对大象而言已算高龄。他记得自己去推一支陷在深深的泥中的枪的事(前额上有一个皮垫)——那是在1842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前,他当时还没那么大的力气。
他母亲拉德哈·皮亚莉——可爱的拉德哈,她在同一次围赶中与卡拉·南格一道被捕获——在他乳牙长出前就告诉他说,害怕的象总会受伤害。卡拉·南格知道这是个好忠告,因他第一次看见壳破裂时发出尖叫,退到一堆步枪当中,刺刀把他一身最柔软的地方刺得很痛。所以他在25岁前就不再害怕了,成为替印度政府服务的最受喜爱和关心的大象。在前往印度北部的途中,他运载了帐篷——1200磅重的帐篷。他曾被一架起重机吊进船里,在水上运行了数天;把一辆迫击炮背到一个多岩的陌生国家,那儿离印度很远;目睹了西奥多皇帝死在马格达拉;又乘船返回,士兵们说他被授予了“阿比西尼亚战争”奖章。10年后,他在一个叫阿里.莫斯德的地方看见同伴死于寒冷、癫痫、饥饿和中暑。后来,他被送到数千英里远的南方,在莫尔麦的贮木场拉、堆大柚木。在那儿他把一只干活偷懒的年轻的象打得半死。
那以后就不让他拉木料了,只让它和另外许多经过专门训练的象一起帮着在加罗山区捕捉野象。印度政府对于象是严加保护的。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捕捉大象并训练他们,再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需要的地方去干活。
卡拉·南格的肩部离地足足有10英尺高,牙被砍掉只剩下5英尺,为防止牙裂开人们在顶部用铜皮扎上。尽管牙短了一截,但他比任何没经训练、长着真正尖牙的象还能干。数周以来,他们翻过一座座山,小心围赶着40或50只野象,最后到达了围场;用树干捆扎起来的大吊门在他们身后轰地一声落下。卡拉·南格得到命令,便来到那群眼冒怒火、发出喇叭般声音的混乱的野象中间(通常在夜晚,因在闪亮的火把下难以辨别距离),找到最大最野的象,狠狠撞他,直到他安静,而骑在大象上的男人们则用绳子拴住一些较小的野象。
老练机智的“黑蛇”卡拉·南格没有不懂的战术:他不只一次迎接了受伤老虎的进攻;他卷起灵活的身躯以免受到伤害,半空中忽然把头形成镰刀状(全是他自己发明的),将迎面扑来的猛兽撞到一边;用大膝跪在老虎身上,直把虎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声嚎叫后死去,卡拉·南格只需拉着这只毛绒绒的花斑东西的尾巴回去。
“是呀,”赶他的“大吐迈”说,大吐迈是把他带到阿比西尼亚来的“黑吐迈”的儿子,是“大象吐迈”的孙子(象们看见他被捉),“除我外,‘黑蛇’什么也不怕。他已经见过我们3代人喂养他,还会看见第4代人喂养他的。”
“他也怕我,”“小吐迈”说,他站直时有4英尺高,身上只围着一片布。他已10岁,是大吐迈的儿子,根据习俗,他长大后将替代父亲的位置骑在卡拉·南格脖子上,掌管那根沉重的、驯象用的铁刺棒——已被他父亲、祖父和曾祖父用得十分光滑。
小吐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他是在卡拉·南格的守候下出生的,能行走以前常玩弄大象的鼻尖,一旦能走后就把他带到河边;所以卡拉·南格决不会想到不听他那尖声的小命令,正如那天当大吐迈把他这个皮肤褐色的小婴带到卡拉·南格的长牙下面,让他向自己未来的主人行礼时,他决没想到要杀死小吐迈一样。
“是的,”小吐迈说,“他怕我。”然后他大步走到卡拉·南格面前,叫他老肥猪,还让他依次抬脚。
“哇!”小吐迈说,“你真是一只大象。”他摇着蓬松的头,一边重复父亲的话。“政府会支付大象的钱,不过他们属于我们看管象的人。等你老了,卡拉·南格,某个有钱的王公会根据你的身材和行为,把你从政府买走,那时你只需戴上金耳环,背上放着金象桥,两边盖着带金的红布,行进在王公队伍最前面。那时我会骑在你的脖子上,啊,卡拉·南格,手拿一根驯象用的银刺棒,男人们会拿着金黄色的棒跑在前面,喊道,‘快给王公的大象让路!’那将是不错的,卡拉·南格,可再好也不如这样在丛林里追猎。”
“哼!”大吐迈说,“你这个小子,像小野牛一样野。在山里跑上跑下并不是替政府干的最好活。我老啦,不喜欢野象。给我一排排砖筑的象厩,每只大象一栏,并有大桩把他们安全拴住,有宽平的路供操练,而不是这样来来去去宿营。哈,这些坎普尔工房真好。附近还有一个市场。每天只干3小时活。”
小吐迈记得坎普尔那些一排排砖筑的象厩,一言不语。他很宁愿过营地的生活,讨厌那些宽阔平坦的道路,讨厌每天在饲料槽里吃东西,以及长时间无事可做,仅仅看着卡拉·南格在拴他的桩子旁烦躁不安的样子。
小吐迈喜欢爬上只有象才能通过的小路;到下面的山谷里去;瞥见野象在数英里远处吃草;受怕的猪和孔雀在卡拉·南格脚下一冲而过;暖和的雨水下得令人迷茫,山上山谷一片雾气;美丽的早晨被薄雾笼罩,谁也不知当晚在哪里宿营;平稳而谨慎地围赶野象,在昨夜的围赶中出现的疯狂奔驰、强烈火光和高声喧闹——大象如山崩中的巨石一样涌进围场,却发现出去不了,于是猛撞一根根粗壮的柱子,结果只有被巨大的吼叫、熊熊的火把和齐射的空包弹吓退。
即使一个小男孩在这儿也有用,而吐迈可抵得上3个男孩。他挥动起火把来比谁都不差。不过围赶开始才是真正美妙的时刻,克达——也就是围场——看起来像一副世界末日画,男人们不得不相互打手势,因为听不到对方说话。这时小吐迈就爬上一根颤动的围场柱,被太阳晒白的褐色头发飘散在肩上,在火把的光中他看起来像个妖怪。一旦暂时平静就能听见他激励卡拉·南格时的高叫声,压过了绳子发出的噼啪声和被拴住的大象的呻吟。“马尔,马尔,卡拉·南格!(向前,向前,黑蛇!)当特杜!(把牙伸出去!)索马罗!索马罗!(小心,小心!)马若!马若!(打他,打他!)注意柱子!阿雷!阿雷!嗨!呀!卡——阿!”他总这样高喊,于是卡拉·南格与野象之间展开激战,在围场里冲来冲去。而捕象的老人们会擦去眼上的汗水,时时向小吐迈点头——他在柱子顶上高兴地扭动着身子。
他不仅扭动身子而已。一天晚上他还从柱上溜下去,在大象中东窜西窜,把绳子一端抛给一个围赶象的人,他正极力抓住一只乱踢的象仔的腿(小仔常比大动物更麻烦)。卡拉·南格看见他,抓住他身子,把他交给大吐迈,大吐迈当场打了他,又把他放回柱子上。
次日早晨大吐迈责备他说:“难道那一排排很好的象还不够,你还得自己去捉吗,可鄙的小家伙?这下好啦,那些薪水比我少的傻瓜猎人把此事告诉了皮特森·莎希布。”小吐迈被吓住了。他对白人不怎么了解,不过在他看来皮特森·莎希布是世上最了不起的白人。他是整个围场里的头目——替印度政府捕获所有大象,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了解象。
“将要——将要发生什么事?”小吐迈问。
“发生!要发生最糟糕的事啦。皮特森·莎希布是个疯子,不然他怎么会去猎这些凶猛的野兽?他甚至会让你也去捕象,睡在炎热的丛林里任何地方,最终被踩死在围场里。你这样胡闹不出什么问题就好了。下周捕象结束,我们这些平原上的人就会被送回到站上。那时我们就可以走在平坦的大道上,把这一切捕猎的事忘掉。可是,儿子,这事是应该让阿莎麦斯丛林里那些卑鄙的家伙去管的,你竟然也卷进去,真让我生气。卡拉·南格只听我的,我必须同他一起到围场里去;可他又只是一只战象,无法帮着用绳子拴住野象。所以我只好安心等待,这才适合一个赶象者的身份——不仅仅是个猎手——我是说一个赶象者,一个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人。难道大象吐迈的家人要在一个肮脏的围场里被踩在脚下?你是个坏小子!可鄙的儿子!去给卡拉·南格洗洗,料理一下他耳朵,别让他的脚上扎有刺。不然皮特森·莎希布肯定会抓住你,让你去捕野象——去追踪大象的足迹,成为丛林里的笨蛋。呸!可耻!滚开!”
小吐迈一字不说走开了,但他替卡拉·南格检查脚时把自己所有悲哀都告诉了他。“管它的,”小吐迈说,把卡拉·南格大右耳的边翻过来。“他们已把我的名字告诉了皮特森·莎希布,也许——也许——也许——谁知道呢?嗨!看我扯出了一根大刺!”
在随后的几天里,大家把象赶到一起,把刚捕到的野象在一些驯服的象中赶来赶去(以免他们在下山去平原的路上惹来太多麻烦),同时察看毯子、绳子和其他东西,它们在林中要么被磨损,要么丢失。
皮特森·莎希布骑着他聪明的母象普德米尼进来,他正结清山中其他营地的账款,因本季将结束;一个本地职员坐在树下一张桌旁,支付着赶象者们的工资。趁每个人领工资的时候,他又回去骑到大象身上,加入到将要启程的行列中。那些捕捉者、追猎者和负责拍打树丛(以惊动猎物)的人,他们长期生活在围场,在丛林里度过一年又一年,这时骑在属于皮特森·莎希布常备力量的大象上,或者靠着树,枪横跨胳膊,取笑就要离开的赶象者,见刚捉到的野象冲出行列跑开时哈哈地笑起来。
大吐迈向职员走过去,后面跟着小吐迈,负责跟踪野兽的头儿马楚亚·阿巴低声对一个朋友说,“不过捕象的人中至少走掉了一个好家伙。让那只丛林的小公鸡去平原上换毛真是可惜。”
瞧,皮特森·莎希布的耳朵非常尖;在一切活物中,野象算是最安静的了,而一个要倾听他们声音的人耳朵必须很灵敏才行。他躺在普德米尼的背上转过头问,“什么?在平原来的赶象者中,我还没听说有谁聪明得能够拴住一只死象的。”
“他不是一个男人,而是男孩。在上一次的围赶中他竟然冲进了围场,把绳子抛给巴毛,当时我们正想法捉住那只象仔——他肩上有块红斑,刚从母亲身边走开。”
马楚亚·阿巴指着小吐迈,皮特森看过去,小吐迈向他深深鞠躬。
“他抛出绳子?他比拴象的铁柱还小呢。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皮特森·莎希布问。
小吐迈害怕得说不出话,但卡拉·南格就在他身后,吐迈做了个手势,大象便勾起他身子,送到普德米尼的额前,正好在大皮特森·莎希布面前。这时小吐迈双手蒙住脸,因他还是个孩子,除了有关象的事外,他同任何孩子一样腼腆。
“啊!”皮特森·莎希布说,长着胡须的嘴发出微笑。“你干吗教你的象那种把戏?是为了在别人晒嫩玉米穗时从房顶上偷取吗?”
“没有嫩玉米穗,‘穷人的保护者’——有甜瓜,”小吐迈说,把所有坐在周围的人引得哈哈大笑。他们当中大多在做孩子时教过象这种把戏。小吐迈被悬在8英尺高的空中,他真希望钻入8英尺深的地下。
“他是吐迈,我儿子,莎希布,”大吐迈愁眉苦脸地说,“他是个非常糟糕的男孩,最终会进监狱的,莎希布。”
“这我倒不相信,”皮特森·莎希布说,“这么大的男孩就能面对一个大围场,怎么会进监狱呢。瞧,小家伙,这儿有4安娜拿去买糖果;你的头虽不大,头发却相当粗密。你最终也会成为一名猎手的。”大吐迈听后更加发愁。“不过你要记住,围场可不是小孩玩耍的好地方,”皮特森·莎希布继续道。
“我绝不能去那里吗,莎希布?”小吐迈喘着大气问。
“对。”皮特森·莎希布又面带微笑。“等你看见了大象跳舞去才合适。那时你就来找我吧,我会带你到所有的围场去。”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因为这是捕象者们的一个老玩笑,意思是绝不可能。森林中隐藏着一些被称为大象舞池的平坦空地,但也只偶尔被发现,谁也没真正见过大象跳舞。当一个赶象者吹嘘自己的本领和胆量时另一个赶象者就会说,“你什么时候见过大象跳舞了?”
卡拉·南格把小吐迈放下,他再次深深鞠躬,同父亲一起离开了,把4安娜银币给母亲,她正在给他的小弟弟喂奶;他们都被放到了卡拉·南格背上,一队呼噜尖叫的大象摇摆着沿山路向平原走去。由于都是刚捕到的野象,他们每遇到涉水的地方都很麻烦,需要时时哄、打,所以这样的行程算是挺不错的了。
大吐迈狠狠用棒推卡拉·南格,因他十分生气,但小吐迈却高兴得说不出话。皮特森·莎希布已注意到他并给了他钱,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士兵那样,被总司令从队伍中叫出来并受到赞扬。
“皮特森·莎希布说大象跳舞是啥意思?”他最后小声问母亲。
大吐迈听到他问就咕哝着说:“就是说在这些山里你永远当不了跟踪水牛的人。他就是这个意思。喂,你们前面的,为啥把路堵住了?”
在两三头象前面有一个阿莎麦斯的赶象者,他转过身气愤地叫道:“快把卡拉·南格带上来,把我这只小家伙教训教训,让他规矩点。干吗皮特森·莎希布要挑我与你们这些稻田里的笨蛋一起下去?把你那只兽弄过来,吐迈,让他用牙刺刺。上帝呀,幸好这些新捕的象发疯了,不然他们会嗅到丛林里同伴们的气味。”卡拉·南格去击打那只象的肋部,使之喘不过气来,这时大吐迈说:“在最后这次捕捉中我们已扫清了这些山中的野象。现在就是你不小心赶他们了。难道要我在整个路上维持好像队?”
“听他说的!”另一个赶象者说,“我们已扫清了山里所有的野象!嗬!嗬!你们这些平原的人真聪明。除了根本不懂丛林的糊涂脑袋外,任何人都会知道本季围赶大象的事结束啦。因此今晚所有的野象——干吗我要对牛弹琴呢?”
“他们要做什么?”小吐迈大声问。
“哦,小家伙。你在那儿吗?好吧,我告诉你,你的头还算冷静。他们要跳舞,你父亲——他已扫清了所有这些山里的象——今晚应该把象柱子好好用铁链拴牢。”
“这是什么话?”大吐迈说,“40年来,我们家中作父子的都在照管大象,还从没听说这种关于跳舞的胡扯呢。”
“不错,可一个住在棚屋里的平原人只知道他屋子的四墙。喂,今晚你就把大象的链子松开,看看会发生什么。至于他们跳舞的事,我见过那个地方——唉!这条‘迪汗河’有多少道弯呀?这里又是一个要涉水的地方,咱们得让象仔游过去。你们后面的静静呆着。”
一群队伍就这样谈论着、争辩着溅起水过了河,开始向着为新捕到的象准备的某种接待营地大步行进。可象还没到达那里早已发起脾气来了。
他们来到营地便把象的后腿拴在大柱上,对新捕的象还另外加固了绳子,并把饲料堆在他们面前。在下午的阳光下,山里的赶象者又回到皮特森·莎希布身边,告诉平原的赶象者们当晚要格外小心,听到他们问为什么时他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