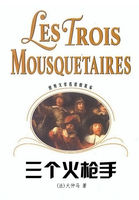那时还不是春天,还下着大雪。姆姆还怀着身孕,坐在门口见一个陌生男人走来。它想吠,但立刻被制止了。小点儿对姆姆打了个手势。她正巧出门刨雪,见他便问:“一清早你怎么找到这里了?!”兽医只是往她跟前走。
她一看见他,立刻在他脸上看出通宵失眠的痕迹。这种痕迹她和他都有,早就有。现在只是渐渐扩大、显著,形成了他们固定的面部特征。他眼神错乱,对她说:“她要死了。”
“就用这种恶毒的诅咒来骗我回去吗?”小点儿龇牙咧嘴,端正的鼻子通红。“你再跨一步,我就把全班人都喊醒,让她们打死你这流氓。”
他用同样的语气重复:“她要死了。”声音平板,连应有的音调都失去了。
小点儿渐渐从一只小兽还原成人:“你说什么,姑父。”
“她要死了。”兽医像生来只会说这一句话。直到她和他双双骑马奔到病人床前,他还怕她不懂似的,指着快咽气的女人说:“她要死了。”她要死了,她终于要死了。他之所以一遍遍重复这句话、这个念头,是因为他如愿以偿又罪有应得。他对此时此刻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恐惧,有多深的欣慰就有多深的痛悔。始终不渝爱他的好妻子这回真要离他而去了,把他撇给这个卑劣的小女子。她每次在昏迷的间歇中,总向他投来一切都明了一切都谅解的目光。他在那目光中跪下了:他的心跪下了。
她拉着侄女汗涔涔的手,把她向怀里拉,似乎硬要把她和罪证拉到一起。垂死的女人再也说不出话来,但他俩懂了她游丝样的声音在空荡的屋里缭绕:你们的丑事可怎么结呢?你们这样胡闹可怎么了呢?你坑了她,她好歹是个女娃,终要嫁人。你也坑了他,没有你,他品行上是没有疵点的。好啦,不说啦。我晓得你们也苦也难。你们冒死偷欢,那滋味好得了吗……
兽医这时用极平静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不放心我和小点儿。我会好生待她,她也会好生待我。”
这男人公然逼她表态。他想要垂死的女人对他们的关系认可。他只需这个女人来裁判他们的关系,只要她首肯,他们无法无天的关系便合法了。而她半合上眼,再次昏迷过去。
“姑父,快送姑去医院,你去场部要辆吉普车来。你去吧,我得守她。不能再耽误了,要马上送医院急救!你怎么还不去?!”
两人争执着,然后动手拉扯起来。兽医向门口迈几步,又退回来。小点儿去抓那个单线电话,它一向打不通,形同虚设。两人终于不再忙乱,很默契地守着心里不可告人的夙愿。他们并肩而立,等天一点点黑下去。
到天黑时,女人忽然有了几声强劲的呼吸。他们两人感到害怕,似乎她只是从一次镇痛剂的昏睡中觉醒,如平常每日重复多次的觉醒。她活转过来了。兽医感到小点儿的手碰到了他的手,他便紧紧将它握住。在这种时候,他们只有结盟,狼狈为奸,才能抵抗这个突然复活的女人。
过一会儿,她呼吸减弱下去,看来她一点一点对他俩撒开了手。他俩谁也不提议开灯,就像谁也不提议抢救她。这个唯一的见证人死了,唯一的罪责消除了。在这时再开灯,他们好堂而皇之地为她收尸。
一支二十瓦的日光灯照着死者。他俩看了她一会儿,突然对看起来。小点儿猛地跳开:“你害死了她!你见死不救!”
兽医用同样无辜的表情说:“你害死了她!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本来她还有救的,起码能多活几天!是你装聋作哑等她死!小点儿以性命作武器,朝兽医冲去。
他也想就此把命拿出来,拼掉算了。他们打,扭绞,她咬他。他与她都以泪洗面。他们以大量的泪水浇灌在他们久旱枯死的良知上。死去的女人用超脱的目光看着他们打作一团。好吧,你们自相残杀吧。只有你们自己才知道该受多重的惩罚。你们彼此严惩,这再合适不过了。谁也代替不了你们自己,来当你们的打手。
“自杀吧。”兽医从小点儿咬紧的齿缝里拔出变形变色的手指。
她点点头。自杀是一切英勇的废物们最拿手的一招,他们被动了一辈子,只争取到唯一一次主动权,那就是自作主张地把自己处理掉,就像这个善良软弱的女人。“难道到了阴间,咱们三个自杀的人还要纠缠在一块,过这种不明不白不清不爽的日子?难道你到了冥界还要一人独霸两个女人?难道这三个人肉麻的乱七八糟的辈分、天伦、感情关系还要一直拖到那个世界……?”
“你的意思是说,不死?你想跟我活着?”
“不,我活我的。你随便怎样都行,你愿陪姑姑就去吧。你一头撞进骨灰盒也行,我认为那样也不错。”
“我撞死,你留下?”
“我是说,我不管。你随便就是了。”
“就像这样挖个坑,把我的骨灰也埋进去?你的主意真不错。这下再也没人知道这段罪孽了。你也像这样在土上踩一踩,踩实了,把脚印用手抹掉,一点痕迹都不留。你不用往雪里点葵花子,明知它活不了。装得多像,多像个真的悲悼者!多像个守丧的晚辈!你这小骗子!”
“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把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你,你连我身上一共有几个痦子都清楚。你不用担心,这些花会活。春天你等着瞧吧!”
参加送葬的十几个老垦荒队员全散了,他和她才慢慢抬起头。
二十瓦的日光灯照着这个奇形怪状的房间,从墙至屋顶都是牲畜器官的剖面,所有内脏拥挤在空间内,没有一丝缝隙。那些褪了色的、已腐败的脏器早已为这屋里的人司空见惯,而此刻,今夜,它们突然这样新鲜逼真。整个屋子都在蠕动,所有脏器都各干各的。
活着的人看着死去的人,才发现死去的人多么好、多么静。一切矛盾都和谐了,一切缺陷都完善了,一切器官都不再嘈嘈切切地开动,不再生出要求、欲望、花招、心计,以至于不再吵闹自己,烦扰别人。她把总闸关了,所有的嘈杂归于宁静,然后她弃舍这一整套停工的设施。她离开了。他们亲眼见她悄悄走出窗口,从此去云游自由的原野。自杀吧,活着的人在这一刻开了窍,在死者飘然离去的眼神中,他们体会到她的幸福。
她还没咽气时,她用最后的气力除去口罩。被口罩捂住的皮肤鲜嫩洁白,酷似婴儿;而常裸的上半张脸又黑又皱。一副面容如此割据,既滑稽又可怕。她的目光越来越柔顺。没有开灯,但暮色反使一切都真实而逼近。他俩眼看着死亡怎样一点一点将那难看的肉体吞掉,将那美好的灵魂驱走。他们想,这就对了,丑与美合而为一的生命是个矛盾,正是这不可调和的矛盾要对她的死负责。
牧马班的姑娘们见办完姑母丧事的小点儿回来了。远远看去,她银灰的脸失却了往日的光亮,她镀了层铅。她面颊留下两条蜿蜒的曲线,那是泪水冲出的沟渠。大家小声地问长问短,表示尊重她的悲痛。
她们连红马失踪这样重大的事也没及时告诉她。老杜刚对她嚷了声:“红马……”柯丹顺手给她一巴掌。她们相信她的悲痛太沉重了,不能再有任何复加的压力。她们把嚷惯的大嗓门全都压低,对她进行着牛头不对马嘴的安慰。
小点儿的心绪复杂到何等程度,她们就是将一辈子的生活经验相加,也无法测量。小点儿突然感到自己在这几天里似乎想念过她们。在姑家暖和但畸形的屋子里,她真切地想念过这顶又薄又冷的帐篷。那是丧事就绪的当天晚上,她依偎在兽医怀里,一股猛烈的思念涌上来。她想到她们的出牧、吃喝、睡觉,没有一件事是多余的。对这种简单明朗的生活怀念,使她推开了他。他把炉火烧得那么旺,她却宁可到外间去挨冻。她闩上门插,任他把门搞得山摇地动。而在这之前,她想念过谁?父母兄弟?情人?都没有。现在她坐在她们中间,对当时那股油然而生的思念诧异极了。就想这一切吗?出牧、吃喝、睡觉?有了点矛盾就大声读语录,直读到声音整齐刻板平和。她明知道这一切没什么值得怀念,而偏偏怀念的就是这一切。
那还是冬宰之后,草地刚变成雪原,毛娅被逐步升级的讲用会送到总场、自治州。这期间有个男知青常来帮她修改讲用稿,他也是先进知青讲用会的代表。有天他把改好的稿子交给她时,附了封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看开头这两句伟大的诗,她立刻明白了信的属性。因为知青中凡写情书,一律用这两句诗开篇。然后他和她握了握手,表示盟誓。
她将这事如实汇报给指导员叔叔。叔叔的学习班恰巧离她住处不远。他听她尖声尖气地说完,又问:“你跟他咋个整的?”
她说,只不过握了个手。毛娅将男知青傻话连篇的情书递给叔叔,他却仰着脸,一口气将它撕得粉粉碎。他不识几个字,也不信这一套。他认为一男一女住一条走廊,天天见时时见,绝不会用笔用纸来干这件事。他不理毛娅的辩解,从随身背的军用水壶里倒出酒来喝。毛娅见他喝酒,立刻取下辫梢上的橡皮筋,又很快为他弄到一小碟豆瓣酱。
女子牧马班的姑娘都熟悉他这奇怪的习惯。从第一次看见他喝酒,就津津有味吱吱作响地嚼什么,吐出来一看,是女孩们扎头的橡皮筋。他把橡皮筋放在血汪汪的辣豆瓣里蘸蘸,然后搁进嘴里嚼。起初以为他嚼它是因为没有任何下酒菜的缘故,后来发现有肉有菜他也嚼它。每个姑娘辫子上的橡皮筋都被他嚼过,他嚼得那么响。咯吱咯吱,开始她们不敢听,后来听顺耳了,只要叔叔摘下酒壶,马上有姑娘解下橡皮筋递上去,然后披头散发微笑着听那咯吱声。他嚼得香喷喷又恶狠狠,末了,吮干净上面暗红的酱汁,它还是根完好的橡皮筋。有次帐篷里马灯没油了,叔叔摸黑喝酒,吱吱地嚼一会儿,便说:“老杜你这根是新的。”她们奇怪地想,伸手不见五指他却嚼得出老杜的味。
毛娅披散头发等他喝完酒。他一只假眼盯着她的脸,真眼却浏览她的全身。
“那个小驴日的,就把你整上手了?”
“指导员!就不过……”
“去!他就这样整上你了?”叔叔站起来,毛娅开始往墙角退。他想,他该早预料到这点:男女知青在一起开会,开会!非开到一块去不可。“男女知青在一块开会,恐怕要开出小知青来。”他低沉地说。
毛娅觉得叔叔的手在咔咔响,犹如春夜竹笋拔节。“你侮辱人!”她再无退路,顺势一坐。她恍惚觉得坐错了地方,却又纳闷怎么会坐得如此稳当舒适,整个身心都因这一坐而暖洋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