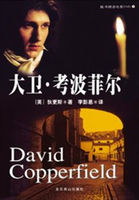到了火车站,凌戈的脑海里还在不断闪现苏志文在雨中一边流泪一边蹒跚行走的情景,不过是次争吵,至于伤心欲绝吗?都三十八岁了,还像个小男孩那样趴在老太太腿上哭,并为此提出离婚,真是不可思议。凌戈虽然心里很同情他,但还是觉得有点别扭。苏志文也太没男子气概了。但是试想,如果有个男人趴在她腿上哭,还是个那么英俊的男人,她大概也会缴械的吧,因为女人就是心软。
有一次,简东平也趴在她腿上,不过不是哭,而是大笑,因为她给他看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你以前原来是这样的,好胖啊,像个小肉圆。哈哈,肉圆,肉圆。”他一边说一边大笑。她当时真想揍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像小孩子一样趴在她腿上哈哈大笑,她又心软了,她最后只是拉了拉他的头发叫他滚起来。所以,虽然沈老太太年纪大了,但她毕竟是女人,看到她的小丈夫伤心成那样,一定非常心疼。凌戈总觉得沈老太太对苏志文的态度,像妈妈对儿子。
她很想立刻把这件事告诉简东平,但一想到他前一天对自己的戏弄和他两年来对她的冷嘲热讽,她就觉得非常难受,所以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放弃了。
节省电话费!跟你这大冰箱说话,就是要节省电话费,因为我不想花了钱还受气,我是个现实的人!凌戈对自己说。
256,火车站到底有没有跟这个数字有关的小旅馆呢?她已经把所有分布在火车站附近小旅馆的名字都记录在她的小本子上了,一共是67家。真够多的,因为有些旅馆搬家了,有些又更名了,所以到现在她才跑了一半,还有34家没跑。这34家都分布在火车站的外围。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周瑾的行李。其实即使真的找到周瑾的行李,凌戈也开心不起来,因为这就意味着周瑾很可能已经出事了。想到这里,她的心咯噔一下往下沉。
两个小时后,她在火车站外围的马路上走了好大一圈,并没有找到跟那两个数字有关的旅馆,她沮丧地用铅笔划掉她刚刚跑过的10家旅馆。看看腕上的手表,快十二点了,今天早饭吃的是章玉芬做的玉米粥和薄煎饼,在饭桌上她没敢多吃,所以早就饿了,她决定去便利店买个肉松面包充饥。一个人的午饭就是好对付。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林仲杰打来的。
“小戈,你在哪里?”林仲杰的声音永远让凌戈犯怵,虽然她从小就认识他。林仲杰是凌戈父亲的老朋友。
“我,我在火车站,简东平让我帮他拿点东西。”她心里有些愧疚,因为不得不对尊敬的林叔叔撒谎,简东平曾关照她不要把调查周瑾行踪的事向外人透露。
“你这丫头真老实,怎么老被他指挥。”林仲杰叹了口气,问道,“你昨天住在那里有什么收获?”
凌戈把前一天跟简东平说过的情况,省去麻将和鱼翅,又跟林仲杰说了一遍。她没有把苏志文跟方琪的事说出来,她准备先告诉简东平后再作定论,虽然很生他的气,但不知道为什么,她还是习惯听他的话,想想就窝囊。
“凌戈,辛苦你了。”林仲杰道。
听出林仲杰打算挂电话,凌戈忽然想起简东平提过的事。
“林叔叔!不,林伯伯!”她叫道。
“嗯?”
“我看了口供资料,我发现,里面有个问题。”她咽了一口唾沫,鼓足勇气说。
“哦,什么问题?”
“方晓曦说,她曾经在储藏室看见过一个竹编小箱子,但是后来现场勘查里没提到这个箱子。我觉得,”凌戈尽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成熟冷静,她放慢语速说,“应该问沈碧云要几个月前储藏室的清单核对一下。”
“小戈,不错啊,终于开窍啦!哈哈!”听了她的话,一贯严肃的林仲杰笑出声来。
难得在工作中受到夸奖,凌戈开心得脸都涨红了,瞬间对简东平涌出一大堆感激。是啊,虽然他嘴巴坏,爱讽刺人,但出的主意倒都是好主意,每次都能帮到她。
“林叔叔你也想到了?”
“是啊,我已经向沈碧云要了。嗯,小戈,不错,继续努力。对了,别忘了把检查写得深刻点,上次那份实在太短,我是无所谓,但交上去不行啊。”林仲杰笑道。
“林叔叔,你放心吧,这次的检查是简东平帮我修改过的,有一千五百多字呢,写得可好了,谁看了都会感动。”凌戈想到简东平曾经深夜替她赶工,写完了那份检查,骤然就原谅了他对她的刺伤。
“看来他对你还不错啊。”林仲杰笑道,“小戈,昨天还有人问我你有没有对象呢,你要跟简东平说说这事,别让那小子自我感觉太好了。”
“我知道了。”凌戈甜甜地笑着挂了电话,心里琢磨不知道是谁在打听她的事,会不会是给她吃话梅的小郑?
她走进便利店,买了一个肉松面包、一根热气腾腾的台湾香肠和两串香菇贡丸。以前她不舍得在便利店里买热食吃,觉得太贵,但今天心情好外加肚子饿,干脆吃个痛快。她在便利店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她的午餐,正准备离开,忽然想到便利店的营业员也许会知道这附近的旅馆信息,不妨问问。
“小姐,请问这里有没有256旅馆?”她索性把数字嵌在了旅馆的前面。
营业员正忙着,头也不抬地说:“256旅馆是没有,不过256饭店就在前面。”
凌戈脑门一亮。
“前面?在哪儿啊?”她东张西望,急急地问道。
“外面外面,墙上写着,自己去看。”营业员不耐烦地用下巴往外店门外一指。
凌戈走出便利店,很快在便利店旁边的一堵灰墙上看到一行歪歪扭扭,用红色颜料写的大字,“此巷256号,胜利饭店,住宿吃饭,往前走。”这行字前面还加了一个红色的大箭头。可能是为了让住宿者看清楚门牌号,这行字中“256”那个数字写得特别大。凌戈走了一段后发现这个广告至少重复了三遍,而且后面省去了饭店的名字,直接写成“此巷256号,住宿吃饭。”256出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凌戈不知道那家旅馆是否就是她要找的,但她决定试试。
“你想打听我姐姐什么事?”她问。声音清脆,普通话极其标准。
简东平注视着面前的女孩,五官跟周瑾长得很像,却不及周瑾一半漂亮。气质显得文静一些,那多半因为她戴了副眼镜的关系。她是周瑾的妹妹周兰,目前在小镇上的中学担任实习老师。简东平通过凌戈提供的档案资料先找到了周瑾的家,随后从邻居嘴里知道了周兰所在的学校。
他的到来令她颇为惊讶,但她还是爽快地接受了简东平的邀请。他们约好在茶坊见面。
“我是你姐姐的朋友,你姐姐好像失踪了,我正在找她。”简东平开门见山地说。
“她出事了?”周兰紧张地问道。
“没有,没有。”简东平忙说。
周兰的表情立刻松弛下来。
“我也有一段时间没跟姐姐联系了。”她推了推眼镜说。
“你最后一次跟她联系是在什么时候?”简东平见周兰脸上露出警觉的神色,马上又补充道,“你姐姐从今年三月起一直在给我们报社的旅游版写专栏,她本来答应五月长假后交稿的,但长假过后,她没有交稿,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任何消息,无论怎么都联系不到她。”
周兰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简编辑?!”她兴奋地指着他问道。
“周琴向你提起过我?”
“她说跟他联系的是个很文雅的年轻编辑,她本来以为杂志社的编辑都是老头,所以看见年轻人特别兴奋。”周兰笑着点头,“我姐姐一定也对你表示过好感吧。”
简东平笑而不答,他还真不好回答这问题。
“别误会,我姐姐没别的意思,她只是常把喜欢说成爱。但当她真的爱上谁,她就会说那是喜欢不是爱。这就是她。她跟别人不一样。”周兰语调柔和地说,嘴角微微漾起笑容,简东平发现她们姐妹俩的感情很好。这种好,不仅仅是单纯的血肉亲情,还包含了朋友之间的理解和欣赏,跟尔虞我诈的沈家姐妹相比,周氏姐妹的感情让人觉得温暖。
“你看过她写的文章吗?”简东平问。
“她把你们报社的网址给过我,我看过我姐的文章,电子版的。”
“有什么感想?”
周兰望着面前的奶茶,轻轻叹了口气:“这些年她在外面漂泊,经历了很多。”
“我有一次听她说,她是做了一件错事才离家出走的,她放火烧了房子。”简东平平静地注视着周兰,看见周兰眼镜片后闪过一道惊异的目光。
“她跟你说过这事?”
“对啊,不过没说理由。”简东平用轻松的语调问道,“她为什么烧房子?”
周兰沉默片刻后才开口。
“既然她连这事也告诉你了,说明她真的把你当朋友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我也不瞒你了,”周兰的声音暗哑下来,“因为我母亲到学校去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姐的事都说开了,我姐姐觉得再也没脸上学,所以偷了家里的钱离家出走,烧房子是为了报复我父母。”她抬起头,犹豫了一下,“不知道她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们两个跟父母的关系都很不好。他们并不是坏人,但也许他们这辈人都是这样,奉行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
“她跟我说起过。她说你父亲,很喜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
周兰笑了出来。
“是啊,他那时候老说,铁就是要不断打才能变成钢。”周兰温和地说,“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患了严重的肾病,腿肿得很厉害,再也打不动人了。他现在有时候也会想起姐姐,所以我说他不是坏人,只是教育方式不对。”
“你父母是不是还报了警?我委托朋友打听周琴家乡的时候,无意中查到了一条报警记录。”
“那是我妈去报的警,事后我爸把她打了一顿。我妈的个性有时候比我爸还要倔。”周兰苦笑道,“后来我姐寄钱回来过,大概前后共寄了三千块吧,其实她烧掉的那些东西根本要不了那么些钱,我妈收到钱后就不再说什么了。她去年春节还盼着我姐姐回来过年呢,你看年纪大了,想法也都变了。”
“你最后一次跟她联系是什么时候?”简东平适时把这问题拿了出来。
“是5月6日。”周兰口齿很清晰。
“是她打给你的吗?”
“不,是我打给她的。我爸的身体越来越差,我想让她有空回来看看。其实春节的时候我也跟她提过,但我姐这人很记仇,她一直不肯原谅我爸妈。虽然嘴上说,好的,我有空回来。但六年了,她一次也没回来过。不过,这次她好像跟前几次有些不一样了。”
“她准备回来了?”简东平连忙问道。
“她说她已经买好了7号回家的火车票。”周兰说到这儿,露出无奈的笑容,“可没想到她又食言了。幸好我没把这消息告诉我爸妈,不然他们一定很失望。”
也许周琴这次并没有撒谎,简东平想,难道所谓的去广州只是一个幌子?
“你后来还跟她联系过吗?”
“9号我给她打过电话,但她的手机关机了。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上她。”周兰说。简东平没从她的语气中听出担心和困扰,也许她对周瑾像这样一声不响地失踪已经习以为常了。
“你那天给她打电话,她还说了什么?”
周兰想了想。
“她说她现在很幸福,很开心。”周兰目光柔和地说。
“她有没有说,什么事让她觉得幸福?”
“她说等回来以后再跟我细说。对了,她还问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说还早呢,要到国庆节。她说她这次回家会把礼金先带回来。”周兰温柔地微笑着,但简东平还是从她的话里听出了一丝失望。
“周琴曾经跟我提说起过一个男人,好像这男人骗了她,你知道这件事吗?”他转换了话题。
“当然知道,”周兰把头一歪,撇了撇嘴说,“我姐姐就是被那个男人害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事情很简单,那个男人是赌徒兼骗子,我姐姐为了讨好他,从家里偷了五千块钱给他还赌债,他拿了钱一分没还就逃走了。结果我姐姐被对方抓个正着,最后被那个赌场老板卖到发廊去当小姐。幸亏我姐姐机灵,趁他们不注意逃出去报了警。回来后,她本来想重新开始生活的,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地方的人都很保守,她出事的地方又是在镇中心,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她。因为丢了五千块钱,我妈后来又去学校骂她。对我们这种不富裕的家庭来说,五千块的确不是个小数目。虽然我妈做得过分了一点,不过后来想想也可以理解。”周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
“我姐觉得在家乡再也待不下去了。她说她想去找那个男的算账。那个男人好像对她说过自己的计划。我姐信以为真,就拿了张地图去找他。”周兰忽然想到了什么,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来,递到简东平的面前。“你看,这就是骗我姐姐的那个男人,倒是长得一表人才。我姐姐说,为他死都甘心。”
简东平一眼就认出照片上的男人正是六年前的苏志文,身材瘦长的他穿了件蓝衬衫,斜靠在门栏上,眼神温柔地注视着镜头,脸上挂着慵懒的微笑。
“这照片是谁拍的?”简东平忍不住问道。
“是我姐姐。他送了台照相机给我姐姐,还教会了她拍照。”周兰端详着照片中的苏志文满怀感慨地说,“我姐姐拍了他很多照片,那时候她每天拿着这些照片哭啊哭的,哭得人好揪心。”
“很奇怪,这男人既然有心骗你姐姐,为什么还让她拍下自己的照片,他难道不怕日后她报警或者找到他?”
周兰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姐姐说,那个男人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对她很好,百依百顺的。她没想到他会突然走掉。所以她可能也想找到他问个明白。”周兰拿起照片抖了抖,“她给了我这张照片,为的就是让我记住这人的长相,如果哪天他再出现在镇上,让我马上通知她。”
“那她有没有找到这个男的?”
“她没说,我后来也没敢问了。我怕提这事让她伤心。我姐姐这几年过得很苦,她以前一直想上大学,想到大城市去生活,想嫁个好男人,过上好日子,可是后来……”周兰说到这儿眼圈红了,她没再说下去。
简东平禁不住想起《我的荒谬旅程》中的段落。
他不停地吻我,每说一句话就要吻一次,所以我们说话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等一句话说了三遍后,他就笑了,笑得像阳光下的溪水清澈明亮。
我说我从来没跟男人在一起过,他又吻了我,然后轻轻地在我耳边说了声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我喜欢你。他又笑了,对我说,不要随便对男人说喜欢或爱,那样你会被看轻的。我问他,你会看轻我吗?他说,在我的眼里,你很轻很轻。接着,他把我抱起来,让我坐在腿上。他把头埋在我胸前,说着话,我听不清他说什么,只觉得身体飘了起来。
他没有定性,有时候,他欲望很强烈,从早到晚,总是要啊要啊,像疯了一样。有时候他却毫无兴致,什么都不想干,连别人不小心碰到他一下,他都会感到厌烦。滚开,滚开,他会这样吼叫,但从不打人。
有时候,他很没耐心,一支烟抽了一口就扔掉了,一碗饭吃了一勺就不吃了,一本书看了两页随手扔了。但有时候,他却比女人还细心。第一夜起来,他给我洗澡,洗头,还为我吹干了头发。然后他笑嘻嘻地摸着我柔顺的头发说,小姑娘,你喜欢我吗?你会永远喜欢我吗?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你看我时很远,看云时很近。这是他喜欢的诗,我后来知道这是一个叫顾城的人写的。
你会写诗吗?我问他。
不会。他说。口气好冷淡。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信手写出几句话却让我心动。
“记得吗,很久以前,
你曾以冰冷的小刀,
刺一朵淡青的荷花在我的背脊。
那个夜里,我的痛楚
你的心事,是我难以磨灭的纹身。”
可惜,我只记得这几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