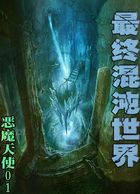公元399年(隆安三年),东晋僧人法显从长安出发,走西域道抵五天竺。他在巡礼了北、西、中、东天竺、师子国、随商舶东归,经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于412年(义熙八年)在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崂山县东)登陆返国。后将其求法经历于414年(义熙十年)写成《佛国记》一书。该书对其陆地行程、天竺、师子国等地的佛教盛况记叙详细,而特别是南海归航经过,描绘的栩栩如生。展现出了5世纪初印度洋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13个日夜的大风暴、海洋动物、商舶、海盗等。当时从师子国到耶婆提国有90天的航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远洋航行的纪实性文献,对探讨4世纪与5世纪初的北印度洋航线有着不容忍视的重大价值。
公元671年(咸亨二年)11月,唐代僧人义净从广州起程,搭波斯商舶,经过今天的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尼科巴群岛,于673年(咸亨四年)到达耽摩立底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南塔姆卢克一带),踏上了佛国圣地。在印度半岛,他瞻仰佛迹,留学那烂陀寺,又在当时佛法兴盛的室利佛逝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东南)逗留了10年,并写出《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两书。再循海路东归,于695年(天圣元年)返国,抵洛阳。
义净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其后一部主要讲述当时印度、南海佛教流行的律仪。而前一部是记载从唐初到义净抵印度时的60余位僧人的事迹。书中详细的记叙了僧人们经南海、印度洋的航线,以及涉及的国家、地区的实况。特别要指出的是有关裸人国(今印度洋尼科巴群岛)的记述,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有关该岛的最早文字记录。7世纪的印度洋已成了佛教交往的桥梁,全书所记61位僧人之中的52位是从海路赴印度的。僧人搭商舶往返,与商人结伴同行,在征服印度洋的惊涛骇浪中留下了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民族精神,当是中国人驾驭印度洋的又一个侧面。
公元674-675年(上元一至二年),唐人达奚弘通曾横渡印度洋。他写下《海南诸蕃行记》一卷,原书早已失存。在《玉海》卷16引《中兴书目》中曾提到,自赤土(今马来半岛西吉打南部)到虔那(今阿拉伯半岛南部之BandarhisnGhorah),经36国。除了起、终这两个地方外,其他34个国家今天都不可考。另外。在《新唐书·艺文志》里也列出此书名,可知,确有其人。
公元572年(天宝十年),唐与东来的大食势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有过一次战斗。唐军败北,随高仙芝西征的杜环被俘,后跟着大食军西行,遍历阿拉伯各地,在那边留居了8年,还从西亚到过北非。762(宝应元年)年,他搭波斯人商舶,出红海由印度洋返回广州。归国后,他把遍历各地及归途的见闻写成《经行记》一书。原书已失传。今天,只能从《通典》中保存的1511个字中见其端倪。幸赖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了张一纯的《经行记笺注》一书。该书虽是残卷,仍不失为中国人参与印度洋活动的信史。
公元1330-1334年(至顺元年至元统二年),1337-1339年(至元三至五年),在此期间,元朝人汪大渊两次浮海。航行所到,前一次,以印度洋区域为主,后一次只在南洋一带。他将出航的纪实,在第一次返航后写出“五年旧志”,第二次归来,将其充实,于1349年(至正九年)成书《岛夷志略》。该书为研究14世纪的印度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全书不分卷,列出100条,其中99条是作者本人亲身访问过的地方。首先,这部书的实践性与科学性不容否论,晚一个世纪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从自身亲历在所着《瀛涯胜览》的“序言”中对该书作了肯定,“知《岛夷志》所着不诬”。其次,该书各条目所记山川形势,民情风俗,使14世纪南海、印度洋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则,汪大渊笔下为我们展现出的印度洋上贸易的班阑景观,堪称不可多得。容后详述。
三、在印度洋上的活动
15世纪前,浩瀚的印度洋既是国家间建立友好关系的通道,也是僧人弘扬佛教思想的桥梁,更是日益繁荣的商业贸易场所。
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奔波于印度洋上的中外使臣络绎不绝,在此,仅就汉朝、元朝作简略阐述。
位于印度半岛东部的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公元2年(元始二年),黄支国还赠送汉朝犀牛一头。犀牛是较大的动物实体,只有先海路运输而后转陆路,才能到达长安。这成了汉朝轰动一时的佳话,在班固的《两都赋》中就提到了犀牛饲养在皇帝的私人花园中。公元159年(延熹二年),161年(延熹四年),天竺国经日南送方物到东汉朝。这是非常明确的由海路,经印度洋而抵中国。古代中外使臣跨越印度洋是来日方长的。时至千年以后的元朝,列于史册的有些着名的外交家,如畏吾几人亦黑迷失于1272年(至元九年),1275年(至元十二年)两次受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八罗孛国(今印度西海岸马拉巴尔一带),后该国国师与迷失同入元,并以“名药来献”。迷失于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又出使僧伽剌(今斯里兰卡),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再度受命西航,出使马八儿国(今印度西南巴拉巴尔海岸一带)。他的这几次出访扩大了中国人在印度的影响。还要提到的是广东招讨使杨庭壁,受元廷派遣先后于1279年(至元十六年),1280年(至元十七年)、1281年(至元十八年)、1283年(至元二十年)四次出使俱兰(今印度西海岸的奎隆)。由于元使多次出访俱兰,致使元朝国威跨越了印度洋,故而在元朝建立的前15年中,印度半岛的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国家马八儿、须门那(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苏姆那)、僧急里(今印度西岸柯钦北面的克朗加诺尔)、来来(今印度古吉拉特邦马希河与基姆河之间一带地方)等不断遣使泛舶印度洋送物来华,与元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印度洋上漂流着使臣的足迹,还传颂着僧人的情操。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中国僧人把去西天求法作为最高理想,起先,他们涉沙漠、翻雪山,不辞千辛万苦,走陆路西域道,抵佛国。而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又由于西域道上政治形势的变化,故而前赴后继的中国僧人大多循海道,上面所介绍的义净着述已有交代。这种情况一直到10世纪,因为佛教在本土的衰微而少见汉文史籍的载录。这里,将要把在茫茫无边的大洋中,许多中国僧人谱写可歌可泣的事件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是义净笔下的常憨。
常憨实现了他的夙愿,踏上了去佛国的海路征程。他先到诃陵国(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尔后由此国附舶至末罗瑜国(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占碑一带),再由末罗瑜到中天竺。不幸的是,起航不久,遇上风浪。因为商舶载物量过渡,舶渐下沉。在这危急关头,人们争先恐后,逃生于小船。舶主可能是信佛者,对着常憨高喊“师来上舶”。常憨答:“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菩提心,忘己济人,斯大士行。”说毕,面向西方合掌,口念“阿弥陀佛”,舶沉身没,言尽而终。时年50岁。他还有一个弟子,受其感到,号眺悲泣,也是在口念西方中,与舶俱没。
常憨的事迹,在当时的生还者中得到广泛的流传。这种忘己济人,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的高贵品格、德性,固然有普度众生的佛教信念,然仍不失为我们民族精神“舍己为人”的固有情操。他的事迹与印度洋水长流千古。
印度洋上活动的重要角色当是商人。商业贸易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依赖手段。使臣僧人虽是随商舶往返,商业贸易当是主要内容。印度洋既然是世界上最早的海运中心,中国人参与印度洋贸易,有明确记载的是公元前2世纪,“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壁流璃、奇石巽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到了410年(义熙六年),法显在师子国无畏山精舍佛殿拜霭时,见到一“晋地白绢扇”供奉在玉佛像前。这里,不管供奉者是谁,它都说明了中国的商品已跨越印度洋来到师子国,5世纪时师子国已有直通中国的船舶,公元429年(元嘉六年),433年(元嘉十年),西域舶主竺难提两次载师子国比丘到南朝宋的首都建康。这说明了在当时的印度洋上,师子国舶已是一支较活跃的商队。到了9世纪初,唐人对师子国舶具体描写如下“南海舶,外国船也。可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而韩愈在公元823年(长庆三年)写的“送郑尚书权赴南海”诗文“番禺军府威,欲说暂停杯,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衙时龙户集,上日马人来。风静爰居去,官廉蚌蛤回。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事事皆殊异,无嫌屈人才”。不仅提供出广州作为唐朝国际贸易港口的兴旺发达景象。而“货通师子国”又明确指出了唐代商品已直达印度洋中的岛国。印度洋上日益频繁的商品贸易,到了13世纪,中国人还在今天印度泰米尔纳得邦东岸的坦焦尔东约48英里的讷加帕塔姆建造一座土塔,“木石围绕,有土砖甃塔,高数丈。汉字云咸淳三年毕工。传闻中国之人其年旅彼,为书于石以刻之,至今不磨灭焉”。咸淳三年即1267年。讷加帕塔姆是中世纪印度半岛上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大港,在此处建立一个中国塔,说明到印度半岛的中国商人之多,在异国他乡书写汉文,既表达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怀念,也反映出印度洋贸易中,中国人参与的程度。
以下,将集中交代汪大渊描绘的14世纪印度洋上的贸易情况。从他的笔下,首先看到了印度洋上交易的商品琳琅满目:如印度洋半岛出产各式各样的布,有明加剌的芯布,高你布,八丹布、大八丹土塔的棉布,马八屿的细布,巴南巴西的细棉布,放拜的绝细布匹、大乌爹的布匹、须文那的丝布等。这些布匹都是参与印度洋贸易的输出品,当时东非沿岸的居民们“穿五色绢缎衫,以朋加剌布为独幅裙系之”。除布匹外,出产在八都马(今缅甸莫塔马一带)淡邈(今缅甸土瓦)、故临、下里、东淡邈、须文那、甘埋里等地的胡椒也是印度洋区域的大宗输出商品。还有,僧伽剌的猫儿睛、大乌爹的鸦鹘石,大食的乳香和没药、曼陀郎的犀角、层摇罗的象齿等。这些,都是带有地区特点的传统商品。至于中国人也是用传统商品以丝绸和瓷器为主参与印度洋的贸易:有五色缎、南北丝、白丝、五色绢缎、青缎、五色紬缎、苏杭色缎、锦缎、诸色缎、苏杭五色缎、土绢、五色绢、青白花瓷、青白花碗、青瓷器、青白花器、瓷瓶、青白瓷等。之外,还有金、银、铁等中国商品。从上面列出的丝绸和瓷器名称,不难看出其销售量大,受到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喜爱。
既然有兴旺的商品贸易,当会有货币流通和税收。从汪大渊的笔下了解到一些有关的情况,如朋加剌“国铸银钱,名唐加,每个二钱八分重,流通使用”。天竺“民间以金钱流通使用”。北溜(今马尔代夫)“以权钱用”。一个朋加剌的银钱可换11520余个子。“将一舶子下乌爹(一说今印度奥里萨邦东北,一说缅甸教固一带)、朋加剌,必互易米一船有余”。这里要特别提出,元代中统钞在印度洋地区可以流通,其兑换率是“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一十两,易子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有余,折钱使用”。至于税收,朋加剌“官税以十分取其二焉”,乌爹“税收十分之一也”。而产蚌珠最富的第三港(今印度南部马纳尔湾沿岸),将珠人所得“于十分中,官抽一半,以五分与舟人均分”。中国商人在沙里八丹用高价购买第三港所产珍珠,“珍珠由第三港来,皆物之所自产也。其地彩珠,官抽毕,皆以小舟渡此国互易,富者以金银用低价塌之。舶至,求售于唐人,其利岂浅鲜哉?”从元钞的兑换通行和购买昂贵的珍珠,显示出远在14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在南海、印度洋的贸易中有丰富的商品和充足的资金。
最后,还要介绍汪大渊笔下的两个负面,一是海盗的猖獗,一是非洲的幼童被贩卖。在龙门牙(今新加坡)条记述到,从印度洋返回的船舶往往在这儿丰富的商品和充足的资金。遭海盗窃掠,其“贼舟二三百只”,说明海盗已成团伙。这反面衬托出南海、印度洋贸易的发达。在加里门将(今非洲东海岸)条中,有“当地丛杂回人,其土商海兴贩黑囡住朋加剌。互用银钱之多寡,随其大小高下而议价”。这非常清楚的说明了东非的黑人幼童被卖到印度半岛东岸。这与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所载相一致,其中称朋加剌是当时阉人与奴隶的市场。这当然是印度洋贸易中不文明的丑恶现象。
综上所述,自公元2世纪以来中国人就参与了开辟印度洋航线,并为这条航线的确立和拓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人类征服印度洋的千百年中,中国人有所作为。在印度洋文明的形成中,中华文明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此来看,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上展示的威武雄壮一页,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