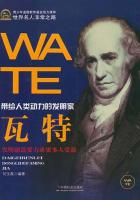守益来信将这些事情告知了阳明先生,守仁于三月间回信称赞了守益,其中道:“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而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矣。”
在这里,守仁再次强调了礼乐的根本在于合乎人情,也因此摆明了他对于大议礼之争的态度。
四月,守仁又复信南大吉。此前,大吉入觐,见黜于时,他致书阳明先生,千数百言,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
守仁读过大吉的信后,于是感叹道:“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看来大吉真的已经步入圣人之门。
欧阳德一向为守仁所器重,在中进士后他出守六安州。几个月后,他来信告诉先生说:自己初政倥偬,后稍次第,始得于诸生讲学。
阳明先生不禁对身边的门人说道:“我平生讲学,正在政务倥偬中,难道必先聚徒而后才讲论学问吗?”
此后,守仁又在致欧阳德的书信中说道:“良知不因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则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圣门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落在第二义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也。”
还是那个宗旨,吾性自足,良知当不假外求。
这一年,钱德洪与王畿并举南宫,但当时大议礼之争闹得正凶,朝廷没有举行殿试,于是钱、王二人偕黄弘纲、张元冲同舟归越。
钱德洪是守仁的余姚同乡,他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德洪仕途坎坷,嘉靖十一年才成为真正的进士,但此后在险恶的政治漩涡中被两度下狱,后被斥为民。德洪既废,遂周游四方,宣讲良知之学。直到明穆宗继位,德洪才得以复官,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神宗嗣位,复进一阶。卒年七十九,学者称“绪山先生”。
王畿,字汝中,山阴人。弱冠举于乡,跌宕自喜,悟性非凡,但有点狂者性情。后受业于守仁,阳明先生闻其言,无底滞,不禁大喜。后守仁征思、田,便留下他与钱德洪主持书院。王畿后来也在险恶的仕途中遭废黜,从此他益务讲学,足迹遍东南,吴、楚、闽、越皆有讲舍,年八十余不肯已。其人善谈说,能动人,所至听者云集;每讲,杂以禅机,亦不自讳也。
当时士大夫为博取虚名争相讲学,而钱德洪、王畿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德洪彻悟不如畿,畿持循亦不如德洪,然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犹不失儒者矩矱。
王畿被学者称为“龙溪先生”。后来,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王畿门徒之盛,与泰州王艮相埒。
看到几位弟子回来,守仁非常高兴,总比陷在是非之地无辜受牵累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引”才成为一种正式的安排:凡初及门者,必令引导,俟志定有入,方请见阳明先生;而每当临坐,阳明先生却只是默对焚香,并无一语。
正像此前守仁对黄绾的忠告,总是重复自我的观念是没有益处的,而且心学归根结底是一位道德实践的学问,学生还当以悟为主,然后落实到行上,这才能成为“真知”。
尤其弟子们的禀赋、性情、志趣各有不同,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NO.5 良知本体
在诸氏死后,为了照顾自己的起居,守仁不得已又续弦了年轻的张氏。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守仁,以久病之躯,对于生育自己的子女早已断了念想。可是,就在新婚不久,张氏却怀了孕,嘉靖五年的十一月,更顺利地产下了守仁的亲子。
看着自己这个白白胖胖的儿子,老来得子的守仁自是喜不自禁,看来上天还是待自己不薄的!同乡中有两位年逾九十的老者,还特以作诗向守仁表示祝贺。
当时,守仁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正聪”。守仁死后,黄绾为了照顾这个孩子(悯其孤而抚之),于是认他做了自己的女婿;就在正聪七岁时,黄绾为了避皇帝(朱厚熜)的讳,便将正聪改名为正亿。
不过此前守仁已经过继了正宪为子嗣,如今又添亲子,正宪将如何安排便成了摆在守仁面前的一个现实棘手问题。由于守仁有爵位在身,正宪的亲生父母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他们自然希望守仁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交代。
可是,由于守仁死得太过匆促,一应后事都未得作妥善安排,正聪的出世反而成了王家不少人的一块心病。
十二月,守仁作《惜阴说》。
此前他的门人刘邦采在家乡吉安(安福县)聚合了一帮同志,取名为“惜阴”会,他们来请阳明先生书写会籍,守仁便作了这篇《惜阴说》。
其中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其所以学如不及,至于发愤忘食也。尧、舜兢兢业业,成汤日新又新,文王纯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阴之功,宁独大禹为然?”可见圣人都是珍惜光阴的表率。
次年,守仁奔赴广西的时候路过吉安,他还记挂着“惜阴”会的事,于是又寄安福诸同志书道:“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程)明道有云:‘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为有志圣人而未能真得圣人之学者,则可如此说。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不至者。惟恐吾侪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专心致志于此耳。”
守仁在信中还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番忧虑,那就是担心有些人急功近利、贪慕虚名,而不能真正下功夫去遵从良知、学至圣人。
在左顺门事件后,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等人由于在议礼中支持了皇帝,事后都得到了升迁。
其中方献夫从翰林学士进为少詹事,但他对朝臣们对自己与张、桂诸人的蔑视心理深感不安,没几年就告病还乡了。
嘉靖皇帝已经隐隐感觉到朝廷上下仍旧存在的反抗情绪,为此他一方面他更加依靠支持议礼的诸臣,尤其是张、桂二人;另一面也开始抓起皇权这把利器,通过狱案严厉打击反对派。
嘉靖五年,延续了达八年之久的“陈洸案”起,凡攻击陈洸及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几乎无不被牵连得罪,逮捕至百数十人。
陈洸本是个无赖之人,曾官居给事中,乡居时常横行不法,被人揭发。当时身为吏部尚书的乔宇在得知陈洸的秽行后,便将他出贬为湖广佥事。
后来,陈洸见张、桂等人因支持皇帝而骤贵,于是也加入了支持皇帝的阵营,并得以官复原职。但他很快就遭到了言官们的弹劾,狱案由此而起。
由于诸多主审大臣不能完全迎合皇帝的意思,结果纷纷遭到贬黜,这其中也包括了良知未泯的黄绾等人,他因参与审判此案受到了不小的牵连。
就在嘉靖六年的正月,守仁便致书黄绾道:“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工夫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平日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弛然日就颓靡者。
近与诚甫(黄宗明)言,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彼此约定,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功夫又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魍魉自消矣。《中庸》谓:‘知耻近乎勇。’只是耻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
今人多以言语不能屈服得人,意气不能陵轧得人,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为耻;殊不知此数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耻者。古之大臣,更不称他知谋才略,只是一个断断无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诸君知谋才略,自是超然出于众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断断休休体段耳。
须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实康济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负如此圣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只有致得自己良知,做事才有充分的自信,才能一往无前。这算是守仁的经验之谈。
不过他如此谆谆教导,显然是对于黄绾一些举动的担忧;虽然不是玩火,但二黄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中,一来不容易全身而退,二来也容易迷失良知。
尤其是黄绾与张璁走得太近,明显有朋党的嫌疑。
四月,邹守益刻阳明先生《文录》于广德州。
此前,守益录先生文字请刻。守仁于是自标年月,命德洪类次,且遗书曰:“所录以年月为次,不复分别体类,盖专以讲学明道为事,不在文辞体制间也。”
不久,钱德洪又掇拾先生所遗文字请刻,守仁有些不悦道:“此便非孔子删述《六经》手段。三代之教不明,盖因后世学者繁文盛而实意衰,故所学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删《诗》,若以其辞,岂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为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经》皆然。若以爱惜文辞,便非孔子垂范后世之心矣。”
德洪解释说:“先生文字,虽一时应酬不同,亦莫不本于性情;况学者传诵日久,恐后为好事者搀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
于是守仁许他刻附录一卷,以遣守益,凡四册。
在守仁的晚年,据王艮所说,阳明先生已经不再重申“致良知”之教,而是只讲“良知”。
比如阳明先生曾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彼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明末的大儒刘宗周指出:所谓“去人欲而存天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其实都是阳明先生在不同阶段教导学生的用功方法,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自己的学说不断进行总结的过程;“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说,远溯之精一之传,盖自程、朱一线中绝,而后补偏救弊,契圣归宗,未有若先生深切著明者也。是谓宗旨。”
可见“致良知”只是功夫,良知才是心之“本体”,守仁自己也说:“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此理为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
而回复到本体,大概也就表明了守仁心学体系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