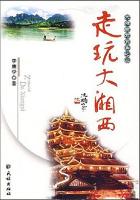“婆婆年纪大些之后,就很害怕死亡,她最担心的就是撇下孤苦伶仃的我。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如果梦见掉牙齿了,就是她要去了。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晚我真梦见自己掉牙齿了。”覃爸爸说得还真有些玄乎,“当时我想都没想,连夜就从学校住家里跑,果然,正如她所说,牙齿掉落,油尽灯枯!”
想必,这个梦是祖母和孙儿的最后一次约定。祖母用毕生的爱,温暖了孙儿原本不幸的童年。而孙儿,也将这些温暖转化成怀恋,走得再远,那些心底永存的印记,是故乡,是村庄,更是祖母额头上纵横交错的时光。
这些怀恋,被游子用心祭奠着,从他的心中传递到下一代,或许这一传就是世代永远。
杉树林里,又燃起了香火。
阳光穿透树梢,将缭绕的香火剪碎成光阴缕缕,撩动着迷人的乡愁。
去往故乡的路上,处处都是美景,尤其是这花桥下的一汪溪水,清澈见底的水里有无数尾鱼儿在嬉戏。
他和母亲一起踏上了回乡的路,泥土路的尽头,便是故乡。
杉树林里,又燃起了香火。
阳光穿透树梢,将缭绕的香火剪碎成光阴缕缕,撩动着迷人的乡愁。那乡愁,跃过村头的香樟树,跃过溪头的八角亭,跃过那一条条去往村庄的泥土路。
春天,躺在黄花堆叠的光阴里
故乡最美的时候,当然是春天。
每年的三四月,油菜花便铺满了原野,从山坡到平原,从田间到溪边,层层叠叠的金黄,将故乡装点得美轮美奂。
历经冬的寒冷,此时的气候温暖舒爽,小伙伴们也都趁着这大好天气,撒开了欢地在花田里追逐嬉闹。玩累了,我也会躺在花田里晒着暖阳,看着黄花堆叠的天空静静发呆。绵软的空气里,沁满芬芳,风在花间行走,留下些许平仄的风痕,那些嗡嗡穿行的小精灵,将细碎的心事裁留在蕊间,轻扯起星星点点的尘埃。
母亲和小姑就坐在花田围绕的瓦房前,纳着鞋底。小姑要出嫁了,我们那儿的陪嫁少不了鞋子,而且,准儿媳得给婆家的每个人准备几双,所以,从春节后到还未插秧的闲适季节,家里的女人们就一直在忙个不停。那时候的鞋子还是千层底,一层又一层,一针又一线,捯饬起来很费工夫。
我和弟弟们就绕在母亲和小姑的身边,无休止地嬉闹着。母亲有时烦了,少不了要骂上我们几句,而小姑则在一旁偷笑着,她的笑容很甜,黄花将新娘子的脸映衬得很好看,有点像中堂画上的仙女。
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弟三个,自然是带不过来的,所以,年长的我就一直跟着姑姑、叔叔们,一起玩耍,一起长大。小姑只比我大十二岁,我和她相处的时间最长,我们的关系也最亲密。
小姑要出嫁了,我自然是舍不得的。所以,只要一有时间,我定会寸步不离地跟在小姑身后。除了要准备嫁妆,在这春天的时光里,小姑和母亲还要去割猪草、采茶叶、拔竹笋。当然,这些都少不了我,一放学,我就踩着软软的田埂,寻摸着小姑的去向。小姑有时就提着竹篮,站在无边的花海中,远远地向我挥着手。
我们就一起挤在田埂上,挖猪草,采野花……
油菜花田的尽头,是一座座山坡,在春天,映山红会将山峦染成紫红色。我和小姑都很喜欢映山红,经常会采回来一大捧,放在条桌上的酒瓶里。而映山红开放的时节,也到了清明上坟的时候了。
小时候,从来都不觉得上坟是件忧伤的事情,因为祭奠的都是一些先祖,谈不上怀念,而上坟的过程,就像是一场爬山游戏。那一天,我们可以放心地玩到天黑,不用担心大人的责骂。虽然特别想玩,但上坟的步骤我们还是会遵照完成的:挂黄表纸、燃烛、上香、放鞭炮、作揖、磕头……当然,有时候,会偷偷省略一步两步,或者干脆几个坟头只进行一次仪式,就算统一祭拜了吧!
边上坟,边玩耍,在密林中我们总能发现很多秘密,比如,巨大的蘑菇、黄色的杜鹃花;再比如,刚长出来的甜甜的茶苞……
然而,油菜花凋落后,小姑就要出嫁了。 当她带着嫁妆,坐着大卡车,要离我们远去时,我哭成了泪人。我跟着卡车走了很远,而后又默默地望着卡车离去。那时候我还太小,什么都不懂,总想着爷爷常说的一句话:“女儿总归是给别人养的,嫁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小姑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想想这些,我不由得很是伤感。
幸好,小姑家离我们家不远。穿过成片的油菜花田,走过一座石拱桥,再前行一段山路,在拐脚处那片竹林的深处,就是小姑的家。我和弟弟们只要一有空,就往小姑家跑,有时候,就干脆赖在她家不走了。再后来,表弟表妹们相继出生,小姑的家就成了我们最温暖的乐园。
每次去,小姑都会给我们做很多好吃的。她的厨艺不是很出众,但那种味道却是令人难忘和感动的。每次表弟表妹们抢着吃肉,小姑都会拦住他们:“先让表哥们吃好,你们等会儿再吃。”而后她就会使劲往我们碗里夹菜夹肉。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小姑笑得很开心。
我的学习很好,也成了小姑的骄傲。为了我的学费,她也是费尽了心思,细细地积攒着每一分钱,到了开学,她就会准时把钱送到我父亲的手上,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她的家庭也不富裕,那些钱都是靠卖橘子、卖甘蔗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
这平静如水的日子,这清亮温暖的时光,我以为会是永远。
那个秋天,我和弟弟们帮着小姑收花生,年幼的表弟表妹们在地头边疯狂地玩耍,远远的村庄,炊烟袅袅。小姑为我们准备了一袋花生、一袋橘子,还塞给我一些零花钱。这些我都收下了,这么多年来,我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情景,她总想多给我点什么,哪怕是几块钱,哪怕只是一些普通的食物。
小姑依然将我们送到村口,送到拐角处那片竹林下。多少年了,每一次,她都站在村口,一再叮嘱我们,路上小心,不要贪玩,早点回家。那日的夕阳很美,她就站在金灿灿的光芒里,凝视着我们。走出去了很远,我无意间回头,发现她还在夕光里静静伫立。
只是,我没有想到,夕阳下那无意间的回头相望,竟是最后的别离。一个月后,那个深秋的夜晚,她悄悄地拿起农药,一饮而尽,那一年,她才二十八岁。
得知她出事的消息时,我正在外求学。当时通信并不发达,父亲托人打电话给一个亲戚,亲戚再打电话给学校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最后再把信息传递给我。可能是怕我伤心,传话的老师只是说小姑出事了,速回家看看。接到消息后,我便慌慌张张地坐火车、转汽车,往家里赶。等我直奔进小姑家时,家里早已哭声震天,场面极度混乱。小姑父正跪倒在堂屋里,哭诉着整件事情的经过,他哭得很伤心,他说他已经尽力了,等发现时已经不行了。他一个劲儿地祈求原谅,却绝口不提小姑自杀的原因。
到这里,我才明白,小姑已经死了, 她就躺在床上,直挺挺的,一动不动。我穿起白孝衣,轻轻地流着泪,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还来不及面对。
小姑被抬进了棺材,母亲抽泣着,拉我看小姑最后一眼,我却撇过头去,不敢看,也不忍看。我和她最后的相望,还是在村口的那个拐角,她笑的样子,很美,很美……只是,如果知道那就是永别,我一定会带她走过开满油菜花的山坡,一定会紧紧拉着她的手,迎着阳光,紧紧相拥。
后来小姑父说要投河,一群人都拦着。我轻轻一笑,为什么非要等到人都走了,再做这些无味的表演,等温暖逝去,才知道那一切来之不易吗?可是,小姑最后的孤单绝望,谁又能真的了解。她永远都笑着陪着我、爱护着我,她永远那么温柔,而我却永远看不到她内心的忧愁。
穿过成片的油菜花田,走过一座石拱桥,再前行一段山路,在拐脚处那片竹林的西边,就是小姑的坟茔。
小姑是嫁出去的人,自然就埋不进我们的祖坟山了。爷爷说过,嫁出去了,就永远都回不来了。如今想来这句话,有一种刺骨的痛。
故乡的映山红开了,又到了清明上坟的时候了。
上坟的步骤依然还是那些:挂黄表纸、燃烛、上香、放鞭炮、作揖、磕头……只是转眼之间,早已长大的我们,有太多令人怀恋的光阴和故人,就像这黄花堆叠的春天,原本那么无忧无虑的季节,如今却也堆叠着浓浓的思念。
油菜花开的时候,依然是故乡最美的时候。
泥土被犁铧翻动着,涌动着一股春的气息。
黄花堆叠的春天,堆叠着无边的锦绣。
黄花堆叠的春天,正是清明时节,山里的小路上,总会出现提着祭品、拿着纸花的少年。
上坟的步骤依然还是那些:挂黄表纸、燃烛、上香、放鞭炮、作揖、磕头……
那一个时光小院
走进这个小院时,炉灶边的烟囱正冒着灰白色的炊烟。老爷爷在水缸边洗着青菜,老奶奶正往炉灶里塞着玉米秆。
老奶奶打量着我手中的相机,笑着问我打哪儿来。老爷爷一听我来自江西,马上就指着村子南边说,一直走,一直走,那是个很远的地方。我笑着诉说着家乡的风物,老爷爷听着,也闲唠了几句家常。陌生的小院,陌生的老人,但这样的陌生却是如此的熟悉,曾经的岁月里,疼爱我的外公外婆,就是在这样的院落里劳碌、苍老直至逝去。
老两口住的房子,是村里唯一的老屋,在四周瓷砖房的映衬之下,这间灰突突的小屋显得很是沧桑。这间老屋,是老两口的婚房,从结婚至今,六十多年的岁月,在这个小院里,他们用岁月的橹,摇出了几双儿女,又摇出了子孙满堂的欢愉。儿孙都已成家立业,大多去了远方。而他们,却依然执守着这一方窄窄的院落,静候着不变的时光。老爷爷说:“住不惯儿孙的家,还是喜欢老两口过,自由自在,唉,也怕拖累他们咧!他们各有各的难处。”
那一方敞亮的小院,那一座幽黑的老屋,似乎还存留着旧日的时光。经由雨水的侵蚀,旧日的痕迹穿透初夏温暖的空气,淡淡地在周围弥散,像一条安静的水流弯过身边,弯进那些久远的故事里。那一年,花轿抬过院门,柳絮漫天,人间四月天里,红红的盖头掀起,两弯细娥眉,一双红酥手;转眼间,苔痕染绿了院角,烟火熏黑了酥手……
坐在低矮的屋檐下,我不由得想起逝去的外婆,恍惚中,外婆背过身子,炊烟下的晨光里,她细细地梳理着满头的白发。岁月像一把犁铧,深入额上那一行一行的田垄,多少时光老去,只是那绾起的发髻依然,就像当年绾起的少女梦,从青丝到白发。外婆的白发随着村口的竹篱笆摇曳,随缕缕炊烟慢慢升起,变成清晨漫天的朝霞。
谈起与老伴相识的过往,老奶奶时不时地用她那粗大的手掌捂着嘴笑个不停,看得出来,老奶奶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年轻的时候,老奶奶是家里的主心骨,做事风风火火,当然脾气也有些火暴,那些年,生活贫困,老两口也会为生活的琐事争吵,但经由六十年岁月的磨合,一切归于了平静。他们在一起拾柴做饭,洗衣铺炕,这样的日子反反复复,平淡却也安然。那渗着流年记忆的木格窗下,老两口端坐在炕沿,窗外柳絮飘荡漫卷……
老爷爷闲暇的时候,经常提个马扎去村口的墙根底下听收音机,也顺便去和老朋友们拉拉家常。他喜欢听河北梆子,当然,也喜欢听些流行歌曲,比如,“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老爷爷说,这歌真不赖。原以为这是电台放的歌曲,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些歌都是孙子帮他拷进去的,他天天都听,百听不厌。老爷爷喜欢看电视剧,更喜欢看闯关类的节目,每天必看《激情大冲关》。他一直和我们强调,那节目可好玩了,老伴也爱看,就喜欢看那个整齐劲儿,看谁跳的技术好,要是跳好了,能过关就一千块,要是过不去就没有,不好挣着呢……而老奶奶,所有的时间基本都在忙碌,打扫做饭,收拾屋子,里里外外,来回转动,没有停歇。小院里来往的人很少,儿孙们大多都在外地工作,只有重孙子会经常扑腾进小院,围在老两口的身边打转,彼时的小院,才显得格外欢腾。
“给你筷子。”“吃点这个吧!”这是吃午饭时,老爷爷说的两句话。夫妻二人,面对面坐着,脚下是两只拱来拱去的猫,他们没有过多言语。只是,那传递筷子的瞬间,恍若凝结了时光的痕迹,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六十年前,这样的传递只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画面,但当这样的画面穿越了几十年,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时,却是那样的令人陶醉。岁月流逝,他们的身影已然蹒跚,他们没有海誓山盟的承诺,没有天荒地老的约定,只有淡淡的相守,默默的依偎。也许这样的爱才是相濡以沫,才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浪漫。
期待在这样的旧院落里晒晒太阳,只是那两天遇上了阴雨天。而我,在今天这样一个艳阳天再将小院想起:是否,此时的阳光穿过树梢,正洒满一地的温暖。老爷爷是否又在水缸边洗着青菜,而老奶奶是否又正往炉灶里塞着玉米秆。树影婆娑的青砖路上,扑棱着翅膀的老母鸡正四处找着食,两只懒懒的大肥猫是否又在望着炉灶上的饭菜。而那满树的榆钱,是否落了一地,无人问津。夕阳的余晖下,老两口又坐在小院里,静静地捡拾着时光……
我也跟着时光,捡拾着童年最绚烂的画面:二十多年前,每当母亲挑着箩筐里的我和弟弟走进外婆家小院的那一刻,外婆就会踮着小脚从屋里向我们飞奔而来。她抱起箩筐里的我们,看看母亲又看看我们,她的笑很甜,她的怀里很暖。黑漆漆的灶台前,就着煤油灯一丁点的光亮,外婆做着香喷喷的饭菜。我在她的跟前来回晃动,我说我饿了,她亲切地说:“细啊!就熟了,再等等!”我并不知道“细”是什么意思,只知道那是天底下最柔软的呼唤。黑漆漆的灶台和时光把她的双眼熏黑了,她眼前的世界,时而昏暗,时而明亮。
外公逝去的时候,我已经漂泊在外,外婆穿着白色对襟长褂,独自睡在院东头的木床上,她不忍听那如泣如诉的唢呐声。外婆说外公离去时一直在喊着我的名字。那晚的月色青蓝,外婆的眼泪很咸。而那个时候我没有回故乡,只知道,想见上我一面,是外公离去前的期待,也是外婆心底的盼望。没有了外公的日子,外婆有点魂不守舍,她总是喃喃自语道:“没有我,他一个人不习惯哪!”她说外公给她托梦了,梦里的外公就站在木床前,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她舍不得外公一个人冷清孤单,她要去陪他,为他洗衣做饭。外婆也走了,走得更为匆忙,我依旧忙碌着自己的生活,漂泊在外。母亲打电话总是重复着一句话:“她真的很想见你们啊,真的很想见……”院东头的木床破了、空了,整个院落都没有了温度。
每个人都有一个时光小院,只是在时光的流逝中,那个小院或是衰草凄凄,更或是没了踪迹。有时候,我们偶尔也会惦记起小院的模样,只是时光不知不觉走得那么快,我们都还来不及细细缅怀。
走进这个小院时,老爷爷在水缸边洗着青菜,老奶奶正往炉灶里塞着玉米秆。
老奶奶打量着我手中的相机,笑着问我打哪儿来,她的白发如同霜雪般耀眼。
夫妻二人,面对面坐着吃饭,没有过多言语。
老两口在一起,静静地捡拾着时光……
大宅院最后的守望者
这儿离平遥古城不远,开车30分钟即可到达。
这儿和平遥城的深宅大院一样,也有着繁华的过往,理应得到细致的保护,但这里的破败却远超我们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