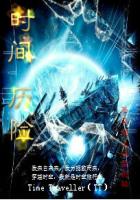酒店电梯里的小孩
前几年出差到上海,在入住的希尔顿酒店的电梯里遇到这么一个场景:一个少妇带着她的孩子进了电梯,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可能是第一次进电梯,随着电梯门的关闭,他兴奋得又蹦又跳,一边大声念着楼层按钮上的数字“一,三,二,五……”,一边开始用他的小手把能够得到的电梯楼层的按钮来了个“格杀勿论”。“东东,听话!不许乱动!”那位少妇一边训斥一边用手将小孩拉到了自己身边。东东显然还不死心,小胳膊伸得笔直笔直挣扎着还要去按那些还没被按亮的按钮,小家伙一定是琢磨出什么东西了,眼睛里闪烁着兴奋和好奇的眼光,脸也挣得通红。“东东,听话!再不听话保安叔叔就会把你带走!”那少妇显然有点力不从心,提高了嗓门威胁道。不过这一杀手锏好像还挺灵验,东东立马就老实了下来,小脸抬起来用恐惧的眼神环视着我们几个男人,好像要窥探我们是不是便装的保安。走出电梯我的心情挺沉重,“听话”两个字总是在耳边回响缭绕,一遍又一遍。
摧残人性的“听话”文化
用“听话”两个字来概括中国文化中教育的精髓恐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用听不听话来衡量其品质和能力的优劣,在家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工作了要听领导的话。“这孩子真听话”恐怕是老师、家长能给孩子的最高评语了。
而“不听话”又几乎是万恶之首。但恰恰就是“听话”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唯命是从,习惯迷信书本和崇拜权威,因而缺乏创新的能力和挑战传统的勇气。和大陆出来的留学生有过接触的美国同事常常会问我为什么他们大多都那么“听话”,但却少有自己的观点而且缺乏挑战权威的勇气,在中国管理过办事处或是企业的美国朋友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中国员工有同样的印象。他们也常常会问起我为什么是个“异类”,并因此给我取了个绰号“中国鬼佬”。意思是我虽然是个中国人,但在公司里却是出了名的有自己独到见解、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将不同意见公布于众的人,也就是说并不总是那么“听话”。
旺鸡蛋里孵出的小鸡
说起来我真的应该好好地感谢父亲对我的影响。可能他自己从小受西方教育的原因吧,虽然父亲中文功底很好也保持着很多传统的中国教育方法和道德观念,但他对“听话”并不十分推崇,遇到孩子们有了新颖独到的想法和做法,父亲总是鼓励我们“试试看”和“你能行”。正是这“听话”和“试试看”之间貌似微小的区别,让我们兄弟几个在心灵深处保留了一点自我和创新的萌芽。
小学时发生的一件小事记忆犹新:一个周末父亲从学校的实验农场里买回了一篮子旺鸡蛋,篮子里发出的“叽,叽”的叫声引起了我们兄弟几个的好奇心,还有活着的生命!原来实验室到了规定的时间就把所有没出壳的小鸡连同死蛋归为旺蛋卖给员工,因为人工孵化器根本不管那些先天不足的小生命的特殊需要,也不可能去提供母性的爱心和耐心。“这些小鸡还能活吗?”“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救活它们?”“我们情愿不吃旺鸡蛋也要救它们!”我们七嘴八舌地缠住了父亲。“可以试试看!不过即使我们能帮助它们出了壳,这些先天不足的小鸡要想长大也不是很容易。”父亲一边鼓励我们一边给我们打预防针。
我们在父亲的指点下七手八脚地忙开了,先把还有生命的旺蛋小心翼翼地挑了出来,凡是没有啄破蛋壳的再帮助把蛋壳轻轻敲裂并在破裂处用水湿润,然后用一只盐水瓶灌上热水代替母鸡给小家伙们加温,并替“母鸡”和它的鸡蛋们盖上了一件小棉袄保温,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再孵化工程。我们成功了!两天内一共孵出了七只小鸡!我们给每只小鸡都取了名字,而且有意思的是七只全是母鸡,除了一只后来不幸病死,其余的都长大产卵,好好地改善了家里的生活。
当然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这件事的过程,我们从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科学孵化的知识,更是让我们经历了失败的痛苦(看着那些最终没能冲出蛋壳而夭折的小生命的心情),品尝了成功的欣喜,培养了我们的求知欲、自信心、耐心、爱心和最初的团队精神(兄弟之间的分工合作)。
用现在的观点看,这绝对是在课本以外集情商和智商为一体的一个综合训练。而从被已经判了死刑的旺鸡蛋里孵出小鸡又何尝不是对权威和习惯的挑战呢?父亲的这种“试试看”的事例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耳濡目染之中我们兄弟们都养成了不安于现状、不循规蹈矩和不太听话的品性。这虽然在那个时代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却为我们最终的成长和成功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后来到了美国,观察自己孩子在美国学校的学习过程常常能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例子,而与此相反的以听话为中心的灌输式教育恰恰是被一根高考指挥棒锁定的中国教育的最大弊端。
为不听话的孩子辩护
我们在身边的亲友中不难发现,过去在小学或中学因为成绩好和听老师话而当上中队长、大队长的所谓尖子生后来到了社会上反而多见平庸者,而那些挺调皮但是成绩平平的学生有不少反倒是因为很有成就让老师、同学跌破眼镜。
我自己小时候受老师最多的批评就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爱做小动作”。其实我的这些缺点主要是表现在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上或者是自己不喜欢的老师教的课上。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科目和老师,像英语、语文和生物,我不但没有“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爱做小动作”的缺点,而且还常常是班上、年级里的尖子生。幸亏那时候还没有“多动症”这种说法,如果有恐怕我也要算得上是个重病号了。
孩子的抱怨
到了我的下一代,中国的教育在高考的死胡同里越走越远。大量的功课和反复的练习还有考试都是围绕着高考这个指挥棒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找出标准答案,而标准答案无疑来自于最终出考题和改考卷的老师,哪里还容得学生有自己的思考天地和独到的见解!除了继续“听话”,孩子们还能做什么?
“我恨死李铁映了!”有一天儿子放学回来两眼泪汪汪,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那时我回国在大连担任纽鲁克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把孩子接到大连上小学。听到他的哭骂我们吓了一跳。李铁映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我们以为他在学校受了谁的欺负,一问才知道,好不容易盼到一节自习课想用来早点完成家庭作业晚上回家可以看电视,老师竟然因为有少数同学“不听老师话,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罚同学们在自习课背《学生守则》。在全班学生乱哄哄地背诵味同嚼蜡的《学生守则》时还能“注意力集中不做小动作的”,我看恐怕倒真是该去看看医生了。
恰恰是孩子当时那张带着泪水的脸庞和他稚气十足的一句诅咒让我和太太如梦初醒,中国的教育制度太糟糕了,太摧毁孩子的创造力了。照说孩子应该诅咒的或是那几个惹是生非的“少数同学”或是做出处罚大家的老师啊。平心而论,这牵扯不上李铁映。不过后来再一想就后怕起来,不得不佩服当时还只有十多岁儿子的思维。你李铁映不是教委主任吗?其实所有这些毛病追根溯源不都是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吗?那我不骂教委主任骂谁!你看这小子看问题看得多有战略眼光!
当时忽然想到如果三十多年前我们兄弟们用旺鸡蛋孵小鸡的一切条件重现,我会让孩子去做我和兄弟们终生难忘的那件有意义的活动吗?即使我会,我的孩子会有时间去做吗?正是这种愈演愈烈的教育歪风使我和太太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深深担忧,而孩子的那声哭骂促使我们不顾老板的反对和威胁,冒着被解雇的风险果断地下了决心辞去了公司驻华首席代表待遇优厚的职位,毅然决然地带着孩子、妻子举家定居美国。促使我们做出决定的动力之一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成为当时中国教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