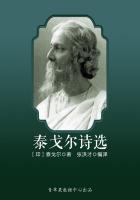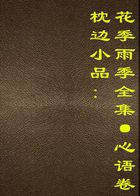38
走着走着,楚楚终于开口了:“这个地方有点眼熟。”
我喜出望外:“你想起来了啊?”
楚楚打断我:“没有,但是我有种不好的感觉。”
我用手指指远方:“看前面都是灯光了,有光就有希望,我有种很好的感觉。”
楚楚说:“我的是女人的直觉。”
我说:“我的是男人的理智。”
说完我拉着楚楚开始飞奔:“来,希望就在前方。”
灯光越来越近,就在快到的时候,两个人端着枪出现我们面前:“站住!你们是谁?”
我吓得连忙站定:“我们是坐火车的。”
左边的人哈哈大笑:“火车在哪里?”
楚楚指着我:“都是你,非让我下火车,这下好了!”
左边的人指着我:“他是人贩子?”
我赶紧摆手:“不是不是。”
那人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乱说了一通,我问楚楚:“他说的是什么?”
楚楚说:“越语。”
我说:“奇怪了,我港片看得还算多,这个算哪门子粤语?”
楚楚冷静道:“越南语。”
右边的抖了一下枪杆子:“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我和楚楚连忙说:“没什么没什么。”
左边的见我刚刚对他说的话没有反应,说:“你们来边境干什么?”
我说:“什么?我们到边境了?!”
楚楚恍然大悟:“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原来到边境了。”
那人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异口同声:“我们是跳火车的。”
右边的人紧张地托着枪把:“大哥,他们不会是上次在报纸上看到的情侣逃犯吧?”
我们连忙否认:“不是不是。”
左边的人显然也觉得我们不像:“他们这样也配得上情侣逃犯,情侣逃犯在我心里是很神圣的——呸!你们给我举起手慢慢走过来!”
我只好举起手慢慢朝他们走去,走着走着,我觉得我怎么感觉不到楚楚的动静,正打算回过头看看动静,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就让我不由自主地倒下去,我想,完了,难道楚楚和他们一伙的?
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睁开眼,楚楚正在吃一种未知的东西,只见她转过来的时候嘴边都是血色的一片,莞尔一笑:“你醒了啊?”
我应了一声:“嗯。”
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楚楚用手拍拍我的脸:“你刚刚怎么又晕了过去?”
我警惕道:“我第一次是怎么回事?”
楚楚乐了:“你被绊了一下,然后就把自己摔晕了,哈哈哈哈,你太逗了。”
我羞愧不已:“你刚刚吃的什么?”
楚楚说:“红椒拌饭,是我们的特色。”
我说:“是给我们的伙食?——奇怪,这是哪里?”
楚楚说:“嗯,看守房,在有人来接我们以前,只能如此了。”
我问:“接我们?你有人认识?”
楚楚说:“没有。”
我说:“那谁来接我们?”
楚楚说:“刚才你晕的时候你的电话响了,他们拿去接了,说是会有人来接我们的。你认识的人很厉害嘛。”
我说:“大概吧——原来这就是看守房啊。”
楚楚说:“是啊,你居然让我进了看守房,我认识的男的还真是不靠谱——”
我苦笑:“不过我算是让你的人生完整了啊。”
楚楚安静下来,轻声地哼起了一首歌: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熟记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离开的原因……
你勉强说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哪一种表情/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封信/都是你离开的原因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一曲唱完,我夸奖道:“唱得挺好听的。”
楚楚看着我:“你知道这歌叫什么?”
我大跌眼镜:“你不知道啊?”
楚楚说:“刚刚门外的广播里听到的。”
我说:“你听了一遍就会唱了?”
楚楚说:“嗯。”
我大为崇拜:“你不用做空姐也不用去售楼了,你应该去做歌手。”
楚楚说:“我的男朋友也这么说的。——忘了是哪个,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和他分手以前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搞音乐的。话说回来没有那个搞音乐的我估计不会这么快和我男朋友分手。你猜怎么着,那天我回家发现门居然是锁着的。大概过了15分钟以后我就看见那个搞音乐的女朋友从门口出来,我进去的时候我男朋友还在床上。我就什么都明白了。我别提多伤心了,要知道那个女的在我看来没一点比我好。我居然败给了新鲜感。其实我想过有一天我会败给时间败给青春,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么早就输给了新鲜感。”
“第二天,我就收拾准备从家里搬出去,收拾到一半我才意识到这个房子是我租的——连押金都是我交的,我一想就忍不住伤心,我就把那个男人的被子掀开,我骂,你他妈给我滚,这是我家!”
“不过他走后我越想越不对,我的家居然让两个陌生人进进出出,我就哭了,很伤心很伤心。”
我插嘴道:“这个时候那个搞音乐的就进来了?”
楚楚说:“你别打断我——不过你怎么知道——真的,我想都没想过他会过来,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不过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就一起相互安慰。”
我继续插嘴:“然后你就住到他家去了?”
楚楚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猜的。”
楚楚说:“你猜得真准——我说到哪里了?哦,对,我就搬到搞音乐的那人家里了,反正他家房间很多。说来你不相信,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孤男寡女待在一个房间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你说奇迹不奇迹?哈哈,就和我们现在一样。不过我那会儿就是不住在自己那里,我觉得恶心。你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随意的人,我甚至可以接受我男友的花心,只是我不能接受他的多情。你觉得这两个没有区别吧?我觉得是有的,不过我也说不清楚。”
“后来我在那个搞音乐的人家里住的时候他就夸我是一个天才。我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夸。他后来带我去见过几个制作人,大家都说我可塑性很好。然后我就出了一张单曲的专辑,名字叫什么来着——哦,《姗姗来迟》,那会儿我的艺名就叫姗姗——很俗的名字,不过容易记住。不过虽然我可塑性很好,可惜我没有包装好,买我的专辑是不送东西的。你知道,现在不送点东西根本没人买。像买份报纸都恨不得能送一台彩电。我的预算不够——那会儿正是非典,要是我能送一个口罩,估计我也能火。而且我还有一个失算的地方,我的专辑封面穿得太保守了,你也知道,姗姗来迟,都迟到了,还不给人看到点精彩的东西哪有人等得住?——早知道我应该一脱成名,错过了。像我这样的歌手第一次不能够火,很难再有机会。”
楚楚的语气中竟是遗憾,我说:“姗姗来迟,你还记得怎么唱吗?”
楚楚说:“我就记得几句了。”
我鼓励道:“来,唱唱看。”
楚楚犹豫了一下,开口:
恋爱等了许多人/几位能够成了真/守株待兔一世苍白的森林/姗姗来迟不知道真爱丢在哪里/太多故事没结尾/太多恋人未相随/问君能有几多愁苦于世人/我怎么能走进你的心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9
我愣了半天,不知道如何评价:“这歌似乎很好听,不过要火也很难。”
楚楚赞同道:“对啊,这歌太沧桑了,你看我刚出道,应该唱些有活力的歌的。”
我深表同情:“你的歌和歌名一样,来错了时代,姗姗来迟——有没有别的歌?”
楚楚说:“我出的是单曲,这是我唯一一首歌。——对了,我刚刚唱的是什么歌?”
我说:“哦——你还记得啊——那歌叫《旅行的意义》。”
楚楚说:“旅行的意义,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好可怜的女孩。”
我说:“其实,离开一个女孩去别处旅行,目的不一定只是为了离开,也许更多的是为了旅行。比如我,我要去一个地方,我只是不得不去,当然我心里也很想去。有些东西,我辜负只是因为我的负责。”
楚楚说:“那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苦笑:“可以这么说。”
楚楚说:“那你这次旅行是想做什么?”
40
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一个陌生人。即使是对于叶子,我都不能坦诚地回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此行是为了一个异性。倘若我只是为了一个男的,也许很多问题就简单了——当然可能也会变得更复杂。而孙菲菲,她注定不能作为一个我儿时的简单玩伴。事实上我也没有几个玩伴。
在我们一个个不知道过去和当下的时候,她已经着眼于未来了。如果说现实是残酷的,那它残酷的地方就是让孙菲菲永远停留在了当下。她不用再考虑中考高考恋爱结婚买房买车,不用担心工作付了房钱没饭钱付了饭钱没房钱,不用担心用信用卡透支一块钱去买一个馒头,不用担心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打的时的纠结和付钱时的忐忑。她只是让我们闲暇之余想起的时候,倍感无力。
41
我一直是个跟不上时代的人,我听到第一首所谓的流行歌曲是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小学六年级,万宝路的毕业歌曲。
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愉快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这歌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内只知道谢霆锋这一个歌手。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最流行的歌曲是《心太软》。
初中的时候,大概因为《还珠格格》是台湾拍的缘故,我们疯狂地开始热衷于台湾的明星,从邓丽君小虎队到周杰伦SHE。很多人连自己爸妈的生日都不知道却可以对周杰伦穿没穿内裤用的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如数家珍。而万宝路却开始唱起了罗大佑老狼朴树,似乎他从来不跟着潮流走。初中毕业晚会,万宝路选择了《同桌的你》,一把凳子,万宝路坐在我们学校食堂的舞台上,一把吉他,他的歌声轻舞飘扬。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那会儿徐婷婷就坐在我的边上,我说:“知道为什么万宝路会唱这首歌吗?”
徐婷婷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是我同桌,我拜托他唱的。”
徐婷婷说:“你眼光不错,他很帅啊。”
我说:“不过我看你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
徐婷婷说:“你安静,下一个是张一扬了。”
张一扬出场的时候也背了一把吉他,不过让他引起大家注意的地方是他手上的玫瑰花——我也很意外:“老徐,不会是要跟你表白吧,这么有想法?”
徐婷婷白了我一眼,微笑地看着舞台:“安静——”
“今天我站上这个舞台,我想先把我手上的这束花送给一个我一直喜欢的女孩——”说完张一扬走下舞台,向我们走来,我紧张得手都开始颤抖:“老徐,真是你啊,隐藏得太好了啊——”在距离我们两米的样子,张一扬突然停了下来……
故事到这里,我的记忆就开始断断续续,唯一可以确定那个女孩不是徐婷婷。我只记得这之后徐婷婷的头都是低着的,一言不发。而最后她抬起头的时候,眼圈已红。
这样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体会。
在我的初中同学录里为徐婷婷留出了一页,我想过有一天她出现的时候,就让她补上。这只是一个好想法,因为真要联系,是断然不会依靠同学录了,真不联系,同学录除了留作纪念毫无价值。
回想上次看到徐婷婷,正是高考结束。徐婷婷选择了南下去读警校,在这个连自己都无暇保护的年代里,她毅然地选择了去保护别人。
42
透过铁窗,微亮,我有点欣喜:“楚楚,看来天快亮了。”
楚楚也笑了:“好啊,我饿了,快点送早饭来吧。”
我说:“是什么让你想到回来做售楼的?”
楚楚嘿嘿一笑:“老了老了。”
我说:“你跟我差不多,应该说还能再做几年。”
楚楚突然睁大眼睛,看着我,看得我的心有点发毛,最后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摸摸肚子:“因为他。”
我大吃一惊:“谁的?”
楚楚看着我乐了:“又不是你的,你激动什么?是我男朋友的。”
我更加大吃一惊:“你现在有男朋友啊?”
楚楚说:“废话。”
我说:“你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啊——你的男朋友怎么不陪你?”
楚楚淡然道:“他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
楚楚说:“他只是我的一个房客,连自己都养不活。其实我早想过了,谁都不一定可靠,最后还是要相信自己。”
我说:“那总是空姐的工资待遇好吧。”
楚楚说:“你不懂,虽然我每天在天上飞,但是天上到底没有地上踏实。你知道如果一个空姐和机长结婚了,就一定会错开航班,如果有一个人飞机失事了,好歹还有一个活着。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得保护我的孩子。而且我去卖房子,至少可以给他找一个安定的家。”
我说:“不好意思,让你的孩子来了这里。”
楚楚说:“是啊,不过我现在不能生气,他们说怀孕的时候生气对孩子的身体不好——我是要多吃一点,多补一点。我就想生一个大胖娃。不过我知识有限,很多东西都不知道——你知道吗,其实我还逼着自己看了很多唐诗啊童话故事啊,可惜我的数学啊什么英语啊都还给老师了——你说我这样会不会影响我孩子的智力开发?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人的孩子四五岁就认识几千个单词,我一点也不羡慕,你说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是童年啊——哦,是快乐童年——以后有大把的时间看书,何苦把上学以前的时光毁了?你也觉得我这个想法先进吧?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我没有做空姐,不谈恋爱好好读书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会不会成为一个老师或者医生?对了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虽然空姐一直是我的梦想,想着能够一直在高空俯瞰这个世界,但是当我真正坐在飞机上,我发现飞机下面只有白云,我甚至感受不到世界的存在。我不希望给我的孩子这样的未来。”
“我不指望他考什么第一名得什么奖,他要做的就是自己。我一直都在做我自己,也许做得不够好,但我一直在努力。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一个母亲。你是大学生,你的父母是怎么培养你的?我以后肯定是又当爹又当妈,我都要学着点。不过我想来你肯定不是真的喜欢学习?你想啊,谁喜欢学习,我觉着吧,我们应该学习国外,不感兴趣就别做。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的儿子跟我说要去做矿工我肯定受不了。我觉得书还是要读,不强求不退缩,能读进去多少是多少。我还想有机会送我孩子出个国,别看我大大小小的国家都去过,我其实很少买过东西。”
楚楚伸出一只手,露出一个手镯:“看,这个,法国的,哈哈哈,我骗你的,是我在申城地摊上掏的。不过我的确在法国的街上看到过,卖10欧元,”楚楚晃了晃手,“我的,5块,人民币。”说完她露出白色的牙齿笑了起来。
女人一聊起孩子,世界都无法阻止。我笑道:“你打算送孩子去哪里?”
“当然是美国,哈哈哈,”楚楚又笑了,“我也就想想,太贵了——听说现在新加坡很便宜,不过我不喜欢,你想啊,辛辛苦苦花了血本跑到国外去,结果都是中国人,搞得整个国家就是一条唐人街。我还不如把他送到台湾或者香港去。对了,我都不知道,你是什么大学的?”
我惭愧道:“青山大学。”
楚楚睁大着眼睛看着我:“青山大学?你真的是青山大学?”
我只好肯定地点点头。
楚楚说:“我原来还能和一个青山大学的人认识啊,而且还和他一起在牢房里。等我的孩子长大了,我一定要告诉他,你有一个叔叔是青山大学的,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也去青山大学。你说我们会不会再相见?不过没事,孩子嘛,要的就是一个方向一个动力,如果看到你真人他估计就很失望了——哈哈——我是说现实总会让人泄气。”
我笑笑:“没事儿,我也觉得,我实在不像是一个类似于榜样的形象。而且一些人听到故事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生成一个气泡,然后在看到真相的时候戳破那个气泡。我们的历史课本很多时候讲的都是连当事人都不知道的事情,偏偏我们还要以为那是真的。”
楚楚说:“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的孩子没看到你,他应该会比较有动力。不过还要看他自己,我不要左右太多。”
我说:“你会是一个好妈妈的。”
楚楚摇摇头:“好妈妈就不会不给他找个爸爸了。”
我鼓励道:“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楚楚说:“嗯,水稻,关稻子什么事情?你来做爸爸?”
我吓得不轻:“我不行我不行,不过迟早会有的。”
楚楚话锋一转:“天快亮了吧?”
我说:“嗯,估计快了。”
楚楚说:“那我先睡儿,今天先是走了长长的路,后来还被吓了一跳,我得好好休息一下,我要补两个人的觉。”
我说:“行,你靠着我的肩膀吧,我不介意。”
楚楚说:“不用,你借一个手臂就行。”
43
高三的时候,父母也不知道是心血来潮还是受人驱使,我被安排去市高考状元的家里寄宿。这个状元的父母是高中老师,像所有老师一样,他们的主业也就是搞副业,炒房炒股或者家教,基本没有人在教书——我去她家住宿就是他们的副业之一。在我去状元家以前,我一直耳闻她叫金银,后来自己暗自感觉应该叫做精英才对,而事实上,她名叫晶莹。我听到名字以后就觉得是我太低俗了,人怎么会取这么恶俗的名字?
不过想想现在她的生活,其实一点不假。她是精英,她穿金带银。
第一次住到别人家的感觉,就像换一个女友,虽然变化不大,但是倍感新鲜。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上学的路程,原来我都要坐公交才能到学校,而现在,学校就在我百米之内。
唯一相同的是,我依然常常迟到。
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褪去了初中时代的光芒,回到了小学四年级以前的状态。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懒得去思考我吃饭是为了活着还是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只知道吃完饭要看报纸,日报、晚报、体育报、娱乐报、故事报,看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今天的作业还没做过,然后安慰自己明天可以去抄柳陈的,安然地入睡。
这不是最可笑的,可笑的是,我看了这么多报纸,我却不是文科生,我甚至还是无法参与班上一些同学的话题。当时我们班的女生已经不再迷恋台湾的明星了,因为他们发现台湾的偶像剧都是模仿韩国的——当然可能一切都是模仿韩国的,而在大家热烈地争论韩星的时候,我慢慢地喜欢上了周杰伦。我发现我的口齿变得不清思维变得混乱讲话老是喜欢押韵没事总是目光无神。至于我们班的男生,他们还是喜欢吃苹果,我不理解一个苹果有什么好讨论的,喜欢的话去买一袋不就行了?
这样,我就成了异类。除了同桌柳陈,似乎已经找不到可以倾诉的对象。而那时,我住到状元家。一周以后,我见到了大四的晶莹。她和我想象中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不同,但是我可以确信她和我们班的同学不同。我内心有一种很虔诚的感觉,状元的光环让我都不敢与她对视。
当时她正在用纸折东西,我好奇:“你当初是如何考成状元的?你看什么书啊?还有你有没有什么秘诀啊?”
晶莹说:“你这些问题我以前都背过标准答案,那时候一个报纸要采访我,就事先跟我说过,然后把答案给我,让我背出来。”
我不解:“为什么要答案?采访你不就是为了知道正确答案吗?”
晶莹说:“我这个文章是一个营养液赞助的,叫什么来着,我那天看你喝过……”
我说:“青山思思佳。”
晶莹拍了一下手:“对!就是思思佳,脑力全靠他!这个广告词我还有印象。”
我笑道:“现在改了,叫,服了思思佳,人人都是思想家。”
晶莹说:“真是有够俗的——反正那时让我照着稿子采访了一下,给了500块钱和三盒思思佳。”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一些你背的,你就说说你的真实感受。”
晶莹停下手里的折纸:“这个东西,和你去问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跑到终点是什么感觉是一样的。他虽然会说我是一心想着祖国——我假设这个运动员是中国人——才坚持下去的,其实怎么可能?马拉松跑到终点的时候,爹娘都不认识还知道什么祖国?其实你问我怎么样考成状元的,我也说不出来,就是不停下来,一直练。其实到了最后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就是一个机器。”
我说:“你这么说我很难向你学习啊。”
晶莹说:“哈哈,你不是第一个住到我家来的人了,你前面已经有三个了。”
我说:“我知道,其实来你家住也很难。首先要海选,然后是和爸妈来一次,算是初试,最后自己来住一天,算是复试。听说我前面那个就是来的那天晚上摔破了一个茶杯才被淘汰的。”
晶莹说:“哦,那你还是走运的——今年似乎名额少,想第二年的时候报名的人就有快一个班级,到最后我爸妈审核复试就花了大半个月。”
我问:“怎么不是第一年最火?”
晶莹说:“第一年嘛,那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不过因为第一年住的那个人也考了个学校的状元,所以大家才知道的。”
我说:“这么厉害,我想都不敢想。”
晶莹说:“其实那人来之前的联考还是区里的状元,应该说还是退步了,不过群众嘛,众口相传,好的事情总是被夸张。听说很多人都叫我金银。”
我说:“我不喜欢读书,我来你家其实也是无奈——对了,你折了半天,到底在折什么?”
晶莹说:“我在折一朵玫瑰花。”
我大跌眼镜:“用纸折玫瑰花?”
晶莹说:“对啊,这个是我最近很热衷的游戏。”
我说:“你玩的游戏还真高级。”
晶莹说:“那没什么——其实我这次来是我爸妈让我和你聊聊,看看你能不能住进来。”
我紧张道:“不会吧,我连被子都搬过来了——你觉得我怎么样?”
晶莹说:“我觉着吧……看我折好了——”说着她手里已经出现一朵白色的玫瑰花,“你看,其实也没什么难的,这是我第一次折。”
我说:“我这辈子没佩服过什么人,你绝对算一个啊。”
晶莹说:“那你也佩服一下你自己吧。”这句话让我一时半会没有反应过来。晶莹已经把玫瑰拆成了一张平纸:“有折痕的,你把它折出来吧,成功的话,你就过关了。”
我直接有种想收拾行李走人的感觉。她把纸给我的时候大概是中午12点半,3点钟的时候,我依然一筹莫展,我甚至都想跑到学校直接摘一朵玫瑰交差。最后,我还是决定坚持试着折出来。晚饭的时候,我把纸玫瑰还给了她:“我尽力了,外面看看基本和你做得差不多,不过里面还是一团糟。”
晶莹拿着看了半天:“你是天才吗?”
我倍感嘲讽:“里面的我实在是搞不懂。”
晶莹说:“我学了两个礼拜才大致学会。”
“你不是今天第一次折?”
“这你也信啊,你还真好骗。”
我说:“那你让我折不是玩我么?”
晶莹说:“楼下的公园不就是玫瑰?你摘一朵不就好了?”
“这也可以啊?”
“显然嘛,你真是不会变通。”
“那我是不是该准备打包回家了?”
晶莹把玫瑰还给我:“回什么家,吃完饭啊。”
我说:“我又没通过。”
晶莹说:“你完成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就是好好读书。”
44
这是我第一次完全被一个人说服,这样的感觉,就像夕阳中的楚楚一样。
我转过头看看枕着我的胳膊安睡的楚楚,手已然麻得毫无感觉了。
周一的高考动员大会上,走进礼堂就看见晶莹坐在前面,我们的校长和其他领导一如既往地迟到——我有时候奇怪为什么我迟到一分钟就是给班级扣分拖班级后腿的害群之马,他们永远是姗姗来迟口齿不清,却还要我们在台下仰望。
我看过晶莹写的演讲稿,她让我给意见,我当时由于正为纸玫瑰的事情不爽,便随口说道:“你很擅长随意命题,那你就随意演讲吧。”
想来不过是一句玩笑。
结果那天,晶莹从口袋里掏出条口香糖,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开始了给我们的演讲。她到底讲了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我想她每年都来,即使真的没有任何准备,要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说几十分钟,对于她而言也不在话下。问题是她是否说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我只记得在之后的时光里,我总是被她所激励着,似乎想起她,我便有了动力。
此刻我想起她,毫无反应。
我再看看楚楚,略有反应。
在我出发以前,我跑去和辅导员请假:“朱老师,我要离开几天。”
晶莹说:“哦?你要去哪里?”
我说:“这个我也不确定,反正有点事。”
晶莹说:“你跑来跟我说是让我阻止你么?”
我说:“不是,我只是想告诉你——以前我和一个去西藏的朋友在QQ上聊天。他和我在QQ上说,等骑车回来就找他喜欢的女生表白——”
晶莹好奇道:“然后呢?”
我说:“然后这段QQ上的留言成了他的遗言——他回来的时候遇上车祸了。”
晶莹痛心疾首:“真倒霉啊。”
我说:“是啊。”
晶莹说:“那你来找我应该告诉我你去的目的。”
我说:“我的目的——就是寻找答案。”
晶莹问:“去了就一定能找到答案?”
我说:“不一定,但是肯定比去上你的政治课有用。”
晶莹说:“你这样说我有点想阻止你了。”
我说:“其实除了纸玫瑰,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
晶莹说:“总之——保持联系。”
我不知道来接我的人是不是晶莹。如果真是她,我一定要说服她公费在这里游玩几天。如果不是,我也想不到还能是谁。
45
高考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我异常地无所事事。每天的安排就是早上和柳陈打羽毛球,下午午睡,晚上看电视。偶尔还要接待来家里贺喜的客人。这些客人中我大部分都不认识,甚至连我的父母都不一定能确定是谁,他们来时无一不对我赞赏有加,走时无一不对我看好有加。但是我还是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真实。因为纵使我明知自己是走运,当他们问起我高中的情况的时候,我都务必光荣地说我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年年都获奖学金。说的连我自己都信。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一直定义我是三好学生。
像一些伟人一样,我的过去已经不是我的过去。我只是在告诉别人他们想知道的。如果我回答他们其实我高中一塌糊涂不爱学习荒废学业不求上进得过且过与世无争,他肯定认为我是谦虚。其实,他们并不需要我的回答,他们只相信他们想相信的东西。
这让我无比同情那些平日里成绩优异奈何失足在高考考场上的学生。当然,单是失足这件事,就值得同情。
46
楚楚也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她把手臂还给我的时候,我的手臂已经麻了。
捏了捏我毫无知觉的胳膊,楚楚说:“你真是一个很瘦弱的人,你们知识分子给人的感觉真是不一样。”
我欣慰:“你是少数让我感谢自己没有白读书的人。”
楚楚说:“不过你这么弱的人,估计没人喜欢。”
我说:“你不是喜欢知识分子么?”
楚楚说:“那是我的初恋——但是你也知道,初恋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修饰出来的。我以前一个同事整天跟我说她以前航班的机长多帅多帅,害得我特地换班去看真人。你猜是怎么个人?又黑又胖,就是一个小黑胖子,哪里帅了?”
透过铁栏杆,天空微白,估计是快要日出了,我指指窗户:“看。”
楚楚也出神地望着窗外:“怎么了?”
我说:“天快亮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
楚楚摸摸肚子:“是啊,我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早饭——几点了?”
我看看手,只剩下一条表带的印记:“不会吧,连手表都给我收走了?”
楚楚说:“嗯,以防万一嘛,我以前看过一个侦探片,手表是可以用来做麻醉枪的。”
我说:“你说的是《名侦探柯南》吧。”
楚楚说:“不是。我看的是电影,是一个人吃了药变成小孩用手表把他女朋友的爸爸麻醉了替他破案的故事。”
我说:“那不就是柯南么?”
楚楚立场坚定:“不可能,如果是柯南我一定记得。”
我说:“你看过柯南吗?”
楚楚说:“没有。”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不是?”
楚楚说:“我也不知道——不过,反正我心里觉得不是。”
我说:“柯南是我小学时很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虽然我的同桌总是跟我说这个是个很恐怖的动画片。你小时候都玩什么?我玩四驱车,但是四驱车和其他玩具不一样。我所要做的就是把车子装好,安上电池,打开开关,放上跑道。接着车子就开了。我做的只是一个看客。我从来不能把自己带入情节,我不觉得我是天王巨星不觉得我是巨无霸,我不会为别人把我的车子超过而沮丧,不会为了一场胜利奋不顾身,不觉得四驱车玩得很好可以成为什么教授、博士,不过我会为我的车子跑得最快而高兴——你知道,其实所谓的四驱车,去掉上面的盖子,只有两种而已。一种是马达在前面,一种是马达在后面。就是前驱和后驱的区别。而决定一辆车子性能的东西有很多,滚珠轴承弹簧滚轮超轻底盘甚至是赛道。但无论什么车子,真正决定它速度的只有两样东西——马达和电池。当然,这个要合适,好的马达你用永久电池,马达根本转不起来。差的马达你非要装充电电池,跑上几圈就把马达烧掉了。”
楚楚愣了一下:“我觉得小时候玩的是跳牛皮筋。”
我也愣了一下,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我所说的,不过记忆已经被我勾起,我决定继续我的诉说:“其实,我之所以喜欢玩四驱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怕累。你看,我一点不健壮,我不喜欢运动,我只是向往而已。而四驱车能够达到我的需要。我看到自己的车子在奔跑我就会觉得很高兴。四驱车是一个很简单的运动,简单到你花的钱就决定了你的速度。没有偶然没有意外。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比较标准,却省去了很多暗箱。有时候我很怀念那段时光,觉得我很简单,简单到就像矿泉水。”
楚楚用她清澈的眼睛看着我:“我真的想不起来除了牛皮筋我还喜欢什么了。”
大一的时候,我创立了一本杂志。
当时我报名参加我们学校的广播台,结果就是没有结果。由于大一课程较少的缘故,我一下子闲到直接跑回家休息了半个月。回到学校,我觉得我不应该荒废我灿烂的大学时光,又为了和广播台这个声音的媒体抗衡——主要是为了这个,我决定做文字媒体——一本杂志。加上我也没什么钱,我只能做电子杂志。
这本杂志名叫《我们的杂质》。
准确地说,那会儿,我没钱,没人,整个杂志社只有我一个人。好在我热情无比高涨,回学校的一个月以后,我便做出了《我们的杂质》创刊号。
再一个月以后,我被叫到了校团委办公室。
一个可以做我奶奶的人坐在办公室里。从她的电脑上我可以看见我的杂志,页面停留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上,里面讨论了一下学校设施的问题。
奶奶和蔼可亲:“你就是张小飞同学?”
我说:“是。”
奶奶说:“这个杂志是你做的?”
我说:“是。”
奶奶说:“这篇文章是你写的?”
我说:“是。”
奶奶说:“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我说:“是——哦,不,我就是写点我看到的东西。”
奶奶说:“你看到的东西?——你看这句‘我们的学校一旦有三个以上教室开空调,就会导致全校停电。而这不是最不幸的事情,最不幸的事情,就是校长办公室和校长会议室一年四季都开着空调。’——这句话也算你看到的东西?你看,我的办公室不是开着空调?!停电了吗?”
我承认道:“对不起,老师,我写错了。”
言下之意,三个教室应该改为四个。
奶奶再接再厉,又指着一句话:“再来看看,‘来我们大学,没门!有的是门栏。普通的车子进来都要交五块门票。五块钱,都可以进一个动物园了,原来学校不过是圈养了一群学生给大家观赏啊。偌大的学校,别说停几辆汽车了,停几个师的坦克都没有问题。学校的领导们个个挥金如土,怕都是从停车费里拿的吧。’——你觉得你这个也是事实?”
我心想能把事实说的跟假的一样,的确值得佩服:“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事实。”
奶奶说:“你看,学校的老师都是很节俭的。”说着用手一指自己的提包,我望过去,是一只LV,不知道奶奶想说明什么。奶奶估计也意识到自己失误,连忙说:“你看,也不是什么限量的,我省了好几个月才买的。”
我佩服不已:“老师,您真是好老师。”
奶奶备感受用,声情并茂道:“张同学啊,也许你是恰巧看到我们学校一些个别老师的行为,才会写这样的文章。这毕竟是你要生活四年或者更久的地方,你要相信学校,相信老师。”
我感动不已:“老师,我错了,我没有仔细思考就写了这篇文章,是我的错。”
奶奶语重心长:“张同学,在你这个年纪,我是知道的,刚来一个陌生环境,一定是有点反抗的。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文学社,你可以在那里展示你的才华——至于什么杂志,就别搞了。”
这就是我办杂志的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