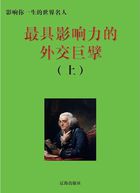“小王其昌”时代,俞鉴曾三次到宁波演出。1944年,她十六岁时以艺名“小王其昌”演出于上海更新舞台。当年,由于抗战影响,王其昌演艺活动不景气,师徒三人(包括师哥宝宝)应“老大鸿寿”之邀回到宁波。在宁波“大世界”京剧舞台,她先后领衔主演了《乾坤圈》《铁公鸡》《杀四门》《翠屏山》《连环套》《骆马湖》《伐子都》《长坂坡》等剧目,受到观众热烈追捧。
小凤十六岁那年,师傅家的日子紧得过不下去了——王其昌脾气太倔,人缘不好,请他演戏的人越来越少。无奈之下,王其昌给王水松写了一封信,表露了想带两个徒弟(小凤和宝宝)到宁波演戏的心思。王水松自然知道王其昌的分量,他一接到信,就打算起班子。
师傅派小凤到宁波打前站。小凤出落成大姑娘,梳着两条长辫子,身穿阴丹士林布旗袍,走路从不抬头。除了练功、演戏,她很少在外面社交,朴素而规矩。坐上从上海去宁波的船,挤在嘈杂的统舱里,她的心像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欢快,一路上吃不下、坐不住,总嫌船开得太慢,恨不能马上回到父母身边。
当时京剧在宁波也很火,演出场地是宁波老江桥(灵桥)旁边的游艺场所“大世界”京剧舞台(现已拆除)。这次来宁波,小凤除了主演《四杰村》《花蝴蝶》等出,还陪师哥演《四平山》里的裴元庆,并在师傅的打炮戏《金钱豹》中饰演孙悟空。
小凤一出场,观众就拼命叫好,师哥的主角李元霸,演不过她的配角裴元庆。这一来,师哥不高兴,大妈(师哥之母)不高兴,王其昌也不高兴——只因她盖过了师哥的风头。王其昌训斥侄儿:“你一个小伙子演不过一个小丫头儿!”但是观众不理这个碴儿,照样给她喝彩,场场爆满,把个戏园子挤得水泄不通。
这次小凤有机会与父亲同台演戏,在《界牌关》(又名《盘肠战》)中,父亲演罗章,她演罗通。台下他是父亲,她是女儿;台上她是父亲,他是儿子,完全颠覆了父女俩在生活中的真实关系。叔叔大爷们调侃说:“闺女演老子,老子演儿子!”父亲不爱听,小凤听着也别扭。当时父亲已年近五旬,小凤趁机劝父亲:“您干脆甭演了。”父亲真的听了女儿的话,从此收山,回家赋闲,钓钓鱼,聊聊天,倒也自在。
父亲曾向麒派著名老生陈鹤峰传授过真刀真枪的把子功夫。后来陈鹤峰在上海大光明剧院演戏,听说在宁波演戏的“小王其昌”是俞见荣的闺女,便赶来捧场。小凤在台上演戏,陈鹤峰在台口摆了八只花篮,以示祝贺。
父亲对小凤要求极严,寄望很高。小凤在宁波初演《长坂坡》中的赵云,父亲看后,生气地批评她:“你演的什么?一点儿戏情都没有!”
小凤不服,辩道:“您那是老派,我这是新派,演法不一样。”
当时她正洗着脚,父亲正喝着酒,听了这话,气得从后面拍了她一巴掌,把洗脚水都打翻了。
为看女儿的戏,母亲也生了一场闲气。她用辛辛苦苦挣来的三块银元买了一张戏票,坐在前三排看女儿的戏。王水松看见,把母亲拉到一边,不让她坐在前面看。母亲生气地说:“我自己花三块大洋买的戏票,凭什么不让我坐在前面看我闺女演戏?”王水松说:“让你看清楚,你闺女就不值钱了,她不是俞月芬,是小王其昌!你坐在前面,人家一知道是你的闺女,这戏就没人看了!”
原来这也是梨园行规,“师门”重于“家门”,既拜了师,为女儿的身份便被为徒弟的身份所覆盖,这里没有寻常人家的女儿,只有“小王其昌”的名头。
这次来宁波,王其昌演了《闹天宫》《闹地府》《闹龙宫》《收六贼》等猴戏,都是西游记里的折子,小凤一一看会了。演了一段时间,王其昌想回上海,王水松见小凤已能挑起他的班子,便对王其昌说:“那你自己回去,把小凤和宝宝留下吧。”王其昌不允,说:“不行,小凤得跟我回去。”
王水松留小凤有两层意思,一是觉得她能挑起自己的戏班,二来想让她和师哥在宁波给师傅挣点钱,这也是为王其昌着想。可王其昌听不进去,也不领情,坚持要带小凤师兄妹一起走。
回到上海,还是门庭冷落,除了练功,师徒三人只好在家赋闲,生活日渐窘困。这时,王其昌的哥哥,小凤叫“二大爷”的王斌飞埋怨王其昌:“你就不该把宝宝和小凤带回来,应该听王水松的,他是为你着想啊,你这是失策之举!”
二大爷实际上是王其昌的经纪人,行话叫“挡手”,每次有人请王其昌演戏,必先与二大爷接洽。二大爷念过四年私塾,会拉胡琴,会演戏,口才也好,遇事比王其昌有头脑。
二大爷又说:“王水松留小凤是有道理的,他有班子、有人,他想让小凤当领班(即头牌,领衔之意),要不我再给他写封信吧。”
第一封信写去后,王水松没答应,说班子都散了,人找回来太难。二大爷又写了第二封,信中客气地说:“我这位三弟处理问题不周到,没领会您的好意……”说了一堆道歉的话,又问王水松成立班子还有什么困难,他可以把小凤和宝宝送过去。
不等王水松回话,二大爷就问小凤想不想回家。小凤一听,当然想回家了;又问她愿不愿意再回宁波,她说愿意,心想巴不得呢。二大爷说:“那好,咱明天就上船。”
二大爷特有计谋,谁都知道散班子容易起班子难。他思忖,这次我主动给你(王水松)把两个角儿送上门,你不起班子也得起。王水松心里也明白,一看人已来了,说:“你们二大爷这招厉害,班子还没起呢,先把角儿给我送来了。”于是他借了印子钱,把人马召了回来。
直到今天,俞鉴依然认为王水松是位善良的老板。在他的戏班里,头三天饭免费,且所有的演员都能带上妻儿一起吃饭。其他班子则没这条规矩。
1946年,小凤第二次到宁波演出,主要陪师哥演《雅观楼》《四平山》,得空就练叉和锤。她当时有个小小野心——当上《金钱豹》主演,非得自己演了才甘心。因为王其昌的看家戏《金钱豹》是不传徒弟的,以前小凤只是在戏中为师傅扮演的金钱豹配演孙悟空,没演过主角金钱豹。她是个有心人,一离开上海,就开始苦练这出戏的技巧,主要是练叉。《金钱豹》是武生应工,却要有“架子花”的味道,要求演员有过硬的基本功。除了耍叉,还有一排小翻、四十个旋子,接着还要跳十几个“铁门槛儿”。娴熟掌握这些技巧后,小凤主演《金钱豹》获得圆满成功,这出戏后来成了她的保留剧目。
当时小凤还没有掌握“锤把顶锤把”的技巧,她向师哥求教,师哥不屑地说:“你能练好‘把顶把’?我‘王’字倒写!”小凤一听,犟劲儿就上来了,每天起早贪黑勤学苦练,别人还没起床,她已经练完了晨功,一口气练坏了八对锤,终于练成了耍锤的各种花样和锤把顶锤把的绝活。在王水松的支持下,她还顶替师哥演了《四平山》里的李元霸,一演就是半年多。
这时,宁波的观众戏看得差不多了,正好温州有人来请,王水松便带着戏班转场温州。在温州,小凤遇见了盖叫天的次子张二鹏,他是参加上海一名武行头组织的演出队应邀来温州演出的,剧目是《闹天宫》。张二鹏很看重小凤的功夫,请她在戏中帮他配演哪吒。小凤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与张二鹏合作演出了几个月,留心学习他的路数和招式,将《闹天宫》从头到尾“搂”了回来——虽是“搂叶子”,具体的技巧还得靠自己苦练。
也是在温州,母亲提醒王水松,小凤已到满师年龄,该归还当年的拜师字据了——一满师经济上即可独立,母亲图的是自己掌握女儿演戏赚的钱。当时小凤已年满十八岁,十年前,她与王水松签订的拜师契约上明确约定七岁到十七岁为学徒期。小凤还记得契约上写着“……病死不管,打跑不究……”。
王水松拖着不想给,母亲就跟他吵了起来,实在闹得没法儿,王水松才拿出字据,交给母亲。
满师后,小凤深感在师傅门里学的三十几出戏不够用了。她意识到,要想在这一行里拔尖超群,还得不断研究新技巧。比如锤、叉、“出手”等,师傅门里没学过——师傅不会锤,不教叉,“出手”也从没见他用过。自己不能仅仅停留在师傅传授的技巧上,必须再提高一步。这段时间,正好有个上海的青年武生也在宁波演戏,小凤得知他在戏中耍锤,就常悄悄地去看他演出,记下招式,经提炼加工,花样翻新,再用到自己的演出中。比如她将耍锤运用到《乾坤圈》中,很能表现哪吒夺取胜利后的欢快心情。为了形象地展现哪吒“三六头臂”的本领,她还独创了同时耍圈、锤、风火轮三样的技巧。经过不断改进、创新,使这出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终成她的代表作。
在温州演出期间,小凤认了个干妈,四十来岁,胖乎乎的,特别喜欢她。“干妈”每天都来看她演戏,还经常到后台看她。温州干妈送给她一只金镏子,还给她扯了一件织锦缎的旗袍。从温州回宁波要坐大轮船,路上要走两三天,干妈又介绍她认识了一艘轮船上的船长和大副、二副,说好回去时帮她买船票。
温州的码头工人也很仰慕“小王其昌”,想请她在码头为工人们演一场戏。小凤一口答应了。工人们挺高兴——当时有的演员稍有点名气就看不起工人农民,请不动,不愿为下层人民演出。小凤身上没有这些毛病。演出结束后,工人们送她一套桌围、椅帔,题赠“小王其昌”,感激地说:“你答应在码头上为我们演戏,是给我们最大的面子。”
跑草头班,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一次小凤露天演出《乾坤圈》,突然刮起了大风,刮走了舞台的顶篷。台上的戏还在进行,可哪吒手中的锤却让风刮得怎么也“顶”不上了。但是观众却没有因为这恶劣的天气而原谅小凤的过失,一味地喝起倒彩来。小凤一肚子委屈,回到后台就哭出了声,心想连顶篷都刮跑了,这锤能不动吗?风停了,小凤擦干眼泪又上了舞台,把戏重演了一遍。这回,她那手漂亮的锤顶锤、把顶把,又赢回了满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期间,大妈提出让小凤给师哥做媳妇,母亲一口回绝了。师哥也对小凤母亲说:“当初王水松把小凤许给我了,这事还算数不算数?”母亲说:“我作不了主,你自己去问小凤。”
此前师哥曾向小凤探口风:“咱俩这事儿是当初王水松跟我叔叔说的。”
小凤一头雾水:“怎么还有这么件事?我怎么一点儿不知道?现在突然冒出来了。”师哥说:“这事儿我妈跟你妈说了,你妈让我问你愿不愿意。”小凤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从小就对师哥没有任何好感——他一直欺负她,她怎么会嫁给他呢?
师哥母子俩将求婚遭拒的事写信告诉了王其昌,王其昌生气地说:“那就别再叫‘小王其昌’了。”母亲也顶上了牛:“不叫就不叫,还姓自己家的姓!”
1947年,小凤第三次进宁波,改名俞少楼(这名字是宁波“干爹”给她起的)。从此,俞少楼挑起大梁,巡演于浙江各地。除了主演师傅门里学的《长坂坡》《伐子都》《两将军》《战马超》《盘肠战》《铁公鸡》《花蝴蝶》《四杰村》《乾坤圈》《安天会》等戏外,少楼还在演出实践中逐步丰富了自己的剧目。她和师兄演出挣了钱,除了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其余的全部寄回上海交给师傅。然而,她与师哥的“婚约”之事还没有完,最终是由干爹帮她“摆平”的。
小凤的干爹是常熟人,曾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团级干部,家里是大地主,膝下无儿无女,很喜欢京剧。以前他在乡下看过小凤的戏,每次都点她的《林冲夜奔》。小凤第三次进宁波时,他已辞去军职,当上了市电灯公司经理,听说小凤又回到宁波,便想认她做干女儿。小凤家的大门正对着他家的胡同口,每天演完戏,她都带着满身汗水,进家之前总要先站在院门口歇一会儿。他一看见她就过来问长问短,日子一长就动了“认干亲”的念头。事前,他找到王水松商量,王水松说:行啊。他便抬了一坛酒,带着金手镯、绸缎衣料、毛线、鸡鸭鱼肉等来到小凤家。没费什么周折,小凤的母亲就同意了。
“拜干爹”这事挺隆重,还登了报。从此小凤有了“牌头”,一提起来就说是谁谁谁的干闺女。旧时的女艺人认“干爹”是常事,无非是多一层保护伞,防止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和附庸风雅“捧角儿”的浮浪子弟骚扰。有时,这种关系会发展到比较暧昧的程度。但小凤与干爹相处始终形同父女,关键时刻,干爹也确实出面帮助了她。
那时小凤常去干爹家。干爹家住三进三出的大院,家里的豪华气派是她以前从未见过的。她原以为干爹的夫人是位年轻漂亮的太太,穿着时髦的衣裳和高跟鞋,烫着飞机头。及至见了“干妈”的面,她却愣住了,怎么是个穿着阴丹士林旗袍、梳着髻儿的农村老太太?完全不是她想象中的样子。
初次相见,她叫了一声“干妈”,干妈和气地应答,问:“你就是那个‘小王其昌’?”她把师傅王其昌不让她再叫这个名字的事告诉了干爹干妈,然后对干爹说:“我妈让您给我起个名儿。”
干爹是见过世面的人,也见过好多京剧名角儿,李少春、李万春、王少楼……他想了想说:“干脆叫俞少楼得了。”(武生演员名字从少、从春、从楼字的比较多)于是“小王其昌”成了俞少楼,“小凤”这名字也不再用了。打这以后,她告别了“小王其昌”时代,开始以“俞少楼”之名挂牌演出。
参军后,俞鉴隐瞒了“认干爹”的事,没敢向组织汇报。她怕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每次来宁波,少楼都要带一出新戏,这次带的是在温州从张二鹏处“搂”来,又经自己一番打磨、改造的《闹天宫》,演出地点还是宁波大世界。海报的宣传口径是“俞少楼巧耍四件闹天宫”,仍是天天满座。少楼将张二鹏在戏中耍两只圈、一杆旗,改成耍一只圈、一杆旗,外加一把锤,腰里再别上一根短金箍棒,独创出自己的“耍四样儿”——梨园行向有“南演北唱”之说,南方观众偏爱武戏,只要有所创新,就叫好又叫座儿。
这期间王其昌又想来宁波演戏,除了生计,他还打算为少楼和师哥的事与王水松理论一番。
王其昌来后,王水松还是按照惯例将他和少楼师徒俩拴在一起演戏,《走麦城》师傅演关羽,少楼演关平;《西皇庄》师傅演老英雄楚标,少楼演“赛花蜂”尹亮;《叭蜡庙》师傅演楚标,少楼演黄天霸……俩人一开打,观众就欢呼:“哎,老的和小的打起来了!”戏迷们就看爱这份儿热闹。
王其昌虽然倔强,但并不狭隘。改名的事并没有影响师徒关系,王其昌也不介意继续与少楼同台演出。他已人到中年,在上海时,少楼仿佛是他的一只臂膀,如今她回到宁波,他感觉好像缺了半边似的。有少楼陪在身边,他就觉得自己有希望——少楼能为自己配戏,也能替他挣钱。这次来宁波演出,王其昌又赚了个盆满钵溢。
出师后,少楼的包银再也不用给师傅了,全由母亲掌管。但王其昌一定要为少楼和侄儿的“婚事”向王水松“讨个说法”。他质问王水松:“我辛辛苦苦教了这孩子十多年,当初你说的话还算不算数?”王水松说不出个所以然,干脆躲到乡下不见面。
王其昌是火暴脾气,找不到王水松,就把气撒到少楼身上,还想说服她“认”下这门亲事。少楼无奈,只得以她和宝宝没缘分托辞。王其昌苦劝道:“这事你不乐意先放下不说。我年纪大了,身边没个帮手,你得跟我回上海帮我配戏,你这点戏还不够,我再多教你几出。我还可以把你介绍给黄金荣,让你在上海出大名,你再跟我一二年,咱们的账四六开、三七开都成,你拿大头。我在上海有房子,把你爸妈也接来跟你一块儿住……”
少楼一听,挺愿意,又学戏又出名,当然是好事,只要不提她和宝宝的事就行。但是母亲坚决反对。
“你今天跟王其昌上船,我立马在码头跳江,死给你看!”
“他说的都是骗人的鬼话!一回上海,你就真成了王家门儿的媳妇了!”
少楼还想跟师傅走,母亲继续以死相挟;王其昌很生气,准备跟她母亲论理打官司。
少楼陷入两难境地:一边是恩师,手把手教了她这么多年;另一边是母亲,母亲的话做女儿的又不能不听。她知道母亲性子十分刚烈,动不动就寻死觅活,但她思想上依然倾向于去上海发展。
少楼被两边扯着,心中特别烦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一天半夜,她爬起来,给自己想了两条路:一是出家当尼姑;二是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
少楼有个小姐妹叫屠宝娣,每天陪她上戏园子,晚上跟她一块儿住。宝娣知道了少楼的心思,怕她出事,每天寸步不离地紧盯着她,劝她说:“你这两种想法都不对,一不能死,二不能去尼姑庵。师傅没错,他老了,指着你帮衬他;你妈也没错,她没儿子,就指着你了。可是打起官司来你妈肯定输,因为你愿意跟师傅走。你那干爹不是挺有本事吗?找他想想办法啊。”
少楼一想,对啊,明天就去找干爹,他一定有办法。
干爹听少楼诉说了事情的原委,说:“这矛盾不难解决,我先听听王其昌要什么条件。”说罢就去见王其昌。
“王水松说小凤是王家门的人,现在又不承认,自己也跑了。这些年我在小凤身上费了这么多心血,我这不是白培养她了吗?”王其昌自有他的理。
“那你说怎么办,你提个条件。”
“我老了,子女又顶不上,小凤得帮我个一年半载的,可她妈死活不答应,那我的心血怎么补偿?”
“能不能用钱来解决?”
“这也是一条道……”
……
于是干爹作主,让少楼把他送给她的那对龙凤金镯给了王其昌,又拿出几只金戒指作为谢礼。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这也算是“三进宁波”中一段不和谐的插曲。
挑班演出的三年多时间里,少楼学会一出戏就上演一出戏,主要演武生戏,兼演老生,反正观众喜欢她,她演什么戏观众都爱看。在不间断的艺术实践中,少楼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拥有了自己的观众群体,在江浙一带,尤其是宁波周边红了起来。在宁波,每天都有人打问:今天有没有“小王其昌”的戏?无论是卖菜的戏迷还是农民,只要有她的戏,就争相买票去看。
半个世纪后,对王其昌师徒当年在宁波演出时的火爆场面,宁波的老观众仍记忆犹新。
早年紧靠宁波老江桥(灵桥)的“大世界”,这是宁波地区远近闻名的一个游艺中心,主要的游艺剧团是以王洪儿的儿子王其昌和王其昌的弟子筱(此处通“小”,下同,原文如此。作者注)王其昌领衔的京剧团。虽然时隔四五十年,回忆王其昌师徒的表演,印象还极深。
王其昌工文武老生,亦擅演红生戏,凭着他武生的基础和一副好嗓子很能叫座。他的弟子筱王其昌是坤角武生,长靠短打会戏很多,武功基础扎实,动作规范,迅疾脆帅,“飞脚”打得又高又响。我曾看过她演出的《林冲夜奔》和《白水滩》饰十一郎穆玉玑、《驱车战将》饰南宫长万,表演干净利落。她几十个旋子下来,还能边舞边唱,真是女中魁元。尤其在《驱车战将》中扮演南宫长万,一手驱着老田座车,又要与鲁国官兵交战,唱念做打并重,很能获得观众好评。
王其昌演出的《斩经堂》中,吴汉劝慰其妻时的一段唱:“贤公主,休要跪,休要哭……”经常被观众传唱。王其昌还经常贴演关公戏《华容道》《走麦城》。配演关平的就是筱王其昌。麦城被擒,她纵身跃起的“锞子”摔得干净利落,与乃师王其昌扮演的关羽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后来听说因为儿女亲事师徒反目,筱王其昌复名俞鉴挂牌演出。以后我去上海上大学,再没有听到这位坤伶的消息。如此色艺双绝的京剧坤角武生再没能看到第二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筱王其昌有时还反串演出,我曾看过她演出的《借东风》反串诸葛亮,一段“学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经常赢得满堂彩。
这是一位当年的老观众在《王其昌师徒与宁波“大世界”》一文中的记述。只是其中“因为儿女亲事师徒反目,筱王其昌复名俞鉴挂牌演出”的说法不甚确切。虽然母女俩拒绝了王其昌侄儿的求婚,却还没有闹到“师徒反目”的程度,事后师徒俩仍多次同台演出;“俞鉴”是她参军后自己改的名字,而当时她是以“俞少楼”之名挂牌的。
三进宁波期间,日本侵略者投降之前是时局最紧张的时期。一次,戏班转场到少楼的老家新昌作短期演出,班主雇人挑着行头和装帽子的圆笼,一行人不分昼夜,战战兢兢地赶路,几百里山路,全靠一双脚。前有国民党,后有日本兵,大家都很害怕:一怕国民党勒索要钱,二怕日本鬼子行凶杀人。一路上没有客栈,也不见饭馆,饿了只能从沿途的村民手中买几个红薯充饥。途经天台山时,正当夜晚,山间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他们举着松明子照亮,整整走了一个星期才回到老家,在沃洲湖畔的三坑真君殿连演了三天戏。
一听说有戏看,乡亲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把寺院挤得水泄不通。戏台正对着大殿,演员演戏时除了台下的观众,还须面对一群泥胎。那次少楼主演了《铁公鸡》和《乾坤圈》。
这次演完戏,班子就暂时解散了。梨园传统,每年6月,天气渐热起来后,戏班就要封箱歇夏。一来防止戏装被汗水浸泡后掉色变旧,二来可让演员回家养息,恢复状态。
少楼回到母亲的老家大市聚镇下求村,继续练哪吒的锤。
旧时酬神演戏,祠堂庙宇多建万年台(戏台),1952年,新昌县曾进行过一次普查,全县553个自然村,共建有827座万年台。其中尤以城隍庙、镜澄埠、八堡龙亭等戏台建筑风格最为别致。俞鉴当年演出的三坑真君殿戏台是其中之一。
2006年秋,笔者专程前往俞鉴家乡新昌大市聚镇沃洲湖畔的三坑真君殿寻访旧迹,但见寺庙依旧、大殿依旧、大殿对面的戏台依旧——尽管有可能经过不止一次的重修,但样式、格局应与当年无异。
在戏台近旁,笔者遇见一位七十五岁的老者,问他知不知道“小王其昌”。他说知道,他小时候在这里看过“小王其昌”的戏。他还记得她是个女孩,只比他大两三岁,“那一身武功,好生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