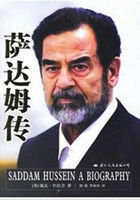这辈子究竟演过多少戏,俞鉴自己已说不清了。若不是老伴儿细致,儿女操心,在她几十年的唠叨中“艺海拾贝”,整理出一份详尽的目录(见本书附录“俞鉴剧目汇览”),这一生演过的“戏码”,她真的说不全了。
根据老伴儿和孩子们的统计,俞鉴一生总共演了六十多出戏。除了专工的武生戏,她也反串过不少花脸戏和武旦戏,如《火烧柏望坡》里的夏侯墩,《金雁桥》里的张任,《金水桥》里的秦英,《借东风》里的诸葛亮,《挡马》中的杨八姐,《武松打店》里的孙二娘……
为什么一个女武生要学演这么多出戏,且剧目又如此庞杂呢?这是因为,无论是从师傅的要求,还是从俞鉴自身的愿望出发,都希望能多学戏、多演戏,尝试各种剧目中的各种角色,探寻多种可能性,以达到既能文、又能武,“文武昆乱不挡”的境界——戏剧表演艺术的至高境界。李少春、关肃霜,还有许多京剧表演艺术家走的都是这条路子;大凡武生演员,也都渴望能够走通这条路。
年近耄耋,俞鉴说出了一句感言:“旧社会给了我技艺,新社会给了我灵魂。”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旧时戏曲艺人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即使入宫当差,有了“内廷供奉”的名分,也还是摆脱不了屈辱的地位。在旧社会里,艺人只能一门心思学艺,师傅怎么教就怎么演;跟着戏班“跑码头”,人家让演什么就演什么。除了一身技艺,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老话说“一招鲜,吃遍天”,所有的演员都拼命往技巧上琢磨,每个人的独门绝技都自己牢牢把着,绝不外传,生怕别人学了去。行话说“宁送十亩地,不让一出戏”。技艺就是吃饭的“本钱”,教会别人,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
像所有的旧艺人一样,俞鉴在旧社会里练就了一身技艺。加入革命队伍后,她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懂得了什么叫“双百”方针和“为人民服务”。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痛苦磨炼,才有了后来的进步,也才有了今天。
让俞鉴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的艺术道路基本上是平顺的,个人命运也没有遭遇大起大落和非同寻常的坎坷。作为一名从旧时代走来的女艺人,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既没有像有些女伶那样曾经受到失去尊严的折磨,也没有像一些艺坛姐妹那样曾经遭受不堪忍受的凌辱。在这一点上,她觉得自己尤其幸运。
当年,俞鉴和老四团的同仁们毅然舍弃北京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大西北。从部队到地方,从北京到宁夏,工作和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团里的主要演员,俞鉴的演出任务一直很重。然而,无论工作环境优劣,物质条件好坏,她从未有过丝毫抱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1958年10月,到宁夏仅仅一个月,她就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一年后转为正式党员。入党后,俞鉴的工作热情更高了,一心想多演戏、演好戏,不仅几十年中一直担纲主演,还相继担任了宁夏京剧团学员队队长、演员队队长、副团长等职务。离休后,她又担任了团里的艺术指导。
作为一名女武生演员,俞鉴不仅要和大家面对同样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比起男性演员,还须克服生理上的特殊困难。就拿练功来说,俗话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盖叫天一生坚持练功,到老不辍,俞鉴也是这样。
自打学戏那天起,俞鉴练功的习惯坚持了一生,直到晚年中风后才不得不中止。平时不论晚上演出多累,第二天的“早功”,她从不省略。从初潮来临到每月的“特殊情况”,及至生孩子、坐月子,一律照练不误。在这方面,俞鉴琢磨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她根据女性生理变化的特点,将女武生的练功划分为少年期、青春期、婚后期、怀孕及产后期四个时期,不同时期的练功有不同的“量级”,时间或长或短,数量或多或少,程度或剧烈、或舒缓,但只有一样——不能省。
对付“特殊情况”,俞鉴的办法是勒紧腹带,垫好下身——以前是用厚厚的粗草纸,后来条件好了改用棉花。练得太狠或演戏太累的时候,她下身流出的是一块块深紫色的淤血。母亲心疼她,到药铺买来益母膏,看着她喝下去,一来活血化淤,二来缓解疼痛……
每天早起练功,夏天六点,冬天七点,自觉自愿,雷打不动。喊嗓子、压腿是必做的功课,和过去在师傅门里练的完全一样。踢腿、扳腿、打飞腿……这是一套腿上的功夫,有固定程式,每天必练;毯子功,跑虎跳、砸踺子、翻小翻……锤、圈、枪——观众最爱看的“耍三样儿”,更须天天练。
俞鉴习惯独自练功,自己给自己规定数目,提要求,把关,其着魔程度近似于医学上说的“强迫症”,自己却因此受益匪浅。因为这样练功,既紧凑,又出效果,时间利用率也高。大家一起练,七八十个人转上一圈,只能练一样功夫,松松垮垮,滥竽充数,流于形式,练不出底气。
怀孕五六个月上,显了怀,挺着大肚子练功不方便,也不能上台了。这时团里如果没有什么工作,她就挑几个条件较好的小学员过来,辅导他们练功。团里的肖英红、李新云、孙连柱等几个年轻演员,她都带着练过。
刚生完孩子,腿踢不起来了,也跳不动了。月子里她一面补身体,一面试着在桌子上慢慢压腿,或按着桌子练习弹跳,逐渐加大运动量。孩子刚满月,她就恢复了“小练”,一两个月后再和大家一起练。这时“打飞脚”还“飞”不起来,翻“台蛮”也还不能做到位,逐渐逐渐才能提住底气。只有生下孩子,坐完月子,她才和大伙儿一起,慢慢儿“缓”着练,一般百日之后,差不多就可以恢复到上台演出的水平,团里也开始给她安排演出任务。
俞鉴生三个孩子都是这样,团里也知道她的情况。所以直到五十多岁,她的体力和功力还基本保持着二三十岁时的水平,也才没有“红在婚前,倒在婚后”,一直演到五六十岁高龄。
由于坚持练功,多少年来俞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和水平。也是由于坚持练功,她演戏从不松散,以圆场功为例,从台口亮完相转身下台时,她能一口气“提”到后台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才喘上一口气。为此,张元奎团长曾说:“我们团里有两个‘气儿’最长的,一个是张正武,一个是俞鉴。”
为了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俞鉴不知想了多少办法。1960年代,我国尚未普及先进的节育手段,俞鉴找到银川中医院一位熟识的老中医,说:“请您想办法把我的子宫破坏掉,让我别再怀孩子。”老中医给她下了几副比较“狠”的药,可牙都吃肿了,也没能“破坏”掉子宫。
这以后又怀了小三儿,俞鉴特别苦恼,差点去做人工流产。被家人制止后,她故意翻小翻、前桥,拼命加大运动量,想把孩子“颠”掉,谁知各种手段都无济于事。她又四处求人寻找偏方。团里管服装的孙大爷给了她一个偏方,却没想到这“偏方”竟是一把绿豆。孙大爷说:“绿豆是凉性的,你生完孩子第二天偷着把它吞下去,以后就怀不上孩子了。”俞鉴信了孙大爷的话,生下老三,她果真吞下了一把绿豆。
三个孩子,三次怀孕,每次俞鉴都是带着身孕到外地演出,每次也都是怀到四五个月上才停止演出。怀老大五个月时,身子已经出怀,她勒紧腹带在北京演出全本《岳云》,两小时的文武戏演下来,累得见了红,她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又上了台。老二怀到四个月上,她在广西演《陆文龙》,当时已担任团总务科长的梁仁华怕她出事,特地在剧院门口备了一辆小轿车——一旦情况紧急,立马送她上医院。老三怀了三个月时,她又到东北演《劈山救母》,还是一辆轿车“候”在剧院门口……
怀孕、生子对女武生演员来说是一大“关”,平时的“小关”就更多了。演出时遇上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女同志的“特殊情况”……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演出都是硬任务。对付这一切,俞鉴的办法只有一个: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有一年在太原演出,正值酷暑天气,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俞鉴主演的《十八罗汉斗悟空》连续演出了近四十场。这期间,她脸肿了没有退却,“例假”来了仍是一声不吭,一直坚持到演出结束。
她这一辈子,付出了许多,也得到了许多。有没有遗憾呢?有,怎么会没有呢?
1980年代以来,京剧开始走下坡路,越来越不景气。演了一辈子京剧的俞鉴,心中不免有很强的失落感。一想到京剧是这样的现状,她心里就发酸,直想掉眼泪。有段时间,社会上风传宁夏京剧团要解散,她心中更加难过,甚至想:假如真有这一天,她希望能把宁夏京剧团的演员们分配到待遇稍好一些的单位。直到1990年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纪念活动,掀起了新一轮宣传攻势,京剧又显出一丝转机,这些年来似乎又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她这才感到些许舒心。
三个孩子中,只有老大京平学了京剧,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京平条件不错,悟性也好,在学员队里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跟头翻得最“飘”。基本功过关后,京平便开始饰演样板戏里的一些群众角色,《红灯记》《龙江颂》《沙家浜》……都是龙套;直到后来,京平在宁夏青年演员汇演中获奖后才开始担纲,先后主演了《乾元山》里的哪吒,《十八罗汉斗悟空》《闹天宫》《悟空出山》等,都是她这个做母亲的多年以来常演不衰的剧目。近几年,京平在宁夏京剧团创编的《新闹龙宫》中饰演孙悟空一角,这出戏在中国第四届京剧艺术节上获得了特别奖。
儿子接了自己的班,又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她一方面感到欣慰,一方面还是感到遗憾——京平起步太晚,十四岁才开始学戏,而学武生一定得像自己这样,要有“幼功”才好。那些年自己在学员班工作,不能给儿子“开小灶”,回到家里,才能给孩子“吃点儿偏食”。若不是这样,京平完全可以达到自己的水平和高度。如今,长期的舞台生涯造成的体力透支,已届天命之年的京平患了心动过缓症,不能再做连续、激烈的武打动作,她又时时为儿子的身体担忧。
一些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巧、绝招,她还没来得及教给学生,自己就老了,因为生病和体力下降,做不动了。比如她擅长的背手接枪、打飞脚……至今无人继承。王其昌教的南派武生戏《长坂坡》,具有突出的南派“重武”特点,而北派演这出戏不讲究“连念带耍”,所以有些东西至今亦无人继承。她常想,假如儿子能早下苦功,也就继承下来了——可京平学的时候心中有杂念,他担心自己掌握不了这些高难技巧,反而崴了脚。还有,像她那样做到位的“乌龙绞柱”也没有人继承——她的“绞柱”和别人的不同,难度更大,因而更惊险。
虽然早已离开了舞台,排练厅对她仍有着极大的诱惑力。无论盛夏还是严冬,有事没事,她的双脚常会不由自主地踏进宁夏京剧团那间颇具历史感的排练厅,不是在把杆上压压腿,就是在地板上下下腰。不为别的,就为这一辈子的习惯。青年演员排戏,她也常站在旁边默默观看,心中暗暗为他们鼓劲儿。长江后浪推前浪,如今,新一代武生演员比起她这样从旧时走来的前辈演员来说,不仅在技艺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人物塑造上更是可圈可点。今非昔比,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又赶上了好的时代。对于这些,她觉得十分欣喜。她愿意看到年轻一代迅速成长,接过老一辈艺术家手中的接力棒,使京剧艺术后继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
离休后,她几乎每天都到排练厅去看本团的这些孩子(学员)练功(像上班一样准时),大的、小的都看,一心想物色几个基本功好、接受力强、又懂术语的孩子“拨拉拨拉”。这一看“看”出了问题,她发现“串翻身”这个技巧,孩子们都没有做到位——不仅在本团,就是在全国,也很少有人能做到位。她心里很着急,这些动作都是老先生教给她的,是小时候用无数次肚肠绞痛的代价换来的。如今自己患脑血栓左手“封闭”,动不了,她就让京平代为示范。还有一些剧目,也没能传给下一代,如老戏《长坂坡》《周瑜归天》《雅观楼》《四平山》等。
这样想着,每天出来遛弯儿,一遛就遛进排练厅。一进门,大的叫老师,小的叫奶奶,她心里特别高兴,觉得自己还有用,还能出力,还有想法。
不久前,她相中了一个北京的小女武生,条件很好,现在能演杨文广,观众也很喜欢她。她想收她为徒,把自己的东西传给这孩子,在有生之年,尽自己最后的力量培养后生。于是她给原宁夏京剧团花脸演员,后调往北京艺校任教的高长清(现已离休)打电话:“我看上了一个小闺女,叫徐莹,是梅派琴师徐兰元的孙女,她爸爸和叔叔都是唱武生的。”
不想高长清却在电话里“打击”她:“俞鉴,这事儿你不要想了,人家是世家出身。再一个原因,你教的东西人家接受不接受还两说呢……”她想想也是。还有常香玉剧团里的一个演沉香的女孩子,功夫也不错。这俩孩子条件都好,动作也都能做到位。她想得挺简单,自己也知道实现不了,可就是不死心。想到自己明年就八十岁了,正赶上北京奥运会,她很想去趟北京,见见这俩孩子……
这些都让她感到遗憾。
但是她不悔。她这一辈子,为舞台而生,为京剧而活,事业是自己选的,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有什么好悔呢?
人老了爱操心。这几年,她常在电视上看到关于腐败的报道,她担心搞企业的女婿与经济的联系太紧密,每每给女婿打电话,她总是说:“妈对你只挂牵两件事,一是你‘发’了以后,不要忘了工人,一定要处理好劳资关系。第二,你经常坐飞机,我担心你的安全,最好改坐火车行不行?”
女婿的回答是:“妈,请您老放心,第一我不会贪污腐败,因为我胆子小,不会犯这种错误。第二,不坐飞机这可办不到,对于像我这样搞企业的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工作节奏快着呢,要是坐火车,把业务都给耽误了。您老放心,我命大着呢!”
有一年,老两口到浙江南浔女儿女婿家小住,女婿对老伴儿说:“报纸上表扬一个女企业家,说她劳资关系处理得好,我要向她学习。”年轻人说到做到,不仅劳资关系和谐,厂里还出资二十多万元,送二十几个贫困人家的孩子出去读书、深造。她和老伴儿亲眼看见墙上挂的女婿获得的各种奖励和奖状,看见厂里的几百号工人对女婿这位带头人的满意和信赖。她终于放下心来,高兴地说:“好!好!小江(女婿学名钱江)继承了妈妈的传统!”
宁夏京剧团至今仍驻扎在银川市兴庆区文化东街,当年老四团刚来宁夏时那个1958年的大院里,大多数演职员和家属也都长居于此。几百号人在这里办公、生活,繁衍生息,到明年(2008年)就整整五十年了。
凡是进过这个大院的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模样。走进大院,恍惚间你会觉得自己一头撞入了很久以前的某一个历史瞬间,时光也仿佛流转回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某一时刻——一条水泥铺就的陋巷,青、红砖或土木搭就的陋屋,屋墙斑驳,杂草丛生。近年在银川市整治陋街旧巷工程中几乎绝迹的小煤房、小伙房,在这里仍像膏药一样贴在楼房一隅,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如此面貌,使这个大院在日渐亮丽的银川,看上去更像一块久已撂荒的“飞地”,全然没有一点“单位”的影子——与其说这里是一个剧团,不如说更像一个几十年前的人民公社社部,或是一家乡间的什么机构。据说有位出身于这个剧团、现今身居高位,已是全国电视界“大腕”的人士来此故地重游时曾说,他打算以这个大院为实景,拍摄一部反映昔日梨园生活的电视连续剧……
俞鉴和老伴儿至今仍住在大院里1986年团里分配的一幢旧楼房中。进了老两口的家,映入眼帘的是破旧的钢窗,灰暗的水泥地面,斑驳的墙面和简陋的陈设,从未进行过任何“装修”,也没有现代风格的厨房和卫生间;一台看上去很有些年头的老式双缸洗衣机,水龙头也都是那种镀锌、旋钮的老款;客厅和卧室除了电视、电话,没有一件时新的家具、用品……
这样的“居住品质”,几乎可以用“寒酸”二字来形容。然而,简朴的生活丝毫不影响老两口享受生活乐趣,不妨碍他们相依相伴,共度晚年时光。
就在最近,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大院已被列入“开发”规划,不久的将来,它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届时,大院里的居民将一律被异地安置,庆贺乔迁之喜;宁夏京剧团也将迁往拆迁多年、至今尚未修建的原银川红旗剧院旧址。
听到这个消息,俞鉴半是欢喜,半是难舍。欢喜的是自己和老伴儿终于能够告别简陋的旧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体验一回“现代化”的方便和美好;难舍的是大院里终日萦绕耳鼓的京胡声,排练厅中孩子们的翻跌扑打,小剧场里青年演员们正在排演的新、老剧目……
思忖再三,她只向团里负责安置的同志提了一个要求:为她找一处离剧团新址较近的二手房。在今后的日子里,她要按照自己的老习惯,天天到团里看孩子们翻筋斗,日日聆听悠扬悦耳、绵延不绝的胡琴声……
闲暇时,俞鉴最大的乐趣是坐在沙发上,和老伴儿一起收看央视戏曲频道的节目。不光看京剧,越剧、豫剧、秦腔、黄梅戏……只要是好戏,一出也不能少。那五彩缤纷的戏装,生旦净丑的扮相,刀枪剑戟的飞舞,翻跌扑打的技艺……仿佛将她引入了一条时间隧道,构成了她全部的记忆时空。
穿越一帧帧色彩绚丽的画面,年近耄耋的俞鉴恍如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回到了“老大鸿寿”戏班,回到了上海滩,回到了宁波“大世界”……
她仿佛看见了弄堂里的垃圾箱,大新公司六楼的京剧舞台,卡尔塔日罗马剧场沸腾的观众席;仿佛听见了北京梨园剧场戏迷、票友不息的喝彩……
她看见了父亲,看见了母亲,看见了淹没在沃洲湖底的故乡青坛村……
她仿佛变回了一个孩子,穿着戏剧里的服装,翘着冲天小辫儿,在红毹氍上翻跌扑打、咿咿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