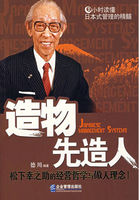1950年,皖北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赈灾义演。浙江省也组织了赈灾演出。俞鉴所在的浙江军区京剧团全体参演,邀请盖叫天、谭富英、小盖叫天(盖叫天三子张剑鸣)、杜近芳、杨盛春、郭元祥等名角,以及上海的一些“名票”联袂演出。
这次演出是军区京剧团与地方剧团的首次合演,团里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完成助演、配演,整台剧目文戏多,武戏少。演出之前研究参演剧目时,团领导挺犯难,说这次请来的都是名角儿,咱们拿什么戏开锣才合适呢?全本《武松》和《关公之死》都太长,其他剧目也不适合,最好是时间短、内容精的传统武戏。这时有人建议说:“就拿俞鉴的《乾坤圈》吧,短小精悍,又有武打技巧,用这出戏开锣,既能给几位名角儿留一个好印象,也显得我们部队的京剧团不是没有像样的主演。”当时,团里最拿得出手的武戏就是俞鉴主演的《乾坤圈》。
就这样,杨盛春的《战马超》(即《两将军》)《武文华》,盖叫天的《卧虎村》,小盖叫天的《金钱豹》,加上俞鉴的《乾坤圈》,这五出戏组成了这台节目的武戏阵容。
谁也没有料到,最受欢迎的竟是年仅二十二岁的小女兵俞鉴主演的《乾坤圈》。论当时的名气,她根本无法与前几位“大师级”的艺术家相提并论,但由于她是年轻女性,又是解放军里的女武生,这使平日看惯“须眉”武生的观众和戏迷感到耳目一新;加之她技艺超群,表演和武打都十分精彩,不仅观众叫好不绝,也得到了前辈演员的高度评价。
俞鉴当时并不知道,她在台上表演的时候,郭元祥、杨盛春等著名演员就在大幕里的台口两侧观看,边看边夸:“这女孩子真棒!想不到军队的剧团里也有这样好的武戏!”还说当时达到这种水平的京剧女武生,连北京也不多见。
在长达半个月的赈灾义演中,俞鉴先后主演了《乾坤圈》《战马超》《卧虎村》《李家店比武》《洗浮山》等剧目。演出盛况空前,她这个扮相英武、武艺高强的青年女武生,也给盖叫天这位艺坛名宿留下了印象。
不久,团里派俞鉴和武生演员王天柱到盖叫天先生家中,请盖老为两名年轻演员指导表演艺术。
盖叫天本名张英杰,原籍河北,八岁入天津“隆庆和”科班学戏,十岁登台,既工武生,也工老旦、老生,幼功深厚,技艺精湛。十二岁到上海后改学文戏,首次在沪登台;其后随班赴汉口,演出于“天一”茶园和“满春”茶园,以《定军山》一剧最受观众欢迎。十五岁应上海春仙茶园之聘抵沪,从此改演武生戏,常演剧目有《伐子都》《金雁桥》《界牌关》《花蝴蝶》《长坂坡》《武文华》《蜈蚣岭》等。1904年十六岁时由杭州织造局和上海洋务局举荐,清廷拟召其入宫内供奉,盖叫天拒不奉召。二十岁回上海,相继在“老丹桂”和“丹桂第一台”演戏,此间适逢梅兰芳初次来沪演出,盖叫天与梅兰芳同台演出。
辛亥革命前夕,盖叫天坚定地反对清廷统治,支持革命艺人演出反清戏剧。1912年二十四岁时首次赴北京演出,两年后加入上海天蟾舞台,演出达五年之久。此间创排多出剧目,先后与冯子和、赵君玉、小杨月楼等名角同台演出,并与第二次来沪的杨小楼在天蟾舞台合演《莲花湖》和《义旗令》。二十八岁时二赴北京演出,此后至上海解放前,先后演出于上海申江亦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黄金大戏院等近十家著名舞台和戏院,排演《乾坤圈》《七擒孟获》《楚汉相争》《西游记》《狮子楼》《武松》《三岔口》等多出剧目。
盖叫天曾因不愿受资本家的挟制而遭排斥,也曾遭流氓逼迫而停演。尤其是1923~1933这十年间,除赴南昌、汉口、宁波、开封等地作短期演出外,长年困居,得不到整期签约演出的机会,以致生活窘困,靠典当、借贷度日。但他不以为苦,长年坚持练功不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盖叫天获得了新生,他积极参加义演和社会活动,曾在怀仁堂为毛主席演出,参加上海市戏曲界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演出,还拍摄了纪录片《盖叫天的舞台艺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先后获文化部荣誉奖,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浙江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主席。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为他举行了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盖老在会上作了题为《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中国共产党》的发言(后收入《粉墨春秋》一书),感人肺腑。是年盖老已六十九岁,仍赴江西、湖北等地,深入部队、厂矿为工农兵演出,并在杭州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冒雨撑伞,步行至盖老家探望。1971年,八十三岁的盖老在杭州因受“四人帮”迫害而含恨辞世。
盖老一生勤学苦练,善于思考,青年时期在武戏技艺上便有很多独创,中年以后更是深入钻研武生戏的人物形象塑造,着力在“武戏文唱”中下工夫,创立了武生流派“盖派”艺术,演艺水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最拿手的两出戏是《三岔口》和《十字坡》,人称“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周恩来总理称赞盖老“勤学苦练,几十年如一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陈毅同志也曾为盖老题词:“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先生这样赞美盖老的表演:“快起来如燕掠波,舒缓之处像春风拂柳。动起来像珠走玉盘,戛然静止就像奇峰迎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盖老1934年在上海大舞台与陈鹤峰合演《狮子楼》时不慎摔断右腿,断骨穿靴而出,后为庸医所误将腿骨接错。他以超人意志以伤腿猛击床栏复断,另请医生重接,两年后腿伤痊愈复出。这段故事在艺坛传为佳话,作为后辈武生的俞鉴自然十分景仰。
盖老长住杭州,故居位于西湖风景区赵公堤旁的金沙港畔,雅号“燕南寄庐”——从这名字可以感受到盖老的绵绵思乡之情。盖老的家,建筑风格南北交融,既有南派的白墙黛瓦,又有北派的四合院和围廊(“文革”期间,盖老的住宅被占为民居,现存建筑仅为正厅“百忍堂”和左右厢房),是一处清幽雅致的所在。
来到盖老的住所,俞鉴和王天柱自报家门,说是解放军京剧团的演员,盖老客气地将他俩迎进家中。时年六十有二的盖老给俞鉴的印象非常精神,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老人。
进到室内,宽敞的客厅散发出淡淡的檀香味儿,八仙桌、太师椅、茶几等都是红木,摆法别具一格,很有品位。墙上挂的也是红木匾额,几个有年代的大瓷瓶十分气派。
落座后,俞鉴自我介绍说是王其昌的徒弟。盖老说知道,他听说过。一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她在上海已小有名气;还有一层,王其昌是盖老的侄女婿。论辈分,俞鉴得叫他“盖爷爷”。
盖老对俞鉴说:“我看了你的戏,功底不错。”第一次与盖老“零距离”接触,两个年轻人充满崇敬之情,恭敬地期待盖老的教诲。
盖老沉吟片刻,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他说,他亮相的造型来自寺庙中四大金刚、五百罗汉的神情;平时练高、矮相时,则先用家里的古董花瓶摆好位置,边看边琢磨。
望着燃香的袅袅烟雾,盖老眼神迷离,说他“跑圆场”是看着香雾绕的“弯儿”琢磨出来的;还有,马趟子怎么走才漂亮,亮相怎样才能摆得好看……这些都是他经常琢磨的。又说他最爱逛寺庙。
不知不觉间,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上午十点多钟,盖老起身说,该给他儿子练功了。自小在师傅家练就“眼力见儿”的俞鉴自然明白,这就是下“逐客令”了。她早已听说盖老家有间屋子是专门给他三儿子“小盖叫天”(张剑鸣)练功用的,但具体练法严格保密,外人看不到。
那段时间,两个年轻人接连去了两三次盖老家,尽管每次盖老的话都说得不多,但她仍然觉得颇有收获。比如盖老向他们示范过几个武松的动作,摆过几个英武神气的亮相,都是全本《武松》里《打虎》和《狮子楼》里杀西门庆的“相”,盖老还用花瓶给他俩摆出几个高、矮相。
回来后仔细琢磨,俞鉴越琢磨越觉得盖老的话有道理。他讲戏情和戏理,主要是怎样向生活学习,只是不涉及具体的技巧而已,更多的东西要靠自己去“悟”。
具体到自己常演的《乾坤圈》,俞鉴当然知道此剧是由盖老所创。1919年,盖老的母亲去世后归葬杭州,在杭州住的半年时间里,盖老曾为创造《乾坤圈》中的哪吒这一形象而苦练乾坤圈舞。这出戏是俞鉴的开蒙戏之一,从十四岁首演起,到如今不知演绎了多少遍。现在她有机会在盖老家中亲聆盖老的教诲,又怎能不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向盖老学习更多的东西呢?冥冥之中,她觉得自己与盖老仿佛是有缘分的。
俞鉴决心学习盖老从生活中寻找表演依据的好经验。她想,既然盖老能从庙里的金刚、罗汉身上找“相”,我演的哪吒是小孩,为什么不能从学生身上去找“相”呢?学生也是孩子,他们在放学路上互相逗闹,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大的欺负小的,小的不服,以哭反抗……这就是现成的“模特”呀。还可以从儿童玩耍时的动作中去找“相”。当时杭州城站火车站站台的宣传画里有小学生跳绳、扔皮球的画面,俞鉴特地去看过很多次,仔细揣摩他们的神态和动作。后来,她将《乾坤圈》中哪吒被石矶仙打败后手哆里哆嗦的程式动作,改为抱头逃窜,运用到演出实践中,得到了同行的首肯和观众的接受。摆圆场时,她也仿照盖老的“香烟绕弯儿法”来做,亮相则按照孩子的特征去做,凡是被同志们认可的动作,从此便固定下来。
用心琢磨的结果,使她的表演更加真实可信。从此,俞鉴每演一场戏都有改进,团里的墙报表扬她的戏有进步,说她演得“像个孩子的样儿了”。
这是俞鉴初次尝试对《乾坤圈》进行小的改动。最大的改革是在后来,她花费了整整三十年时光打磨《乾元山》。
1950年代后期,盖老积毕生心血,口述了自传体记录《粉墨春秋——盖叫天舞台艺术经验》(何慢、龚义江记录、整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本书与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和周信芳先生的《周信芳舞台艺术》齐名,生动地记述了盖老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貌,堪称经典,也是任何影像资料所不能替代的。
俞鉴家中至今珍藏着盖老这本首版于1958年、再版于1980年、定价仅为一元六角的书。翻开这本如今已破旧不堪的书,字里行间布满或红、或蓝的横线和圈点——这是俞鉴在反复学习、琢磨盖老的演艺经验时,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所作的标记。她希望自己能将盖老的体会“化”为自己的体会,将盖老的经验“化”作自己的经验,常学常悟,常演常新。
俞鉴从盖老处获益匪浅。她一生都是盖老的崇拜者和“盖派”艺术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