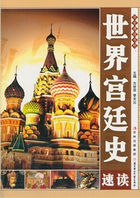我的手机里有母亲的一张照片:穿着对襟布扣衫的母亲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本书在看,面容专注而宁静,仿若名媛,仿若大家闺秀。这张照片是我母亲从乡下到我这儿度中秋时,我在一旁偷偷拍下来的,母亲没有发觉。
母亲78岁了,眼神依旧好,穿针走线都不在话下。但是,母亲看书,却令我没有想到。因为,我的母亲,是真正的大字不识。她会写的字只有三个,是她繁体字的姓和名,会认的字,多一个,是我父亲及她的儿女们的姓——一个“谢”字。
我家客厅的茶几上堆了好几本书,母亲常常会一本本地拿起来,一本本地翻。国庆节前一天,母亲见我下班回来,满脸的皱纹笑得如花瓣儿一样,她把书里面的一个个“谢”字指给我看,问:“这是你的名字吧?”这些书上,有些有我的名字,但大多数都不是,除了本家同姓的人名外,像感谢、酬谢、谢顶、凋谢这样的构词,也多得很。母亲敢这么肯定地指认给我看,一定是因为她听人说她的儿子会写文章,书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她还指着一本登有我照片的杂志对我说:“这本书上的照片,就你的像最小。”母亲语气里透着些骄傲,脸上却有些许不高兴,仿若是出书的把相片登小(与其他配照相比)了,亏欠了她儿子似的。
母亲没读书,但她爱让她的儿女们读书。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男男女女,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毕业没毕业的都有,但每个孩子,都是自己读到不愿读为止。在六七十年代,依我们的家境,父母能这么做非常不易。但母亲乐意供孩子读书,哪怕每年的春秋两季开学她都要厚着脸皮去东挪西借。那些日子里,哪怕日子再艰苦再难撑,母亲也是两句话常挂在嘴边:“饭管饱,不误身子,书管读,不误脑子;饭吃饱了别硬塞,书不读了不强求。”这是一个当家女人对儿女的许诺,也是她的治家方针。或许正是因了这样的治家方针,我们家很少添置什么贵重物品,甚至连碗筷也是点着人买,缺一只补一只,缺一双补一双。家中稍有余钱,除了交学费还学费,就是买米添粮。母亲的生活目标简单明了,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效果却是出奇的好:一晃眼,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已经是“奔四奔五”的人了,但自小到今,我们的身体都结结实实,无病无灾,再加之,我们多少也都算是读过书开了窍的人,脑子都还好使,各自成家后,生活虽然没有大富大贵大出息,每个人还算过得和和乐乐滋滋美美。
儿女们都大了,母亲便心欢了。儿女升了学在她够不着的地方有了好工作,她高兴,没考上在跟前种地的,她也不数落,是真正的顺其自然。到后来,女儿出嫁了,儿子到外地工作了,母亲便经常要到散居各地的儿女们那儿看看。母亲说,手背手心都是肉,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血肉,一年半载的没见到,总感觉哪儿少了一块。父亲去世之后,母亲一走动,家里的老屋便经常空着。房子一空,便容易遭贼。今年春上,母亲正在姐那儿“巡视”着呢,却突然听大嫂打来电话说家中被偷了,母亲急成什么似的,她从不敢坐摩托,那天却冒险让姐夫用摩托载了她回来。破旧的老屋里,贼把所有的陶陶罐罐弄了个底朝天,狼藉得很。母亲却不管,直奔一个樟木箱子而去。都以为老人家藏了什么宝呢,打开一看,却是满满的一箱子书。这个大而沉的箱子是母亲的陪嫁,她舍得用来装书,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无金银首饰可搁,二是樟木箱子搁书不招虫子又不易受潮,搁多久都像新的似的。看到满满的一箱子放了二十几年的“新书”还在,母亲这才长舒一口气,说:“亏得那贼人不读书,不识货。”和母亲一起清理旧物的大嫂不知母亲的心思,嫌这些书没地方搁又重得搬不动,便对母亲说:“这些书早没用了,我们当废纸卖了吧?”母亲盯嫂子一眼,说:“这可都是六崽留下来的书呢?书是读书人的灶头,你见过有谁家卖灶头的吗?我都当宝守了二十几年了,你能狠下心来卖了啊?”嫂子一下子就红了脸,没了声。
国庆节那天,我应酬到晚上八点才回到家里。客厅里一团漆黑,母亲不看电视,在干什么呢?我推开儿子的房间,却见儿子在做作业,妻子在一旁辅导,头发花白的母亲,也拿着一本书在看。三代同室看书的情景,让我一下愣在那儿。我问母亲为啥不看电视,母亲忙把我拉到外面,说:“小孙子在做作业,我看电视,他哪安得下心?”然后,她又咧着没牙的嘴直笑:“小时候,你们做作业,我也是这样假装识字的样子,坐在一旁陪着你们,你不记得啦?”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小时候母亲陪读的情景?不怕你笑话,大哥家的新楼房里,至今还放着一个又大又旧的书柜,里面码放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课本和作业本啊什么的。我家不是什么书香人家,母亲却如此看重这些破烂东西,这让我们村里的人很难理解,其实,这些书要是搁别的乡下人家,大人不是给小孩擦屁股、糊墙就是压陶陶罐罐的口子去了。但母亲从来不拿我们的书这样去“糟蹋”,一直当钱一样存着看着,在三十年前就专门费了大钱添置家里最贵的大件——全樟木做的七层大书柜。如此这般,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在村里人嘴里多了一个“书呆子”的叫法。
说来也巧,那天母亲拿起书指点给我看的时候,电视里正在重播“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78岁生日的访问节目。袁隆平老人终其一生专注于杂交水稻的科研,造福人口众多的祖国甚至是全人类。想起母亲今年也正好78岁,而我们兄弟姐妹七个及我们的儿女,对于我不识字的母亲来说,无异于也是一个“大家”和一个小小的“人类”。她倾尽一生心血让儿女们茁壮成人成家,犹如袁隆平之于水稻的专注和投入。
那一天,我心里在健健康康的农田里的大科学家和健健康康的不识字的“书呆子”母亲之间划了等号。母亲和袁隆平,天地不一样,身手也不同,但他们生命的意义却一样深远,赢得的敬重和感恩,也一样厚重——至少,在我的眼里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