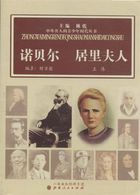杭州上学
浙江高等学堂是当时浙江的最高学府,是一所新式学校。它拥有优秀的教师和学生,邵锡康(邵飘萍考试报名时用名)、陈布雷、邵元冲等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比何炳松高一届,而金兆梓则进入了杭州府中学堂。异乡求学,举目无亲,难免寂寞,于是,何炳松与金兆梓这两个原先并不太熟悉的小伙伴自然而然地亲近起来。杭州是我国名胜之地,风景如画,六桥三竺之间,经常可见两人出游的踪迹。在何炳松逝世后,金兆梓曾深情地回忆过这些数十年前的往事。
经过六年学习,何炳松学到了全面的近代文化知识,娴熟地掌握了英语,为进一步的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2年冬,他作为浙江高等学堂(当时已改称浙江高等学校)第二届毕业生顺利毕业。当时,毕业生分为一、二两类,每类又按照成绩分为最优等、优等和中等。据台湾“教育部”所藏有关档案,何炳松的毕业分数为89.8分,列第一类之首。而在平时的学习中,他的成绩也十分优秀,升入正科后,曾连续三年被学校授予第一名奖。司琦编:《何炳松校长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6页。因此,金兆梓说他“无试不冠军”。当时的学校监督孙智敏在《金华何君柏丞墓表》中说:“同堂师友咸心许君之学行卓然异等”,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好学生。由于平时品学兼优,而毕业成绩又获全校第一,他被浙江省选派官费留学美国。
在杭州就学期间,何炳松通过同窗汤修慧认识了她的丈夫邵飘萍,以后常相往来。
出国之前,何炳松回乡省亲,此时他已经与同乡曹绿芝结婚。在短短的探亲期间,他还应母校金华中学的邀请,教了一段时间的英语课。当时,即使在金华这样的城市,英语教师还是十分缺乏的。那么,这位初为人师的青年的教学效果如何呢?当时的二年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杜佐周曾有过生动的描述:“有一天早晨,我们抱着很热烈的希望和很兴奋的情绪,等待一位新聘英文教员的来临。上课的钟已经敲过了,这位年轻隽秀的先生,就出现在我们这一群静肃而愉快的学生前面开始他的教学。他的风度,他的清晰正确的发音,他的扼要动听的说明,以及他的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们都感觉着得到一位昔未曾有的优良教师教学的幸运。”“我从少就欢喜英文这一科,我的成绩亦从来没有使先生们失望过。故何师对我亦特别看待。平时奖誉我,鼓励我,而且给我许多将来的期望。我们师生间的深厚感情,就在这个时候树立一种坚强的基础。”看来,这位代课教师不但课上得好,而且非常敬业,对学生十分喜爱,因此也深得学生爱戴。这种师生间的纯洁友谊,伴随了两人的一生。
据杜佐周回忆,20世纪初叶,他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到北平(今北京)参加公派留学的复试,因为这一年浙江省的留学名额只有5人,而传闻人选已经内定,考试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由于家道清寒而毫无背景,他觉得非常失望,于是请求当时在北京任教的何炳松探听究竟,并代为力争公道。这位昔日的老师一口应允,并笑着安慰他说:“此系谣言,当非事实。果若然者,自当就力之可能而代争之。”后来,杜佐周被录取为官费留学生,何炳松为之大喜,详细地告诉他留美应该注意的各种事项。因为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出国以后,杜佐周一帆风顺。
杜佐周学成回国后,何炳松曾数次邀请他共事,都因各种原因没有成功。1935年,何炳松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在他的坚邀下,杜佐周终于担任了总务长兼大学秘书。民国年间,大学大多不设副校长,大学秘书地位仅次于校长,负责协调各方关系,所以职责重大。从此,作为重要助手,他追随何炳松左右达7年之久。抗战后期,在重庆为暨大洽办校务的杜佐周又因何炳松的推荐而被任命为国立英士大学校长。数年后,他因故力辞校长获准,教育部改派何炳松接任,不久,何炳松因劳瘁过度溘然而逝。杜佐周对此事悔恨交加:“我也不才,治校无成。否则,何师或不至调长英大;若不调长英大,何师或可不死;即死,亦不至若是之速。是则何师之死,诚我害之也!”均见杜佐周:《我与何柏丞先生》,《读书通讯》第117期。师生情深,可见一斑。
负笈美国
1913年2月初,24岁的何炳松辞别亲友,坐船横渡浩瀚的太平洋,抵达美国西海岸,进入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当时的美国东西海岸发展程度相差十分悬殊,加州人少地广,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对外国学生没有什么吸引力。当时即将从加州大学毕业的蒋梦麟说,该大学创办于1868年,到1912年已有学生5000人,教职员600人。它对本州居民身份的学生不收学费,外州或外国学生则半年收10美元的学费。中国学生凡在国内高等学校毕业者,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入学,并允许以中文代替希腊文或拉丁文,即免修一门外语。上述规定对中国学生来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根据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规定,官费生每月经费80美元,虽然各省实际支付数额有差异,但加州大学的学费对中国留学生而言,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当时在加州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才20多人,包括3名女生。蒋梦麟:《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壬子年留美学生年报》(1912)。当时中国留美学生集中于美国的东部及中部,西部人数较少,看来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西部经济、文化等都比较落后。
何炳松入学后,选修了法语D、政治学1B、经济学105B等三门课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他就请了长假离校,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返校。20世纪80年代中,为撰写《何炳松年谱》,笔者曾致函何炳松在美就读的各所大学,了解有关情况。据当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W。M。Leatsch先生告知,何炳松是办理了请假手续离校的,根据注册单,假期是2月13日至3月13日。至于为何没有返校,原因不明,但显然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浙江省每个月寄给留学生的费用是80美元,为各省之冠。
当年夏天,通过考试,何炳松被位于美国中部的威斯康辛大学录取,并于秋季入学,成为该校政治系的一名学生。威斯康辛是美国的著名大学,它对学生的要求较高,课业负担也比较重。一年级上学期,何炳松选修了五门课程,包括两门政治学、两门德语和一门地质学。下学期则选修了两门政治学、一门地质学、一门德语和一门法语。二年级上、下学期,分别选修五门政治学课程,并开始做毕业论文。与此同时,还应聘担任本系助教,负责收集有关远东和中日关系的史料。
在完成繁忙课业的同时,何炳松还积极参加了校内外的社会活动。入学不久,他就向《留美学生年报》投稿,并因此结识了当时担任该报编辑的胡适,两人成为笔友。据何炳松在《增补章实斋年谱序》中回忆,他是向《留美学生季报》投稿,但此时该报尚未创刊,可能是将其前身《留美学生年报》误记为《季报》。《留美学生年报》是由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主办的刊物(但杂志署留美学生会),它的前身是《美国留学报告》,宣统二年(1910)六月改名,它的第一任总编是一位女性——胡彬夏,侯德榜:《留美中国学生季报创办历史及其历来办理情形》,《留美学生季报》第七年(1918)冬季第四号。其弟胡刚复是我国物理学的奠基人,清末与两兄长敦复、明复先后留美,被称为“一门三博士”。
胡彬夏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留美学生朱庭祺均曾在《年报》第一期上撰文,分别介绍留美学生及其组织的情况,但两人对留美学生会成立时间的说法不同。据朱说,中国学会成立于“去秋”,即宣统元年(1909)秋季,它的宗旨有三条:输进学识于中国,研究学问、发达学问,联络学习专门之人,学会下设三个机构:著作部、职员部、专门部。胡彬夏:《中国学会留美支会之缘起》,朱庭祺:《美国留学界》,《留美学生年报》庚戌年(1910)第一期。胡则说中国学会留美支会成立于“今岁七月”,即1910年。然而《年报》已在6月出版,故胡彬夏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而且,阴历七月已是公历9月,所谓“七月流火”即指心宿现于西方,秋季将到,故朱庭祺“去秋”的说法是正确的,胡彬夏的“今岁七月”之说疑为“去岁七月”之误,或是文章写成于前一年,发表时忘了改日期;而“中国学会”则或是“中国学会留美支会”的简称。该会虽然在美国编辑稿件,却在国内出版,由上海国光印刷所印刷,中华书局发行。
其实,《年报》的真正主办者可能是李肇安任会长的西美学生会,该会办有两个杂志——英文月报和中文年报,总编辑分别为张履鳌和胡彬夏。当时另有顾维钧任会长的东美学生会,而东西美学生联合会的会长是王正庭。1914年3月,《年报》改名为《留美学生季报》。据该报《凡例》,每年发行4期,逢3月、6月、9月、12月在上海出版,由留美学生会发刊,中华书局发行,但它不是留美学生会的机关报。它的编辑和干事由东美、中美、西美留学生会按会员人数的比例在留美夏会上公举产生,再在其中选出总编辑和总干事。
所谓“留美夏会”,是留美学生在夏季举行的年会。为什么要在夏季换届选举呢?那是为了让当选者有半年时间筹备次年任内之事宜。1914年5月,该报工作人员换届,经过选举,产生张贻志、李锡之等11名编辑以及王谟、邢契莘等11名干事;并推举任鸿隽任总编辑,过探先任干事部总干事,比较特殊的是,唯有何炳松兼任编辑和干事二职。编辑部成员任期一年,自次年年初开始履职。无论《年报》还是《季报》,在留学生中和社会上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因为它是了解留美学生情况的最重要的窗口。
这一年,何炳松还被选为由29名留学生组成的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学生会副会长。
金兆梓等友人这样描述何炳松:性格沉静,外表给人的感觉有点“冷”。作为至交,他们的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这更适合中年以后的何炳松。而在美国留学期间,何炳松则富于激情,十分活跃,积极参与留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例如,1915年5月,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学生会在学校的格致教室举行第一次辩论会,就“男女应享同等参政权”这一议题组成正、反两方进行辩论,双方各有一名主辩、两名助辩。尽管此时何炳松已临近毕业,诸事毕集,但他还是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是3名裁判员之一。据《留美学生季报》民国4年(1915)夏季第二号记载,双方雄辩滔滔,舌战达1小时多,结果,正方获胜。巧合的是,反方的一名助辩郑宗海是何炳松在浙江高等学校时的同学,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民国时曾任浙江大学教务长。
由于经常与其他留学生探讨各种问题,何炳松的眼界日益开阔,思考问题也越发深远。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种种弱肉强食的现象,他对祖国的命运倍加关切,在《留美学生季报》民国4年春季第一号上发表的随笔《课余杂录》,就体现了这种深情。文章开头就沉痛地说:“租借地一日不归还,吾国国耻,终一日不能洗尽。”他在分析我国面临的形势时指出,日本战胜俄国后,对华方针已经大变,时时流露瓜分我国的野心。而1914年日本在胶济湾与德国的战事中,更是屡屡侵犯我国主权,足见“弱国无公理”。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日本“脱亚入欧”,不认自己为黄种人,急欲与欧人争霸的原因,也有国人未能尽自己义务的原因。因此,要想避免任人宰割,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强不息。何炳松不但殷殷提醒人们警惕日本的野心,还驳斥西方的“黄祸论”,认为所谓中国10年内养兵百万即可纵横欧亚的说法“未免过当”。这种正确估计自己,不妄自尊大的清醒认识不但在当时难能可贵,即使在今天对某些人也不啻一副清醒剂。
民国4年(1915)夏天,经过两年的学习,何炳松从威斯康辛大学毕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同时,还获得了学校颁发的荣誉奖。当年秋季,他考入了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
在毕业前夕,何炳松开始主动与同乡傅则黄(即傅东华)通信,尽管这时他特别繁忙。接到他的频繁来信,傅东华既感到意外,更觉得感动,因为,此前两人并没有什么来往,眼下的地位又相差悬殊。傅东华曾回忆道,两人虽是同乡同里,各自的父亲都是金华城里有名的塾师,但父辈之间的交往并不密切,因此儿童时期难得有机会见面。自己12岁时父亲去世,第二年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兄长又因病不治,只剩下寡母弱妹,家徒四壁,以至无人理睬,而比他大三岁的何炳松这时已经以幼童身份进学,在城里名噪一时了。此后,何炳松更是一帆风顺地放洋留学,而自己当时“还是一个在社会上瞎碰瞎撞以觅自我教育机会的流浪青年”,两人完全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那么,“他为什么要跟我通信呢——这疑问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我当时那种自我教育的苦斗生活使他感动了,这才使他不断以书信给我鼓励,给我安慰的”傅则黄:《与我相处大半世的何柏丞》。何炳松这种“己欲立而立人”的行为想必给傅东华以很大的鼓励。其实,何炳松对傅东华的关心和理解,有些是傅本人也不知道的。抗战中暨大内撤,傅东华因侍奉年近八旬的老母,行动迟缓,不幸陷敌。何炳松闻讯忧心如焚,他年纪尚幼的女儿在一旁不知轻重地说:“这人为什么不以身殉国呢?”他立刻严肃地说:“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何淑馨:《怀念父亲》,《何炳松纪念文集》,第587页。表示了对友人不幸的同情和体谅。而傅东华这位解放后在《辞海》的编纂中,唯一通读并修改全文,默默地为祖国文教事业作出巨大奉献的学者如果知道这一切,对何炳松的这种态度想必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在给傅东华的信里,何炳松谈到了美国的生活。他没有多讲美国的繁华,反而经常抱怨吃不惯以面包奶油为主食的西餐,说很想念家乡风味,以致形诸梦寐。幸亏,仅仅过了一年,他就顺利地结束学业回国,否则,还真难医治这思乡病呢。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一所极为有名的学府,所藏中国书籍特别多。威尔逊总统曾任该校政治学教授,后任校长,学校师资力量十分雄厚。在何炳松留学期间,美国历史学界正在进行着重大的变革。自19世纪以来,德国的兰克学派统治了欧美历史学界,历史著作几乎都着眼于政治史的描述,而不注意其他方面。到1900年,尽管德国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发出了不同声音,但其影响相当微弱。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美国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为首的一批史学家大力倡导“新史学”,反对只重视政治史,主张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用综合的方法分析和解释历史,而非传统史学坚持的仅仅描述历史。鲁滨孙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后来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先后主编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的《年报》、《美国历史评论》,还曾任新社会研究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他不但撰写了大量著作,如《形成中的思潮》(The Mind in the Making,1921)、《知识的人性化》(The Humanizing of Knowledge,1923)、《文明的考验》(The On deal of Civilization,1926),及所有著作中最重要的《新史学》;而且还培养了比尔德、绍特威尔、约翰逊、巴恩斯等一大批成就斐然的学生,这些人在历史、教育等学术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张广智说:“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史学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新史学运动。”张广智:《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新史学派的影响,还越出国界,遍及世界历史学界。
其实,19世纪末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的特纳也提出过与鲁滨孙相同的观点,并为相当多的同行所接受。因此,尽管何炳松入学时特纳已经离校,但流风所及,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由于率先译介了大量新史学派的著作并以此理论进行史学研究,何炳松遂被公认为是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1916年初夏,何炳松取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国际法》还荣获学校论文第一名奖。在美期间,他还用英文写了论文《中国政党小史》,后来节译成中文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校刊《法政学报》上刊载。文章认为,中国有政党自戊戌政变始,这就是立宪和革命两党。辛亥革命后,虽然政党林立,都是两党的化身;当时最大的两个党中,进步党就是原来的立宪党,国民党就是原来的革命党。文章先叙述了立宪党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对清廷的态度,以及它们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接着叙述了国民党、进步党的分化组合及与袁世凯的不同关系。
《中国古代国际法》是一篇万余字的长文。何炳松有感于清政府不懂国际法,在对外交往中动辄得咎,而西方蔑视我国为无法之邦的现状,研究中国古代的国际法。他认为,希腊、罗马的国际法,与《左传》中的记载相同,《战国策》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他从春秋时列国之间的交换使臣、缔结条约、建立同盟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从中西各国均重使臣、信赖神权、尊重条约等方面作了比较研究。他指出,秦统一后,“国际习惯发生之机会,于以告终”,于是国人便误将国际法视作西方的新学。何炳松:《中国古代国际法》,《法政学报》第2卷第5期(1925年5月)。
7月,在双亲的不断催促下,何炳松迅速办妥了各种手续,启程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