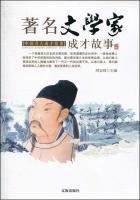表现之一:傻和赖。
报载: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押赴刑场的途中,动用全部心思在脸上挤出媚笑……一个要死的人了,还要强迫自己笑,真也难为他了。原来这是有原因的,他开始跟警察蘑菇:“我能写毛笔字,你们就别毙我了,留着我给你们写字,天天写,写多少都行……”一个曾经做过高官的人,难道会不清楚此时毙不毙他并不由押送他的警察说了算?求生的欲望使他变傻变贱,能求就求,能赖就赖,伸出手乱抓救命草。
还有另外一种傻,湖南有个死囚犯赵正洪,行刑前的最后一个夜晚,通宿没有合眼,临到要上刑场了,“脸上又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并带着乞求的神情对一个穿便服的人喊:记者大哥,能给我照张相吗?”这时候还要照张相给谁看呢?如果是想给自己留纪念,显然已经用不上了,他这时候倒应该“万念俱灰”才对。想给别人留纪念?好像也多此一举,就算是他的家人,会愿意看到他被枪毙前的照片吗?再说他的相已经照得不少了,至少在抓他的通缉令上,他的尊容已经散发到了全国!其实,他是下意识地想找点事干,拖延时间,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好在这个请求不像胡长清的请求那么不切实际,警察立刻就满足了他。
表现之二:懵懂无知。
今年春天,我跟踪了两个死刑犯行刑前后的全过程,他们对待死的态度更令我震惊。一个是抢劫杀人,在行刑前警察问他要留什么遗言,他大大咧咧地寻思了一会儿,然后没头没尾地扔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别告诉我大姐。”我猜他可能最尊重他大姐,或者他大姐最疼爱他。另一个是强奸未遂怒而杀人,临死前警察问他对家里人还有什么要说的?他咧咧嘴,想笑而没有笑出来:“说什么呀?快给咱来根烟吧!”我当时深信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死,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正经地活过。死亡是今生的一部分,人有什么样的生,才会有什么样的死。有个名人说过:人们往往以为日以继夜地在学习如何生存,实际一直在学习怎样死去。死是生的自然延续,至死方休——这就是整个人生!按一般规律,活得越久的人越怕死,而他们还太年轻了,一个21岁,另一个只有19岁,一个说上过小学,一个说上过初一,自小就惹事生非,劣迹不断……糊里糊涂地来了,又糊里糊涂地走了。
表现之三:极度恐惧、失态。
被称作“杀人狂魔”的张君,身上背负着29条命债,曾嚣张地说过:“凡是在我抢钱的时候妨碍了我,凡是看清楚我的人,我都要打死他!”临死前却彻底变了一个人,“早上7时20分,在法警为他上警绳时(即枪决前的五花大绑),竞发出了绝望的哭嚎,还间或伴有刺耳的尖叫,那一刻看守所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张君那变腔变调的如女声一样嚎叫。”在这之前他还向检察官磕头,对法警表白:“我过去很少说人话,今天要说点掏心窝子的人话……”在恶人中他算是死得最痛苦的。人一般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对死的恐惧是空洞的,总觉得具体的死亡离自己还很遥远。张君就不同了,他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死期,还要亲眼目睹自己死的来临。他的生活本身就一直被死神所支配,所追赶,这强化了他对死的想象,也就越发加剧了对死的恐惧。
另一方面,他的极度恐惧还来自死的公正,他的死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而是根据社会的意志,取决于法律的意志,这样的死不可逆转。“官法如炉真是炉,人心似铁不如铁”,过去他曾对别人的生命极端轻蔑,却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死——这也正是死刑的意义之所在。他的恐惧和失态,使其罪恶的一生画上了一个丑陋的句号。
表现之四:冷静,麻木。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死囚。炸死了168人的美国死刑犯麦克维,从被宣判死刑后就开始节食,到死的时候,1.88米的身高却只有71公斤重,有意让自己变得瘦骨嶙峋,制造慷慨赴义的形象。处决的前一天被移到候刑室,在与律师和亲友道别时,“心情显得异常轻松,对于由自己一手造成的大爆炸惨案仍坚持不悔,并自认是胜利者,以一人之力对抗联邦政府。”他的律师奈伊甚至说:“麦克维精神高亢,非常健谈、和气,还保持幽默感。”他还超下19世纪一位英国诗人的几句话,作为自己的遗诗:“不管这门有多么狭窄/不管承受怎样的惩罚/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舵手”。行刑的时候,他专注地将所有观看行刑的人看了一遍,似乎要把这些人的人数记清楚。他把杀人当做一种信仰,有了自己犯罪哲学。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他有来生,还会继续杀人。这就叫死不改悔!张君的同伙中也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名叫许军。执刑的前一天晚上一直呼呼大睡,押赴刑场前是法警把他喊醒的,好像被枪决后他就再也没有睡觉的时间了。将死的恶人还有其他一些表现,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观察和研究恶人在临死前有多少种表现,大致就可以推算出还活着的恶人有多少种类型。要抑恶扬善,就得先要了解恶。